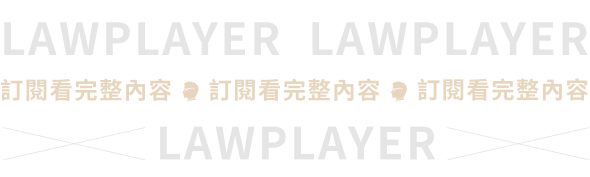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九十八年度重上更(八)字第二00號
關鍵資訊
-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 案件類型刑事
- 審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 裁判日期98 年 09 月 1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八年度重上更(八)字第二00號 上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丁○○即劉博仁 選任辯護人 郁旭華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三五四號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九九七二號),提起上訴,經本院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第八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原名劉博仁)明知甲○○並未同意在其(借款人應為呈駿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呈駿公司,名義負責人為蘇湫城,實際負責人為劉博仁》之誤)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企銀)借貸新臺幣(下同)四百五十萬元借款中,擔任連帶保證人,卻於民國(下同)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未經甲○○同意,擅自在其所立向臺灣企銀借貸四百五十萬元之借據上,於連帶保證人欄下,偽簽甲○○之署押,並盜蓋甲○○之印章,使甲○○成為該借款案之連帶保證人,嗣因丁○○無力清償該筆貸款,甲○○遭臺灣企銀向法院訴請清償時,始知悉上開偽造事實。案經甲○○告訴因認被告丁○○涉有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一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云云。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一百五十九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 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定有明文。本案所引證人在警詢所為之證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列為證據,且迄本院審理時,亦無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斟酌前開證人在警詢所為之證述,係在自由意志下所為陳述,並親閱筆錄無訛後始簽名作成之情況,且該證言及文書證據適為本案待證事實應審酌之必要事項,自有證據能力,合先說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且須適合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0五號、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二七五0號等判例參照)。復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等判例參照)。 四、公訴人認被告丁○○涉有前揭偽造文書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甲○○之指證與被告自承在前揭向臺灣企銀借貸之借據上代簽甲○○簽名,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丁○○堅決否認涉有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辯稱: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上的文字是伊填的,確經甲○○同意,章是她拿至呈駿公司蓋的;伊之所以在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上代簽甲○○簽名,乃因對保當天甲○○在場,經臺灣企銀承辦人員丙○○告知保證債務內容及確認連帶保證人之意願後,甲○○同意作保,惟甲○○未帶印章,銀行即將借據交予伊,並囑伊持之與連帶保證人蓋妥印章,故伊認甲○○既已同意作保,又在借據上蓋用印章,伊才在借據上代簽姓名,未盜蓋甲○○印章云云。 五、經查: (一)坐落臺南縣關廟鄉○○○段一二一九之一、一一三九地號二筆土地,地目為田,係被告所購買,因被告及其妻徐竹葉無自耕農身分,乃於八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先登記在有自耕農身分之其岳父徐度名義,於八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甲○○,再於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配偶徐竹葉名下;前揭二筆土地曾於八十三年四月十二日,以徐度名義向臺灣企銀設定一千五百萬元本金最高限額抵押權,由被告經營之呈駿公司向臺灣企銀借款三筆,分別為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之一百七十五萬元,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四百五十萬元、五百五十萬元,甲○○均為連帶保證人等情,為被告供述在卷,並有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授信約定書、一百七十五萬元中長期貸款契約影本、四百五十萬元借據影本在卷可參(見偵查卷第五至二十四頁)。其中四百五十萬元,與五百五十萬元之借款係同時間辦理,且五百五十萬元借款,於八十四年十二月間全數清償,有臺灣企銀93年11月25日93善化字第7029300231號函及93年12月13日93善化字第7029300250號函所附五百五十萬元貸款之週轉金貸款契約書可稽(見本院更一卷第五十九、六十一、六十二頁)。據被告辯稱:當時系爭二筆土地會以買賣登記在甲○○名下,乃因甲○○建議為免徵收贈與稅,先以買賣登記在甲○○名下,再以買賣移轉登記給徐竹葉云云,亦為告訴人於本院坦承:「(當時何以土地登記為你名義?)因呈駿公司買土地時,需自耕農之身分,所以無法登記給其太太,就登記給其岳父,本來他太太要遷戶籍到他岳父家,要半年才能取得自耕農身分,因當時我有自耕農身分,被告就要求是否能先用我之名義先登記為所有權人。」(見本院更八卷第七十二頁)。而被告辯稱:系爭貸款,因農地所有權人是甲○○,應銀行要求所有權人要當連帶保證人,才以甲○○為連帶保證人等語,並核與告訴人於偵查中告訴狀中所稱:八十三年五月間,因被告之妻徐竹葉向其商借名義以登記所有上揭坐落臺南縣關廟鄉○○○段一二一九之一暨同段一一三九號農地之所有權,前開土地已向臺灣企銀抵押借款等節相符合。然告訴人僅承認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之一百七十五萬元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坦承有親筆簽名蓋章於借據及授信約定書;否認為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四百五十萬元、五百五十萬元借款之連帶保證人。然四百五十萬元、五百五十萬元二筆借據上連帶保證人印章與告訴人印章相符,另連帶保證人欄上告訴人之署押被告坦承為其書寫;因五百五十萬元借款已全數清償,且公訴人亦未起訴五百五十萬元借款部分,本件乃僅就公訴人起訴之四百五十萬元借款,論述被告是否經告訴人同意,簽署告訴人之署押,及被告是否盜蓋告訴人之印章。 (二)上開二筆土地向臺灣企銀設定本金最高限額抵押權一千五百萬元,告訴人承認之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借款一百七十五萬元及不承認之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借款四百五十萬元,均在該額度內,雖臺灣企銀本件借款承辦人丙○○、乙○○於歷審到庭作證時未曾說明四百五十萬元借款為最高限額抵押權額度內增貸部分,但告訴人承認四百五十萬元借款為增貸(見本院更八卷第七十二頁)。而該筆本金最高限額抵押權額度內第一筆借款一百七十五萬元有向告訴人徵信,經告訴人於授信約定書上簽名蓋章(見偵查卷第二十二頁,見簽人為王明山,承辦人丙○○稱之為「對保」),告訴人並於一百七十五萬元借款之中長期貸款契約(借據)內簽名蓋章,為告訴人供認在卷,並有中長期貸款契約影本可憑(見偵查卷第二十一頁);另增貸四百五十萬元借款部分,據證人即承辦人丙○○於民事案件證稱:「銀行採印鑑制度,授信約定書第一次一定要本人親自簽名蓋章,以後只要印鑑相符,即可借款。」(見八十八年度重訴字第二五五號民事卷《下稱民事一審卷》第十八頁反面),於原審證稱:「與授信約定書上的印鑑一致即可放款,所以不核對是否為本人簽名。本件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上甲○○的印章與授信約定書一致。」(見一審卷第二十六頁),證述臺灣企銀增貸承辦手續,不須承辦人拿借據予連帶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祇須借據上連帶保證人之印章與原授信約定書內之印章一致,即合乎借款程序,亦即不須有見簽人見證連帶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之所謂「對保」手續。復據證人即該行襄理乙○○於原審證實本件四百五十萬元借款不需要對保,只需告知保證人保證的範圍(見一審卷第四十六頁)。依上開證述,可知臺灣企銀貸款程序,僅第一次辦理借款時須由承辦人「對保」,即承辦人向連帶保證人徵信,拿授信約定書及借據予連帶保證人確認,並在其上簽名蓋章;第二次以後額度內增貸部分,則不須承辦人拿借據予連帶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祇須借據上連帶保證人之印章與原授信約定書內之印章一致,即合乎借款程序,亦即不須有承辦人見證連帶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之所謂「對保」手續。承辦人丙○○於原審稱之為對保(見一審卷第二十五頁),於本院更四審證稱不是對保(見本院更四卷第0一八頁),於本院更八審證稱:「(你剛才說有到呈駿公司,這些事情,你認為這不是對保?)這應算對保,但這次不算對保,因對保一定要有見簽人。」「(你何以在原審作證時,說這就是對保?提示並告以要旨)也算是一種對保。」(見本院更八卷第九十五、九十六頁),因丙○○先後所述不一,模糊借款對保手續,致本件四百五十萬元增貸借款案情紛擾難解。 (三)本件呈駿公司向臺灣企銀借款,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借款一百七十五萬元及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借款四百五十萬元,承辦借款手續之人均為丙○○,為丙○○供述在卷(見本院更四卷第一0八頁、本院更六卷第七十七頁)。而一百七十五萬元借款出去向告訴人辦理對保手續,即持授信約定書、中長期貸款契約(借據)予告訴人簽名蓋章者,由卷附授信約定書顯示見簽人為王明山(見偵查卷第二十二頁),即為該行襄理王明山,亦為丙○○證實(見本院更六卷第七十六頁),並為告訴人所不爭,足見丙○○此次未參與對保手續。另四百五十萬元增貸借款,承辦人丙○○及另一襄理乙○○,曾於借款前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呈駿公司,為丙○○及乙○○證述在卷(見本院更一卷第七十三頁、本院更四卷第一一0頁、本院更八卷第九十五、一0三頁),襄理乙○○並於民事事件八十九年六月九日準備程序期日提出其上記載襄理乙○○及辦事員丙○○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四十分,一同外出至關廟鄉「勘現洽客戶」之員工外出登記簿影本一紙為證(見八十八年度上字第四九0號民事卷《下稱民事二審卷》第三十九頁反面、一審卷第四十九頁)。被告供陳:伊之所以在系爭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上代簽告訴人簽名,乃因對保當天告訴人在場,經臺灣企銀承辦人員丙○○告知保證債務內容及確認連帶保證人之意願後,告訴人同意作保,惟告訴人未帶印章,銀行即將借據交予伊,並囑伊持之與連帶保證人蓋妥印章,故伊認告訴人既已同意作保,又在借據上蓋用印章,伊才在借據上代簽姓名等語。業據丙○○於本院更四審證稱:「(《提示原審卷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筆錄後附員工外出登記簿影本》此員工外出登記簿影本第七欄記載十二月二十一日你曾經與乙○○襄理外出洽公,去何處?處理何事情?)那天是我與乙○○襄理到一家呈駿公司,看公司是否確實在營運。」「(此行的目的為何?)主要看公司是否正常營運,因為要放款不放心公司是否確實在生產、營運。」「(是否還有其他目的?)另外要確定保證人是否知道有保證的事情。」(見本院更四卷第一一0頁),且據證人乙○○於原審證稱:「(《提示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百五十萬元借據》當時是否由你承辦及對保?)沒有去對保。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與丙○○到關廟鄉呈駿公司,目的是勘查現場看公司有無營業。」(見一審卷第四十五頁),於本院更八審證稱:「我是陪同放款之經辦人去勘查現場。」(見本院更八卷第一0三頁),一致證述當天係去查勘借款之呈駿公司營運情形,及確認保證人是否知道有保證之事,不是去辦對保手續;乃因四百五十萬元增貸借款,不須予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僅須核對借據上連帶保證人之印章與原授信約定書內之印章一致,即合乎借款程序,不須辦理「對保」程序,詳如前述,故二位承辦人證述僅查勘借款人呈駿公司營運情形,並確認保證人是否知道有保證的事情等詞,應屬事實,此外卷附彼等外出登記簿亦登載「外出事由:勘現、洽客戶。」(見一審卷第四十九頁),亦可確定二位證人丙○○、乙○○之證述為真實可信。而證人丙○○迭於原審及本院更四、更八審均證稱:至呈駿公司之前有先打電話予告訴人(見一審卷第二十五頁、本院更四卷第一一七頁、本院更八卷第九十四頁),證述有通知告訴人到場,並據證人乙○○於民事事件審理時證稱:「我只是審核借款人營運是否正常?借款用途是否恰當?保證人是否有足夠資力作保?我不負責審核是否本人簽名,我不用對保,我有到借款人公司去,因時間太久是否看過甲○○沒有印象,目的是要看公司是否營運正常?我們內規是必須通知保證人願不願作保,若不願作保我們會通知更換保證人,本件我們有通知,開庭前我有問過經辦人員,經辦人員丙○○說絕對有通知」證實(見民事二審卷第三十八頁);又本件貸款之承辦人係丙○○,證人乙○○則負責審核借款人及保證人資力等項,故有至現場勘查之必要,證人乙○○所陳銀行內部規定必須通知保證人,如不願作保將會更換保證人,衡情本件如告訴人未同意作保,勢將更換保證人,否則銀行無從放款,上開事項屬於乙○○審核範圍,既已勘查現場後准予放貸,當時應有通知保證人到場,否則如何審核?況告訴人為貸款土地之名義提供人(當時上開二筆土地之所有權人為告訴人,詳如後述),臺灣企銀放款時更不可能會忽略或放過抵押土地之所有權人,又證人丙○○上開證述,核與證人徐度及被告所述當時到場人數相同,足認當時臺灣企銀確已通知擔任連帶保證人之徐度及告訴人到場。證人丙○○復於民事案件證稱:「甲○○人有到公司,她說『印章未帶』。她確實有到公司(指呈駿公司),她要做保證人要簽契約及保證書時有在現場,我請他們公司的劉博仁帶回去給甲○○蓋,而且我也交代林小姐印章一定要蓋與銀行留存的授信約定書相同的印鑑章。」「(當時有否在場?有否反對?)在場,也沒反對,她說『劉先生拿回去後她會蓋章』,剛才所說的公司是劉博仁的呈駿公司不是到我們的公司蓋章,當時有劉博仁、甲○○、徐度,因仁德不熟,我和襄理一起去。」(見民事二審卷第二十七頁正反面),於原審證稱:「我有先確認他們的身份,..我有告知他們劉博仁公司要再借另一筆四百五十萬元借款。當天徐度及甲○○沒有帶印章,所以借據就先放在劉博仁處,我特別告訴他們印章一定要與授信約定書一樣。」(見一審卷第二十五、二十六頁),於本院更六審證稱;「我當天去呈駿公司,被告介紹一名女子說他就是保證人甲○○,但當天保證人沒有帶印章,我就將借據交給被告,並交待證人要蓋跟授信約定書上同一個印章。」(見本院更六卷第七十四頁),於本院更八審證稱:「(你到呈駿公司時,甲○○是否有在場?)我當時並無核對其之身份證,但丁○○有當場介紹她就是甲○○。」「(你當時有無詢問她是否同意要作保?)我當時有告知她有二筆借款,其中一筆是四百五十萬元,其中一筆是五百五十萬元,因她沒帶印章,所以我就把二張借據交給丁○○,請他拿去給甲○○蓋章,我還當場告訴甲○○一定蓋用授信約定書上之印章,否則銀行不會放款。」「(你當場有無告訴甲○○,她是擔任這二筆借款之連帶保證人?)有,她說她知道。」(見本院更八卷第九十五頁),證述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呈駿公司時,經被告介紹告訴人在場,有告知借款四百五十萬元之事,告訴人未帶印章,乃將借據交給被告,請被告拿去給告訴人蓋章,還當場告訴告訴人一定要蓋授信約定書上之印章;並核與證人徐度於原審經提示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並訊以:「(有無擔任劉博仁之連帶保證人時?)有,是我外孫載我到關廟的工廠對保,現場有三人,二男一女,我女婿(指被告)說二個男的是銀行的,一個女的是代書,是來對保的。」(見一審卷第四十三頁),所陳告訴人在場,銀行人員到場辦理四百五十萬元貸款之事,並無不合。足見告訴人應知悉本件四百五十萬元增貸借款之事,亦明知而為本件增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顯見告訴人同意為本件四百五十萬元增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無訛,則被告所稱因得告訴人之同意而代簽借據之告訴人簽名等語,自非無據。況四百五十萬元增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印文核與告訴人之印章相符,亦經原審於民事案件審理時,當庭以對角折線法核對該印文,確與前揭中長期貸款契約書及授信約定書相符(見民事一審卷第九十三之一頁),並為告訴人所不爭,是被告所為簽署告訴人之署押,顯與偽造文書構成要件不符。 (四)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訴:因前開土地向臺灣企銀抵押借款,渠才於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一筆一百七十五萬元之貸款契約書上簽名蓋章,後來被告向渠稱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簽署之契約書上漏蓋印章,請渠再次交付該印章,俾補蓋印章,渠未加防備而交付印章,被告卻於四百五十萬元之借據上,盜蓋該印章,並偽造其署押,渠完全不知該筆四百五十萬元之借貸,被告盜蓋渠印章,使渠成為四百五十萬元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云云。然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之作成日期為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借據影本一紙在卷可稽(見偵查卷第六十三頁),告訴人承認之一百七十五萬元借據乃係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作成,二者時間相差五個月,倘如告訴人所稱被告係以一百七十五萬元借款契約漏蓋印章為由,向告訴人騙取印章而盜蓋在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上,衡情騙取告訴人印章之時間應在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後不久(況告訴人尚於告訴狀內陳稱:該補蓋之印章,被告於翌日即返還,見偵查卷第二頁、民事二審卷第三十三頁),豈有事隔多月,始稱漏蓋印章,而告訴人仍深信不疑未加防備之理?況依告訴人前揭所稱該補蓋之印章,被告於翌日即還,則被告在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補章之後,既已於同月三十日返還,則告訴人之印章又豈可能重新放置在被告處所,迄至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始再行返還之理?此亦與告訴人所述不符。再者,告訴人指稱遭被告盜蓋上揭之印章,固非其留存於戶政機關之印鑑章,惟仍係其擔任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借款一百七十五萬元之連帶保證人留存於借款銀行臺灣企銀之同一印章,該顆印章既係由告訴人自己保管,並未交付被告保管,被告與告訴人又非有同居共財之情形,被告自難以從告訴人處取得印章;況告訴人為執業多年代書,為其供述在卷,對於有保證責任之銀行印鑑章,有其職業保管之敏感性,依常理而言,其對於印章之使用及保管之注意程度必較一般人為高,如非得其同意,自不會隨意交由他人蓋用,甚或被盜用之可能。是公訴人指訴被告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未經告訴人同意,擅自在其所立向臺灣企銀借貸四百五十萬元之借據上,於連帶保證人欄下,盜蓋告訴人之印章,使告訴人成為該借款案之連帶保證人云云,尚屬無據。另告訴人於民事案件主張:該印章係被告所偽刻蓋用云云,已為原審於民事案件審理時,當庭以對角折線法核對該印文,確與前揭中長期貸款契約書及授信約定書相符,是該印章既非被告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借款四百五十萬元時盜用,則該印章既在告訴人保管中,被告欲使用蓋連帶保證人章,應認被告所辯告訴人在借據上蓋用印章等詞符合常情,而得認定。 (五)本件四百五十萬元借款,臺灣企銀業對被告及告訴人等六人提起連帶給付借款之民事請求事件(八十八年重訴字第二五五號),告訴人於該請求給付借款事件,原否認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面額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上連帶保證人欄之簽名為其所為,印章亦非其所有,尤否認授權他人簽名、代刻印章,並主張:該印章係被告所偽刻蓋用云云(見民事一審卷第六十一頁),但原審於審理時,當庭以對角折線法核對該印文,確與前揭中長期貸款契約書及授信約定書相符,告訴人始改稱:係被告所盜蓋云云(見民事一審卷第九十三之一頁),然為民事事件判決所不採,仍認告訴人為該面額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上連帶保證人,應負四百五十萬元借款之連帶保證責任,為告訴人敗訴之判決。告訴人提起上訴,亦經本院八十八年上字第四九0號民事事件認『本件上訴人(指告訴人)因原審同案被告徐竹葉信託登記系爭二筆農地之所有權予其名下,而以該二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予被上訴人(指臺灣企銀),被上訴人要求提供物保之土地所有權人之上訴人(指告訴人),應一併擔任系爭借款主債務人之連帶保證人(人保)者,核與金融機構核貸習慣相符,且為兩造所不爭,此部分事實堪以肯認;又上訴人於本院前審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行準備程序時,自陳其職業為代書,按諸常理,其對於印章之使用及保管之注意程度必較一般人為高,乃上訴人竟稱:伊簽了一百七十五萬元(貸款契約)後,過一段時間,劉博仁說:一百七十五萬元(貸款契約)有漏蓋章要補蓋,沒有說何處漏蓋、因我沒空,而印章又不是登記的印鑑章,所以就交給他,隔天劉博仁才拿印章來還我等語,然系爭印章縱非戶政事務所依法審認之印鑑,惟係上訴人簽署系爭中長期貸款契約時所使用,上訴人既任代書工作,豈有不知其重要性,上訴人竟稱因補蓋印章,即將重要印章交付劉博仁使用云云,何其輕忽至此,不似一般代書所為,其所陳與常情不合,已難盡信;參諸系爭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係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簽立者,亦有前開借據在卷可參,斯時系爭二筆土地仍登記予上訴人名下,則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為提供物保之所有權人,應一併擔任系爭借款主債務人之連帶保證人者,與上開習慣相符,即上訴人亦不否認在主債務人呈駿公司位於台南縣關廟鄉之公司所在地與被上訴人襄理見面之事實,核與證人丙○○、乙○○、劉博仁供證會面情節並無不符,且有證人乙○○於本院提出而為上訴人所不爭之員工外出登記簿影本在卷可佐,雖證人丙○○、乙○○、劉博仁等三人對於雙方會面之細節供證,因時日已久,難以記憶詳述,亦屬人情之常,要不影響其三人供證上訴人確於呈駿公司所在地與被上訴人公司員工會商系爭四百五十萬元借據簽立之事實,凡此,俱見證人丙○○及原審同案被告劉博仁供陳:已向上訴人說明須由上訴人蓋用其先前留存之印章,及上訴人親自蓋用印章於系爭四百五十萬元借據者,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上訴人抗辯系爭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上印文係劉博仁盜用云云,核係事後飾卸之責,不足憑採。』(見民事二審卷第五十八頁),駁回告訴人之上訴,告訴人再上訴三審,亦經最高法院九十年度台上字第四九五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經本院更三審調閱本院八十八年度上字第四九0號民事事件全卷查明屬實,並有八十八年重訴字第二五五號、八十八年度上字第四九0號、九十年度台上字第四九五號民事影印卷及判決在卷足憑,顯見告訴人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面額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上擔任連帶保證人為真實。告訴人指訴被告盜蓋其印章,自不足採信。 (六)告訴人提出下列指訴,因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符,仍不足採信: ⒈告訴人指訴:「丙○○稱當天到呈駿公司是要去對保,且有先打電話給甲○○及徐度等語,苟丙○○所言屬實,衡情應會告知甲○○、徐度二人攜帶印章、身分證明文件到場辦理對保始是,然丙○○又供稱林、徐二人未攜帶印章,顯與所述通知對保乙節不符」云云。本件四百五十萬元為增額借款,不須承辦人拿借據予連帶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祇須借據上連帶保證人之印章與原授信約定書內之印章一致,即合乎借款程序。丙○○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呈駿公司,僅查勘借款人呈駿公司營運情形,並確認保證人是否知道有保證的事情,並非去辦理「對保」手續,詳如前述,是告訴人質疑丙○○所證之細節與對保不符,尚不無道理,丙○○於本院更八審亦證述:「這次不算對保,因對保一定要有見簽人。」 ⒉告訴人指訴:「苟丙○○與林、徐二人見面,且係要辦理對保,而林、徐二人均已到揚,對保人員為確認林、徐二人擔任連帶保證人之意願及確認是否為其本人,縱連帶保證人未攜帶印章,按理亦應先要求親自簽名,並告知擔保之金額及擔保責任,同時確認身分始是,惟查丙○○不此之圖,竟未令林、徐二人在對保文件上親自簽名,顯與對保之本旨有違,益見丙○○所述將文件交給被告,被告交由林、徐二人蓋章簽名云云,違反對保之作業常規,甚且與情理有違,殊無足採」。因承辦人丙○○於原審稱之為對保(見一審卷第二十五頁),於本院更四審證稱不是對保(見本院更四卷第0一八頁),致告訴人誤認丙○○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呈駿公司,係去辦理「對保」手續。事實上丙○○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呈駿公司,僅查勘借款人呈駿公司營運情形,並確認保證人是否知道有保證的事情,並非去辦理「對保」手續,詳如前述。是告訴人質疑丙○○所證情節,違反對保之作業常規,顯係誤解臺灣企銀辦理增貸借款之程序。 ⒊告訴人指訴:「告訴人於擔任一百七十萬元貸款之契約保證人欄都親自簽名,足見慎重之一般,而金額高達四百五十萬元及五百五十萬元之貸款,告訴人竟未親自簽名,而委由被告簽名,豈有是理?」臺灣企銀貸款程序,僅第一次辦理借款時須由承辦人「對保」,即承辦人向連帶保證人徵信,拿授信約定書及借據予連帶保證人確認,並在其上簽名蓋章;第二次以後額度內增貸部分,則不須承辦人拿借據予連帶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祇須借據上連帶保證人之印章與原授信約定書內之印章一致,即合乎借款程序,亦即不須有承辦人見證連帶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之所謂「對保」手續,詳如前述。是告訴人認四百五十萬元增貸借款,未經其親自簽名,不合情理,乃質疑臺灣企銀辦理增貸借款之程序。 ⒋告訴人指訴:「丙○○稱其係一百七十五萬元貸款之承辦人,告訴人又係該筆貸款之連帶保證人,則丙○○就應該已見過告訴人,惟本件貸款竟又推說不認識告訴人,才找襄理去云云,益見丙○○辯稱,四百五十萬元貸款對保前未見過告訴人?顯然丙○○說謊!」但丙○○係一百七十五萬元借款之承辦人,而出面向告訴人辦理「對保」手續者,為另一「王明山」襄理,詳如前述,故而丙○○於辦理被告四百五十萬元增貸借款案時,稱不認識告訴人,情理上尚無不合。 ⒌告訴人指訴:「被告劉博仁辯稱印章是告訴人交給他,另又稱印章是告訴人自己蓋,前後矛盾,顯見劉博仁說謊;其次,依劉博仁所述,印章是告訴人所蓋,則告訴人既可以親自蓋章,為何不能由告訴人親自簽名呢?劉博仁說謊,其理至明!」本件公訴人起訴被告盜蓋告訴人之印章,使告訴人成為四百五十萬元增貸借款案之連帶保證人,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一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乃訴追被告有無盜蓋告訴人之印章,至於該連帶保證人之印文已為真實,告訴人質疑是否為被告蓋用,或係被告蓋用之細節,到底被告所稱為正確或是告訴人所言為正確,則為本院按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審究範圍。而本件如前所述,仍不能證明被告有盜蓋告訴人印章。 ⒍告訴人指訴:「如果四百五十萬元及五百五十萬元貸款我知道的話,銀行行員會不認識我嗎?一百七十五萬的貸款我都如此慎重的親自簽名辦理,四百五十萬元與五百五十萬元如此大金額的貸款我會假手他人嗎?由此可知,劉博仁及銀行人員是在我不知情的狀況下,逕行簽名辦理這兩筆貸款案。」但臺灣企銀對於增貸借款四百五十萬元部分,不須承辦人拿借據予連帶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祇須借據上連帶保證人之印章與原授信約定書內之印章一致,即合乎借款程序;且告訴人為執業多年代書,對於有保證責任之銀行印鑑章,有其職業保管之敏感性,依常理而言,其對於印章之使用及保管之注意程度必較一般人為高,如非得其同意,自不會隨意交由他人蓋用,甚或被盜用之可能;告訴人亦未曾舉出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實盜蓋其印章。 ⒎告訴人指訴:「該時土地價值不足借款金額,其不可能同意擔任連帶保證人。」但上開二筆土地,地目為田,於八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以買賣為原因,由原所有權人徐度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告訴人,再於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配偶徐竹葉名下;又前揭二筆土地於八十三年四月十二日以徐度名義設定本金最高限額抵押權一千五百萬元予臺灣企銀,上述農地嗣後由告訴人過戶予被告配偶徐竹葉,再向臺灣企銀借款設定二千萬元之本金最高限額抵押權,其有關登記事宜,均係委任告訴人為「土地登記代理人」經手處理,有土地登記申請書謄本、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等影本在卷可稽(見偵查卷第五至二十頁)。告訴人已參與上述農地之買賣、借款及設定抵押等事宜之程序,自知該農地最少有一千五百萬元至二千萬元之價值。而呈駿公司以該土地為擔保向臺灣企銀借款三筆,分別為一百七十五萬元、四百五十萬元、五百五十萬元,合計為一千一百七十五萬元,以借款時計仍在該土地價值範圍,則告訴人所指該時土地價值不足借款金額,其不可能同意擔任連帶保證人之指訴,即屬無據,亦不能為被告不利之證明。 (七)本院更四審判決固謂:「借款人在借款時取得銀行多餘之空白借據,亦非難事(行員桌上即有擺放),此為知悉銀行貸款業務者所週知之事。因而若被告於八十三年七月間借款時先行取得多餘空白借據,而於八月間再向告訴人借印章佯稱補蓋時,加蓋於多餘借據上,於十二月間再借款,應為極為容易之事。」等語(見本件更四判決第五頁中段)。惟查:⒈遍查卷內所有資料,查無被告於八十三年七月間借款一百七十五萬元時,即先行取得多餘空白借據之任何相關證據,自難徒憑前揭「亦非難事」、「極為容易之事」等臆測之詞,遽予認定被告即涉有偽造文書之犯行,故上開論述有違證據裁判主義及無罪推定原則,自不足取。 ⒉復經本院更五審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善化分行查詢結果,本案四百五十萬元、五百五十萬元二筆貸款,均係呈駿公司於八十三年十二月六日送件申請為經該行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始核准等情,有上開銀行96年8月13日96善化第7029600133號函及客戶授信申請書可稽(見本院更五卷第八十、 八十一頁),申言之,在八十三年七、八月間,被告根本未向臺灣企銀提出四百五十萬元、五百五十萬元借款之申請,自更不可能知悉此部分之增貸借款必獲臺灣企銀核准,更四審判決謂:「若被告於八十三年七月間借款時先行取得多餘空白借據,而於八月間再向告訴人借印章佯稱補蓋時,加蓋於多餘借據上,於十二月間再借款」云云,純屬臆測之詞,,尚非事實,自不足採為被告不利之證據。 (八)本次最高法院發回意旨提出疑點,說明如后: ⒈最高法院發回意旨:「證人丙○○既於民事事件審理時證稱一百七十五萬元貸款係伊承辦,為何又證稱伊在承辦本案四百五十萬元貸款之前,並不認識甲○○?」證人丙○○雖不否認為一百七十五萬元借款之承辦人,而一百七十五萬元借款出去向告訴人辦理對保,即持授信約定書、中長期貸款契約(借據)予告訴人簽名蓋章者,由卷附授信約定書顯示見簽人為王明山(見偵查卷第二十二頁),應為該行襄理王明山,亦為丙○○證實(見本院更六卷第七十六頁),並為告訴人所不爭,丙○○並未參與對保手續,故其證稱在承辦四百五十萬元借款之前,並不認識甲○○等語,尚無不實。 ⒉最高法院發回意旨:「證人丙○○證稱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為辦理本案四百五十萬元貸款事宜,因為伊不認識甲○○,所以請襄理陪同前往台南縣關廟鄉呈駿公司等語,該襄理究係何人? 」查四百五十萬元增貸借款部分,承辦人丙○○及另一襄理乙○○,曾於借款前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呈駿公司,為丙○○及乙○○證述在卷(見本院更一卷第七十三頁、本院更四卷第一一0頁、本院更八卷第九十五、一0三頁),襄理乙○○並於民事事件八十九年六月九日準備程序期日提出其上記載襄理乙○○及辦事員丙○○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四十分,一同外出至關廟鄉「勘現洽客戶」之員工外出登記簿影本一紙為證(見民事二審卷第三十九頁反面、一審卷第四十九頁),證人乙○○於本院更四審亦證稱伊於當天確有去關廟看這家工廠有無營運等語(見本院更四卷第一二九頁),是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與證人丙○○一同前往台南縣關廟鄉呈駿公司之銀行襄理,應係乙○○無疑。 ⒊最高法院發回意旨:「證人丙○○既曾證稱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為辦理本案四百五十萬元貸款事宜,因為伊不認識甲○○,所以請襄理陪同前往台南縣關廟鄉呈駿公司等語,經查,該襄理為乙○○,惟何以乙○○竟證稱伊不認識甲○○?」上開疑點,業據證人丙○○於本院更四審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審理時證稱:「因為在此之前,我當時以為是王明山襄理陪我去的,因為授信約定書是他去對(保)的,且有一筆一百七十五萬元的借據也是他拿去給甲○○簽的,所以我當時以為是王明山襄理陪我去的,才以為是襄理認識,後來查外出登記簿才知道不是王明山襄理陪我去的,是乙○○襄理陪我去的。」(見本院更四卷第一一一頁)。是以,證人丙○○前證稱因為伊不認識甲○○,所以請襄理陪同前往台南縣關廟鄉呈駿公司等語,乃將陪同前往之乙○○誤認為係向告訴人辦理對保,與告訴人有見面之緣之王明山,才說請認識告訴人之襄理陪同,故證人丙○○上開證述純屬其語誤,既為證人丙○○更正,則證人丙○○證述尚無虛偽。⒋最高法院發回意旨:「銀行既採印鑑制度,認章不認人,證人丙○○為何證稱伊在電話通知劉博仁時並無請劉博仁要甲○○帶原來的印章?」此之疑點,即證人丙○○何以通知被告時並無請被告要告訴人攜帶原印鑑章乙節,或係證人丙○○之疏失,或係證人丙○○認為被告應該會通知告訴人攜帶原印鑑章,或係證人丙○○認為當天只是要先確認保證人是否有意願作保而已,保證人若同意作保,可以以後再蓋章,所以未通知告訴人攜帶印章。然不論原因為何,充其量僅係證人丙○○承辦業務上之流程是否妥當之問題,尚不得據此證明被告即有偽造文書罪責。 ⒌最高法院發回意旨:「證人丙○○如係初次見到告訴人要確認其是否同意在四百五十萬元貸款案擔任連帶保證人,為何未核對其身分證件,又如何能確認是否為告訴人其本人到場?」此據證人丙○○於本院更四審審理時證稱:「因為那天是劉博仁介紹的,我有交二張契約書,一張借據(即四百五十萬元)、一張週轉金契約(即五百五十萬元),且交代如果放款要認授信約定書上面的印鑑,特別交代印章一定要跟授信約定書一樣,也跟他介紹的甲○○說印章要跟授信約定書一樣,他們也都跟我說知道,至於那一個人是不是就是甲○○,因為她也沒有反對,也說知道,我才認為她是甲○○。」(見本院更四卷第一一二頁)。是以,證人丙○○未請告訴人出示其身分證件,充其量僅係證人丙○○承辦業務上之經驗不足所致,尚不足認證人丙○○證述之詞虛偽,而採為被告有偽造文書犯行之不利證據。 ⒍最高法院發回意旨:「證人丙○○既證稱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告訴人有到場,何以未當場讓告訴人先行簽名於借據?」而增貸四百五十萬元借款部分,據證人即承辦人丙○○於民事案件證稱:「銀行採印鑑制度,授信約定書第一次一定要本人親自簽名蓋章,以後只要印鑑相符,即可借款。」(見民事一審卷第十八頁反面),於原審證稱:「與授信約定書上的印鑑一致即可放款,所以不核對是否為本人簽名。本件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上甲○○的印章與授信約定書一致。」(見一審卷第二十六頁),證述臺灣企銀增貸承辦手續,不須承辦人拿借據予連帶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祇須借據上連帶保證人之印章與原授信約定書內之印章一致,即合乎借款程序,亦即不須有見簽人見證連帶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之所謂「對保」手續。復據證人即該行襄理乙○○於原審證實本件借款不需要對保,只需告知保證人保證的範圍(見一審卷第四十六頁)。依上開證述,可知臺灣企銀貸款程序,僅第一次辦理借款時須由承辦人「對保」,即承辦人向連帶保證人徵信,拿授信約定書及借據予連帶保證人確認,並在其上簽名蓋章;第二次以後額度內增貸部分,則不須承辦人拿借據予連帶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祇須借據上連帶保證人之印章與原授信約定書內之印章一致,即合乎借款程序,亦即不須有承辦人見證連帶保證人親自簽名蓋章之所謂「對保」手續。是以,證人丙○○未請甲○○當場在四百五十萬元借據上先行簽名,或係承辦人丙○○認祇須借據上連帶保證人之印章與原授信約定書內之印章一致,即合乎借款程序之「認章不認人」制度始然,倘證人丙○○當時予在場之告訴人簽名,本件亦不必勞費多時,惟仍不足據此證明被告有偽造文書犯行。 ⒎最高法院發回意旨:「證人徐度於第一審另證稱:『(問:是否知道對保是多少錢?)我不知道』、『(問:由誰聯絡你去對保?)是我女婿,銀行沒有』、『(問:你女婿是否有要你帶印章前去?)我外孫要我帶印章去』等語(見一審卷第四十三、四十四頁)。就何人通知其到場、有無攜帶印章、有無告知保證人對保金額等情節,輿丙○○之證詞亦不一致,何者為真實,亦待查明?」查坐落臺南縣關廟鄉○○○段一二一九之一、一一三九地號二筆土地,地目為田,係被告所購買,因被告及其妻徐竹葉無自耕農身分,乃於八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先登記有自耕農身分之其岳父徐度名義,於八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甲○○,再於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配偶徐竹葉名下,業如前述,則徐度既僅曾出借名義登記上述二筆農地,及經通知後確實有到場,且本件借款人又是向其借名義登記之被告,則徐度對於保證金額多少未予聞問,尚符合一般社會經驗法則。又被告印象所及,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當天是臨時叫其子去載證人徐度到關廟鄉工廠並沒有告訴他要帶印章。證人徐度於原審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作證時巳高齡七十六歲,且距事件發生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已將近五年半,其記憶力自會隨著年齡、時間而減退模糊,故其證稱:「銀行沒有(通知我去)」、「我外孫要我帶印章去」等語,應係記憶錯誤所致。 (九)綜上各情,公訴人所提積極證據所為之證明並未達到於通常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故不能遽為被告有偽造文書罪之判斷。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被告有公訴人指訴之偽造文書罪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六、原審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本院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公訴人上訴意旨稱原判決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違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珍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8 年 9 月 16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 黃 崑 宗 法官 王 明 宏 法官 蔡 長 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書記官 李 培 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9 月 1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