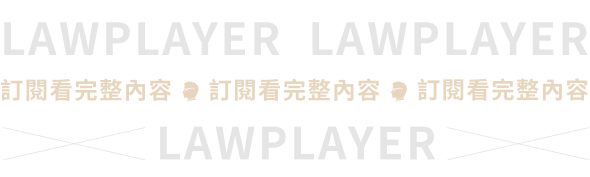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庭(含改制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613號
關鍵資訊
- 裁判案由綜合所得稅
- 案件類型行政
- 審判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庭(含改制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 裁判日期100 年 11 月 17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0年度訴字第613號100年10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白蓮蘋 訴訟代理人 張庭銘會計師 侯委晋會計師 黃詩瑩會計師 被 告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吳自心(局長) 送達代收人 杜思思 訴訟代理人 張翠容 上列當事人間綜合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00 年2 月14日台財訴字第09900546570 號(案號:第0990333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民國9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經被告依據通報及查得資料,發現原告配偶朱順一於94年間將所持有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勤公司)股票8,000,000 股,轉讓予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投信公司)經理之「兆豐國際精選優質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下稱系爭私募基金);另原告與配偶於93年間成立捷磊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捷磊公司),並以原告配偶為負責人。原告配偶於93年8 月間賣出合勤公司股票,同時由捷磊公司買進合勤公司股票;被告認涉有藉股權之移轉,蓄意移轉94年度應獲配合勤公司之股利,報經財政部核准按所得稅第66條之8 規定,核定取自合勤公司營利所得新臺幣(下同)25,600,000元及10,041,772元,併同查獲漏報配偶朱順一執行業務所得1,980 元,歸課核定原告94年度綜合所得總額246,537,785 元,補徵應納稅額12,656,599元,並處以0.5 倍之罰鍰6,328,299 元。原告對核定朱順一取自合勤公司營利所得及罰鍰處分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亦遭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財政部近年來為增加稅收,其行政處分屢屢違反租稅法律主義或增加法所無之限制,迭遭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違憲,如司法院釋字第650 號、657 號、661 號、663 號、673 號、674 號等,其認事用法已失之偏頗,早已喪失稅務工作者之專業性並忘卻公務人員依法行政之職責,而屢屢引起民怨,其主張已不足採。而原告與配偶多年來誠實納稅,自93年至97年的5 年間,累積已自行申報繳納3 億5,358 萬元(93年:7,987 萬元,94年:6,842 萬元,95年:9,710 萬元,96年:6,007 萬元,97年:4,811 萬元),且於87年至99年間,現金捐贈竹苗地區公立學校及政府(包含獎助學金及校務基金、救災專戶等)累積已逾6,281 萬元(87年:1,040 萬元,88年:399 萬元,89年:305 萬元,90年:580 萬元,91年:310 萬元,93年:1,242 萬元,94年:315 萬元,95年:580 萬元,96年:250 萬元,97年:220 萬元,98年:600 萬元,99年:440 萬元),另原告配偶於94年捐贈現金3,000 萬元設立慈善公益之教育基金會,並每年個人再透過基金會現金捐款捐助竹苗地區公立高中獎助學金,截至99年為止,此現金捐助亦累積共計1,780 萬元(94年:210 萬,95年:370 萬元,96年:210 萬元,97年:390 萬元,98年:300 萬元,99年:300 萬元)。此項捐助使得○○○區○段志願之高中,如竹東高中及竹南高中,得以長期資助校內大量之弱勢家庭困難學生完成學業並改善其升學率,藉教育促進社會底層階級之往上移動。另外,原告於100 年6 月20日捐贈所持有之上市公司合勤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500 萬股予國立交通大學,以當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該股票每股收盤價23元計算,該筆捐贈市值約1 億1 仟5 佰萬元。且原告與其配偶從無採用過去坊間流行的捐贈納骨塔,或綠化工程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節稅,誠為一優良之納稅人及慈善家。姑且不論原告及其配偶多年來所繳納的稅額及現金捐贈,僅94年當年度,原告及其配偶之慈善及公益現金捐贈即已達3,582 萬元,早已超出本次被告核定之補稅金額。原告及其配偶絕不會為了此一小小金額而大費周章逃漏稅,本件提訟純求公道。被告不思針對分散及藏匿所得等蓄意逃漏稅者加強查核,反而針對誠實申報納稅者,因取得其資料容易,目標明顯,便處心積慮徵稅,蓄意忽略有利於原告之事實,恣意擴大法律解釋,誠然已有失職守,其主張不足採信,合先敘明。㈡本稅部分: ⒈以私募基金持有合勤公司股份認屬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部分: ⑴被告認定原告配偶係透過私募基金,涉有蓄意安排,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其事實之認定實屬專斷,蓋以私募基金與公募基金同為共同信託基金,皆集合眾人資金以進行證券投資之投資工具,性質相似。私募基金亦需向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報備始得成立及招募,被告所稱該基金係非法成立,實有誤解。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信投顧法)第3 條第1 項、第11條第1 、2 項、第14條第1 項及金管會所制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下稱基金管理辦法)第53條規定,私募基金與一般公募基金相同,其設立及募集皆受到相關法令之規範及監督,並應向金管會申報。其與一般公募基金主要的差別即在於私募基金有應募者之資格及人數上之限制,而一般公募基金則無。另,由於私募基金已在應募者之資格及人數上做某種程度之限制,其應募者應具備有足夠之專業判斷能力並可承受較大之投資風險,故法令准許其投資範圍較一般公募基金為廣。而兆豐投信經理之私募基金,係由兆豐投信依基金管理辦法設立,並依法向金管會申報備查。該私募基金之成立,非可由原告配偶等蓄意安排設立,合先敘明。 ⑵政府於93年底因SARS造成股市投資低迷,為鼓勵大眾投資,增加投資管道而開放私募基金。原告配偶響應政府政策,受兆豐投信招募而應募該私募基金。不料嗣後竟遭金管會證期局人員未徹底了解稅法或徵詢稅務專家意見,逕認系爭私募基金有避稅效果而與開放私募基金意旨不符,故於94年11月私下施壓兆豐投信結清私募基金。惟該局卻於嗣後同年12月7 日始以證期四字第0940005783號函發函通報財政部,請該部查明該基金之受益人是否有逃漏稅事宜。不但未告知該私募基金違法事實認定之證據及法令出處,甚至連最基本的發函通知受處分人該行政處分皆未為之。造成外觀上是兆豐投信自行結清基金而非基於證期局之行政處分,使實際上受處分人無法據以申請訴願。該行政處分顯有重大瑕疪。被告據此有重大瑕疪之行政處分即指原告配偶有逃漏稅捐之情事,實有未洽。 ⑶原告配偶係該私募基金之應募人,非基金之設立人,對該基金亦無控制能力。該基金取得、處分資產等投資決策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下稱信託契約)規定係由兆豐投信決定,原告配偶無置喙餘地。被告所稱原告配偶利用私募基金蓄意安排移轉股利以減少稅捐,顯與實情不符,蓋依基金管理辦法第5 條及由該私募基金之經理公司-兆豐投信與保管機構-建華商業銀行所擬訂之信託契約第13條第3 項規定,兆豐投信對該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享有絕對之自主權。故若基金經理將原告配偶之合勤公司股票於發放股利前予以出售,並購入其他投資標的,亦非不可。倘原告配偶如被告所稱係為安排移轉合勤公司股利予基金以減少稅捐,豈有同意此等條款存在之理。被告於100 年8 月1 日之答辯狀第6 頁及第7 頁以信託契約第18條、第23條及第25條賦予受益人買回受益憑證、更換經理公司及終止信託契約之權利即稱原告可控制私募基金之詞,實為無稽。查系爭信託契約係以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所制定,並經財政部核定之「共同信託基金信託契約條款範本」(下信託契約範本)為藍本所訂,茲將信託契約範本第19條、21條對照及系爭信託契約第23條、25條,即明系爭基金信託契約係以信託契約範本,係為一定型化契約。原告配偶絕無得依契約規定申請買回或終止基金或更換經理公司而即可對該基金有控制能力,被告之詞實為無稽而不足採。 ⑷原告配偶因絕大部分資產為合勤公司之股票,當然只能以該股票進行投資,同時因高科技股票隨產業變化很快,起伏也很大,亟需分散一部份單一資產,為分散風險,將部分合勤公司股票資產交由兆豐投信理財,以分散投資。另原告配偶因係公司經理人身分,處分股票有許多申報及處理限制,且自行大量處分股票也會影響股價波動和市場議論。故原告配偶一次申報轉讓8,000 張合勤公司股票,約佔原告配偶合勤公司股票之10%,交由經理公司投資理財。惟如前述原告配偶對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無決定權,而需兆豐投信事前同意,始得為之。再者,兆豐投信隨時可出售原告配偶所交付之股票並購入其他投資標的,是故原告配偶以該股票做為對價交付兆豐投信進行投資,與一般投資人以現金做為對價交付基金經理公司進行投資實無二致。惟因該基金旋即遭金管會強制要求解散,故無後續投資操作。被告所稱系爭私募基金選擇合勤公司股票為主要投資標的,比例高達99.8%,異於常情…云云,實乃倒果為因、昧於事實之詞,與實情不符而不足採。 ⑸針對兆豐投信系爭私募基金之募集過程,依兆豐投信100 年5 月4 日兆信字第1000000188號函:「三、主管機關於93年底,開放投信業得募集發行私募基金,本公司於94年開始規劃私募基金之募集發行。本基金於94年7 月下旬開始對特定人進行募集,…」等語,足證明兆豐投信於94年7 月下旬始開始進行募集。而原告於94年8 月間轉讓合勤公司股票予基金,實為時間上之自然發展,而非為規避股利所得而為之。且原告係應兆豐投信之募集而應募該基金,而非主動洽詢兆豐投信為之。原告配偶係兆豐銀行之客戶,當初兆豐銀行帶領兆豐投信人員前來招募,兆豐投信對原告配偶表明私募基金係政府所開放之合法之投資管道,且兆豐銀行與兆豐投信均隸屬於官股控制之兆豐金控,故原告配偶始放心參與應募。原告應募基金之原意,實為分散資產及投資並交由基金經理依其專業判斷於合適的時間點做適當的投資決策。其它應慕者亦經兆豐銀行轉介兆豐投信應募,共同特徵為早期投資於合勤公司而累積配有股票,單一資產風險大,亟需藉專業分散投資並分散風險。原告若為規避股利所得,自可在合勤公司發放股利前出售股份,並於六個月之後買回。不可能也無需透過官股持有,而原告配偶無法控制的兆豐投信所設立的私募基金為之。況且兆豐投信按基金管理期間及基金規模收取基金經理費及管理費,官股之兆豐投信也不會不賺基金管理費,而只為幫助他人避稅,成立私募基金後又短期結清,被告稱系爭私募基金應募人間之特殊關係,足證系爭私募基金之成立、募集及投資標的之選定,係基金經理公司與原告配偶等共同精心策劃及安排之結果,實為無稽。 ⑹再者,同基金應募人朱品磊之同事實行政訴訟案件,鈞院亦以100 年訴字第178 號判決勝訴。依該案判決書第24頁倒數第6 行以下『本件據兆豐投信公司98年3 月19日兆信字第0980000161號函稱(見原處分卷第28頁):主旨:兆豐國際精選優質私募基金(以下稱本基金)之成立與終止說明。說明:…二、本基金係於94年7 月29日成立,隨後獲悉金管會相關政策,對有節稅效益之私募基金,認不符合私募基金設立目的,並應儘速協調基金受益人,終止本基金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系爭私募基金經金管會同意,於95年3 月22日結束完成清算(見金管會95年3 月21日金管證四字第095108467 號函,原處分卷第89頁),兆豐投信同性質之私募基金「兆豐國際安得高成長基金」亦於94年11月7 日完成基金清算,有該公司95年4 月14日兆信字第124 號函可憑(見原處分卷第88頁),鑑於兆豐投信公司係兆豐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兆豐金融控股公司係由政府官股所控制,兆豐投信公司並非原告所可控制,兆豐投信公司上揭函示稱「係因金管會要求而結束系爭私募基金」,並無不足採信之理由,不能認定系爭基金係因原告之要求而終止,且原告為受益人,亦無證據顯示其可控制(或勾結)系爭私募基金經理人何時終止系爭基金,可知原告就系爭基金何時終止,並無預期及控制之能力,而原告係於94年9 月9 日、10月11日、11月17日贖回私募基金,系爭基金系於95年3 月22日結束完成清算,因基金終止清算程序(出賣資產)需要時間及有利時機,併就清算所需時間、贖回時序性觀察結果,原告主張其贖回基金係「基於基金經理人要求終止基金」,堪信為真,原告短期內贖回基金,乃迫於時勢,而非其主觀意願,亦難認原告有所得稅法第110 條第1 項「逃漏稅捐」之故意過失。』 ⑺系爭基金收益約定不分配,係信託契約制式約定,非原告配偶所指定,原告配偶無從決定前述信託契約條款內容。考其原意,除係參考當時市場上大多數股票型公募基金亦多約定不分配基金收益,為考量同業競爭,亦比照辦理。另,基金累積收益不予分配亦可擴大基金規模,對基金經理公司而言,不但可增加每年管理費收入,及受益人買回時所收取的買回手續費,亦可擴大可投資資金規模並有利未來市場推廣行銷。本基金成立時點為94年7 月,搜尋當時證券市場有關股票型公募基金之收益分配規定,高達約90%係約定基金收益不分配。若市場上其他不予分配股利之基金未被視為蓄意安排,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被告只因系爭基金同樣不分配股利即稱原告配偶蓄意安排,不當規避納稅義務,實有違行政法平等原則,要不可採。 ⑻原告配偶參與該基金本意即為利用基金之平台以進行投資,雖合勤公司配發股利予基金之階段不課稅(但保留其可扣抵稅額),惟若基金購買其他股票而獲配股利亦不必課稅。此乃因股利本身已課徵過營利事業所得稅,而基金本身為信託,依信託所得導管理論,信託階段獲配股利本即無需再課稅,此為所得稅法及上述93年函令之基金課稅規定所致。被告所稱原告配偶利用私募基金蓄意安排移轉股利以減少稅捐,顯有失公允。再者,私募基金證券交易所得自95年起亦要納入課徵個人基本稅額,非為被告所稱之免徵證券交易所得稅,故股利所得對基金投資人而言僅暫時性免稅,贖回時要依基金所含股利及股票現值計算基金之淨值,基金之受益憑證以基金之淨值計價,基金淨值之增值為受益憑證贖回時之證券交易所得,要納入課徵個人基本稅額。 ⑼政府於93年底開放私募基金募集就知其稅則跟公募基金一樣並允許成立,金融機構依法成立私募基金並招募投資人並無不法。政府如覺得私募基金只有少數投資人,跟公募基金適用一樣的稅則可能太優惠或不妥,應修改私募基金適用之稅則,而不應怪罪金融機構依法而設立之私募基金及應募之投資人。本件如非官股兆豐金控下之兆豐投信偕同兆豐銀行人員前來招募,並稱政府開放合法成立,原告是絕對不會參與私募基金。財政部於94年底發佈基本稅額條例,自95年1 月1 日起私募基金的證券交易所得要納入課徵基本稅額,非如公募基金一樣仍適用證所稅停徵。可見財政部自行修正做法,怎可怪罪之前依法而行之金融機構與投資人,同時依新稅則而行,並不需要強迫依法設立之私募基金結束並清算。私募基金至今仍為合法開放,適用此新稅則,可見財政部也認為私募基金只要依此新稅則繳稅即可。 ⑽依財政部於94年12月28日頒佈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8條:「本條例施行日期除另有規定外,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準此,自95年1 月1 日起,買賣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證券交易所得要納入個人基本稅額課稅(下稱最低稅負)。非被告所稱為證券交易所得適用停徵證所稅。查原告配偶於95年間贖回私募基金受益憑證,原告配偶已依行為時上開規定,於97年11月14日補申報個人所得基本稅額完竣。被告於原告複查申請及訴願時均未對原告此一已依法報稅之事實予以答覆,猶以漏報所得視之,更稱本件為94年度案件,並無該條例之適用。被告之辭實為指鹿為馬,而不足採。 ⑾按現今社會對稅負不公之觀感主要為對富人財富主要來源之資本利得課稅不足,其中兩大資本利得未課稅之來源,一為土地(含房產)買賣僅依公告地價課徵土地增值稅,未依實價課徵買賣差價之資本利得稅;另一為有價證券僅課股利所得稅,未依買賣價差課徵證券交易所得之資本利得稅。私募基金與公募基金之性質類似,適用稅則也一樣,買賣基金受益憑證均為證券交易所得之資本利得,但私募基金因投資人為少數人,雖然政府於93 年 底開放設立私募基金,但旋於94年底頒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明定買賣私募基金受益憑證之證券交易所得要納入個人基本稅額課稅。非如公募基金仍適用證券交易所得停徵證所稅,95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軟體亦已含私募基金證券交易所得基本稅額一項。雖然私募基金仍可保留收益不分配繼續投資,但買賣受益憑證時,所有增值要納入個人基本稅額課稅。政府既已對私募基金所得最大宗之資本利得課稅,被告不得超出法律之要求,稱原告配偶將股所得轉成證券交易所得避稅,被告之舉實已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且嚴重違害法律之安定性而有違人民之期待。 ⑿由於自95年度起,買賣私募基金之證券交易所得應課徵所得基本稅額,故私募基金投資股票獲配股利而不分配,受益人縱可免納營利所得稅(可扣抵稅額也不能取回),但若受益人日後贖回基金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受益人仍需就該證券交易所得繳納所得基本稅額。在受益人投資基金產生巨額證券交易所得的情形下,受益人所需繳納的所得基本稅額將會高於其直接持有股票獲配股利所需繳納的綜所稅,惟如何課稅須依所得類型及行為時之法律,方符合租稅法律主義。今原告配偶處分私募基金受益憑證剛好是虧錢,如果賺錢且資本利得所需繳納的最低稅負較股利所得所需繳納的一般所得稅高,被告此時恐將不會採本案之主張,惟課稅應依所得及行為時法律,被告要不得事後看何者稅較高而擅自追溯採用對被告有利之主張。 ⒀被告認定原告配偶向私募基金買回合勤公司股票以將原應獲配營利所得轉換成證券交易所得。然原告配偶贖回基金係因金管會片面解讀稅法,不敢公開行文要求基金結清,只敢私下施壓兆豐投信,要求自行結清基金,造成外觀上為兆豐投信自行結清。故原告配偶向基金買回合勤公司等股票並贖回受益憑證絕非出於原告配偶之要求。至於當時為何兆豐投信會選擇將合勤公司等股票賣回原告配偶,實係為配合金管會之儘速停止基金運作之要求,若於短期間拋售合勤公司股票,將造成股價波動,非但非為主管機關所樂見,亦可能會影響其他合勤公司股東合法權益,又為配合主管機關要求兆豐投信結清,採原投資方式退回投資,本屬合理之舉。故兆豐投信選擇原投資之方式,即於盤後交易賣回原合勤股票予原告配偶,係出於避免股價波動及退回原投資之考量。被告未查此一事實,又未考量財政部已於94年底頒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私募基金證券交易所得已不適用證所稅停徵,要於95年起納入所得基本稅額課徵,並無避稅空間,原告配偶於95年度處分基金受益憑證並已申報95年度個人所得基本稅額,被告仍對原告加以補稅裁罰,實有失專斷,並已有行政疏失而不足採。且金管會當初發函給賦稅署僅是請該署查明是否有逃漏所得稅之情事,更益證其未有確實之證據。另,被告狀稱原告配偶等人只須要求兆豐投信修改契約分配收益即可讓基金繼續存續。經詢問兆豐投信何俊龍先生,其表示當初金管會並無做上述表示,金管會當時之立場明確,即要求兆豐投信結清係爭基金,且若基金修改契約分配收益即可繼續存續,兆豐投信必然會採用此種方式,因基金若繼續存續,兆豐投信可繼續收取管理費,又無需草草結束基金,徒增應募人之困擾。故被告未了解實情,即信口雌黃。實則本案源於金管會自做聰明,未了解實情即通報賦稅署查核。而賦稅署及財政部採取寧可錯殺一百不願錯放一個之態度,指示被告查核,始造成本案諸多爭議。 ⒁原告申報94年度所得,皆係依法為之,所有所得及扣繳憑單均已申報。至於被告稱短漏報之部分,系爭股權既已移轉予兆豐投信所成立之私募基金,系爭所得之股利憑單亦發予該公司,則按所得稅法應履行申報系爭所得義務之行為人,依法自應為兆豐投信,故原告配偶自無義務就系爭所得為申報。且所得與憑單既非交付原告配偶,自無從履行申報義務,否則將發生同一筆所得由兩名納稅義務人重複申報的重複課稅現象。財政部於94年底頒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私募基金證券交易所得要於95年起納入所得基本稅額課徵,原告配偶於95年度處分基金受益憑證應申報95年度個人所得基本稅額,是原告配偶原申報之所得資料,將95年度處分基金受益憑證所得列報為當年度個人基本所得,應屬合法且正確,無短漏報情事,原處分逕以漏報營利所得視之,應有違誤而不足採。依鈞院所曉諭,茲將係爭私募基金94年8 月底持有之股票種類及股數臚列於證物27號。 ⒂綜上,系爭基金依基金管理辦法成立,並向金管會報備生效,係合法成立之基金。原告配偶係被告知私募基金為合法投資管道,為分散投資故而應募參加該私募基金,對該基金並無控制能力,該基金之投資決策亦由兆豐投信之經理人決定。該基金股利分配政策與市場上其他大部份相同類型之共同基金相同,皆為擴大基金規模而不予分配股利。該基金之結清係應主管機關之要求而為之,非原告配偶主動請求,原告配偶向基金買回原合勤公司等股票亦為減少股價波動,採退回原投資之方式,以避免傷害其他合勤公司股東,以上皆可證明原告配偶非為稅租上之考量而應募該私募基金。且財政部在93年底開放私募基金募集成立,即知私募基金適用稅則與公募基金一樣並允許成立,政府如覺得不妥,應自行修改稅則,不能怪罪依法成立之私募基金與應募之投資人,財政部也確於94年底頒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自95年起對私募基金證券交易所得課稅,無避稅空間,至今私募基金仍是合法開放,適用此新稅則,即是財政部認為私募基金依此稅則繳稅即可,原告配偶業已依行為時之法律,依此稅則條例申報私募基金證券交易所得95年度之基本稅額,被告所稱原告配偶透過私募基金蓄意安排,不當規避納稅義務,其事實之認定已屬專斷,以一己之臆測而對原告予以補稅,實違反實質課稅原則及租稅法律主義而不足採。 ⒉以捷磊公司持有合勤公司股份認屬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部分: ⑴按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規定意旨,對營利事業有藉保留盈餘規避股東或社員之稅負者,所得稅法明定以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為度。被告不此之圖,另闢蹊徑擬援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按實質課稅原則為核課依據,就同一事實對原告另行開徵綜合所得稅,已超過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所規範之法定納稅義務,顯已違稅捐稽徵法第11條之3 :「財政部依本法或稅法所發布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不得增加或減免納稅義務人法定之納稅義務。」規定。況其將實質課稅原則無限上綱應用,置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規定不顧,又違背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使人民負擔法律規定以外的稅負,侵犯憲法賦予人民之財產權,首應指明。 ⑵「自一百年度起,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率者,超過部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係為所得稅法第43條之2 所明定。依前述法條,公司資本與其負債相較,縱然微小,亦僅剔除相關利息支出而未全面否定投資公司之法人人格。被告動輒祭出實質課稅之大旗,而否定私法自治,實已影響法律之安定性而不足採。且公司股利收入因於被投資公司階段已課徵過營利事業所得稅,為避免重複課稅,於公司階段不再課徵營業所得稅,惟此收入仍會併入計算公司盈餘,保留盈餘未分配時要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前手已繳之營所稅和公司部分繳之未分配盈餘稅合為股東可扣抵稅額,公司就盈餘分配股利予股東時,股東仍得就此收入申報綜合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可抵稅,多退少補,股東實然並非永久不必報稅,公司未分配盈餘時,公司仍有已繳納之可扣抵稅額,捷磊公司99年度有就保留盈餘分配股利295 萬元,非全然不分配股利。且其他公司獲配股利而未分配,皆僅加徵10%未分配盈餘稅,未見財政部以實質課稅原則重新核課稅額,被告特別針對原告配偶如是核定,實有違行政程序法第6 條規定之行政行為平等原則而應予廢棄。 ⑶次按被告認原告及其配偶設立捷磊公司旨在避稅,其所謂「證據」,係從資金面稱捷磊公司資本額不足,購買合勤公司股份之資金係由原告與配偶處借款所得,而此等借款經年未予償還,有違一般經驗法則云云。惟按修正後公司法第100 條已刪除最低資本額限制,職是,現行公司法已肯認實收資本額與公司營運狀況及資力無一定關聯性並刪除最低資本額限制,被告孜孜於股本必須大於所取得之資產方謂有資力,實能取得倍數於資本額之資產,顯未深耕現行公司法思潮,以表面思維衡酌此一事實。被告對以借款取得股份所需資金核屬不當作法,不啻限制投資公司僅得以增資方式取得所需資金,有違私法契約自由原則,且再依公司法理中商業判斷準則,若公司治理中之財務操作均須由行政機關核屬正當允否,嗣後爭執再行爭訟手段,恐係浪費司法資源,被告非目的事業主關機關,卻企圖以行政手段干涉公司之財務操作,顯為不當。再查稽徵機關過往案例顯示,公司增資後若有獲配股利或出售土地等取得盈餘之行為,倘再減資將股款退還股東,往往被視為係透過形式上之減資。故若採被告核認應增加資本之做法,反使納稅義務人爾後辦理減資時,有可能被認為是支付股利,從而陷入具高度不確定性的稅務風險。顯見其所敘根本窒礙難行,兼有高度稅務風險,強指此法方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實難令人信服。按單一股東之公司,股東需負擔所有營運資金,其出資究竟多少登記為股本,另多少登記為股東往來借款,對股東出資、股權擁有、負擔盈虧、公司資金利用以及公司或股東之稅負,都無差別。股東也隨時可將借款轉登記成股本。捷磊公司即於99年將借款2000萬轉增資,股本從1000萬增為3000萬元,借款也減少2000萬。依公司法,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有限公司負其責任,股本小風險較小,故單一股東之公司常登記小股本,而由股東借款運作。被告認原告及其配偶設立捷磊公司,資本額不足,資金係由原告與配偶處借款所得,而此等借款經年未予償還,有違一般經驗法則云云,為不符經濟實質原則。 ⑷原告透過捷磊公司持有合勤公司股份,並未規避或減少終局納稅義務。被告單以捷磊公司僅繳納10%保留盈餘稅即據此稱原告短繳稅捐,而未將資本利得與投資公司終將分配盈餘予個人股東之終極稅負列入考慮,不僅與其先前稱不以法律形式為限改按經濟實質為準等語自相矛盾,亦有割裂適用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之虞。依兩稅合一原則,公司階段所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為暫繳,分配股利給個人股東時,公司已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亦將同時分配給個人股東為股東可扣抵稅額,而個人股東則應將獲配之股利併入其所得總額以計算個人綜合所得稅,故最後之稅負將以個人股東本身之稅率為準,公司階段已繳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將成為股東可扣抵稅額可抵繳個人股東之綜合所得稅,多退少補。被告既稱係破除法律形式外觀,按實質經濟效果衡酌本案,則應計算投資公司分配盈餘至原告之終極租稅效果,比較兩者對股東之終極稅負,而不應比較個人股東之稅負與投資公司之稅負。另要比較包含所有所得之終極稅負,即包含股利所得與資本利得之終極稅負,不應只比較股利部份,尤其個人獲配之股票股利以面額計所得,公司獲配之股票股利,非現金,不計入所得,計入資產,增加股票股數並降低平均成本,出售時用以計算資本利得。且所謂投資公司獲配之股利免繳營利事業所得稅,實非免稅,而係因投資公司獲配之股利因在發放公司已繳營利事業所得稅,後手投資公司階段不再重複課徵,保留前手已繳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而分配過來之可扣抵稅額,這是稅法之設計與規定,非為免稅。投資公司會將所獲配之現金股利與買賣股票之資本利得合計為公司盈餘,並分配給股東,也將公司階段已繳之稅,含公司獲配股利時隨附之股東可扣抵稅額,一併發給個人股東,個人股東還是要就此獲配盈餘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 項計入所得總額並依累進稅率計算報繳個人綜合所得稅,並不能規避稅負。惟股東可扣抵稅額可抵稅,個人股東僅須繳差額,多退少補,所以終局稅負還是以個人股東之稅率為準,並未因此減少,被告所做類比實不合理。另被告以40%之個人綜合所得稅率與公司之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相比會製造認知混淆。公司分配盈餘予股東個人時,同時會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是為公司階段已繳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股東只要報繳個人稅率與可扣抵稅額之差額,多退少補。如公司稅率為25%,則公司繳納營所稅後分配予個人股東之可扣抵稅額亦為25%,以綜合所得稅40%稅率之個人股東只要再繳15%之差額,對比個人股東透過投資公司持股,除公司繳納的25%營所稅外,若公司將稅後盈餘分配予投資公司,而投資公司未分配該盈餘予個人股東,則投資公司需就前述獲配之盈餘再加徵10%的未分配盈餘稅,故透過投資公司持股,於股利最終發放予個人股東前,累積已繳納32.5%之稅捐(即25%+ ((1 -25%))×10%)。故個人股東透過投資公司持股於股利最 終發放予個人股東前之稅負,僅較個人股東直接持股而獲配股利之稅負差7.5 %(即40%-32.5%),非為40%與10%之差。假如股東之個人稅率為20%,分配盈餘的話還可退5 %的稅,不分配的話公司扣了32.5%的可扣抵稅額(25%+7.5%未分配盈餘加徵),亦較個人稅率為高。原告透過捷磊公司持有合勤公司股份,依兩稅合一的終極稅負為合併所持合勤公司股票增貶值盈虧之資本利得和獲配之現金股利所產生之稅負,當資本利得高時,此稅負會遠大於個人直接持股之股利稅負,只有資本利得為虧損時稅負較低,故將股票由個人直接持有轉為經過投資公司間接持有,並不會產生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顯不該當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個人或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個人或營利事業……相互間,如有藉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要件,被告自不應援引該條文逕行調整。且其將課稅主體區分成原告與投資公司,刻意忽略終局稅負效果不變乙節不論,單以捷磊公司僅繳納10%保留盈餘所得稅(刻意不提這是在被投資公司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後再加徵),也未合併計算資本利得之稅負以比較總稅負,即據此稱原告短繳稅捐,以圖彰顯其所謂的規避租稅,不僅與其先前稱不以法律形式為限改按經濟實質為準等語自相矛盾,亦有割裂適用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之虞。且其他公司獲配股利而未分配予股東,皆僅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未見財政部以實質課稅原則重新核課稅額,被告特別針對原告如是核定,實有違行政程序法第6 條規定之行政行為平等原則而應予廢棄。茲將原告之投資以下圖示例:B 股利流向C 股利流向個人股東<-----------投資公司 <-----------合勤公司 <------------------------------- A 股利流向 依兩稅合一原則,公司階段之稅皆為暫繳,分配股利給股東時為股東可扣抵稅額,最後之稅負以股東之稅率為準,公司階段已繳之稅為可扣抵稅額可抵稅,多退少補。比較個人直接持有股票和透過投資公司持有股票應以最終稅負為比較基礎始為公平。以上圖所示,A 點代表個人直接持有合勤公司股票並獲配股利,而B 點代表個人透過投資公司持有合勤公司股票並獲配股利。若要比較該二種投資方式,應比較A點 及B 點(含C 點公司階段之暫繳稅)之最終稅負,始為公平。而今被告竟以A 點與C 點之稅負比較,並只比較股利所得之稅負而不含資本利得之稅負,而稱因為C 點只課10%未分盈餘稅(事實上為在合勤公司已繳納完營利事業所得稅後再加徵),即逕稱個人透過投資公司持有合勤公司股票稅負即較低,並以之補稅加罰。對於透過投資公司持股,最終仍需分配股利予個人並由個人納入綜合所得課稅一事,隻字不提,也不提C 點分配證券交易所得之盈餘至B 點時,會將原個人A 點免稅之證券交易所得轉換成B 點之應稅股利所得。此實有類比不當之錯誤,有違當年兩稅合一稅制設計之初衷,並破壞量能課稅之所得稅基本精神而不足採。 ⑸原告配偶於公開市場出售合勤股票並轉而由捷磊公司買入持有,實因原告配偶為合勤公司董事與大股東之身份,每次申報及轉讓股票張數與程序須符合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2 規定,手續繁複,實為不便,並影響市場投資人疑慮,故原告配偶一次申報轉讓出售小部份持股,並由投資公司買入持有,日後有繳稅等資金需求時可隨時處分以獲取資金,因認為股票可繼續增值,還不需用錢時就保有股票以增值,意圖單純,非被告指稱原告蓄意藉由股權不當移轉,以逃漏稅捐。由合勤公司之歷年股利分配表(請詳證物11號)可看出,合勤公司92年以前為成長期,公司每年配發股利以股票股利為主,保留資金以供營運成長之需,股東未獲配現金,但需現金繳納獲配股利所產生之綜所稅。原告配偶為公司大股東,薪資不多,主要所得為獲配之股票股利,沒有現金收,但每年需大量現金繳稅,另每年有大量之慈善公益現金捐贈,必須賣股才能籌此現金。由於原告配偶為公司大股東與主要經理人,每次處分股票有許多申報與轉讓之限制,也會造成市場投資人之疑慮,故於93年一次申報轉讓3,000 張股票於市場賣出,其中2,606 張由原告與原告配偶所設立之捷磊公司自市場買入持有,等於實際賣出股票394 張,所得價款約2,600 萬元,足夠當年資金所需。投資公司持有之股票可隨時處分,不須再申報,也沒有轉讓限制。投資公司持有之2,606 張股票僅佔當年原告與原告配偶所有股票之3.67%,原告配偶實無必要為此小數額大費周章規劃避稅。此純為資金調度之便,個人可視需要隨時隨意小量處分投資公司持有之股票獲取資金,不需要資金時就繼續保有股票增值。 若股票上漲,投資公司出售持股產生資本利得,透過投資公司持有股票之最終稅負將較個人直接持有為高,只有股價下跌,持股虧損時,稅負才較低。原告繼續持有股票即可合理推測係預期未來股票將持續上漲。因若推測未來股票會下跌,則原告不可能繼續持有股票。原告亦不可能為了節稅而保有預期未來會跌價的股票,因為跌價所產生的損失將遠大於可能的節稅效益。被告稱原告配偶移轉合勤公司股票予捷磊公司僅為規避稅負。惟原告配偶自93年移轉系爭股票予捷磊公司,至97年股票價值已損失約56,941,100元〔合勤公司93年年平均股價為70.99 元,而97年年均股價為27.38 元(請詳證物21號),股價跌價所造成的損失為每股43.61 元,即使加上5 年來每一股配發的現金股利7.15元及股票股利市價約14.61 元(過去5 年每股配發股票股利合計0.5337股(請詳證物28號),以97年年均股價27.38 元,股票股利=0.5337股×27.38 元=14.61 元),捷磊過去5 年來持有合勤公 司共虧損了56,941,100元((43.61 元-7.15元-14.61 元=21.85 元×2,606,000 股))〕,與被告審查二科核定93 年至97年原告因移轉合勤公司股票予捷磊公司而減少之應納稅捐計11,860,983元(請詳證物29號)相較,原告配偶股票跌價損失遠大於其所減少之應納稅捐。以一般常人斷不可能為了金額較小的省稅效果而甘冒金額較大之股票跌價損失,故被告之主張殊無可採。 ⑹至於被告所稱投資公司嗣後未有出售股票之舉動,查合勤公司歷年股利分配表,合勤公司93年以後進入成熟期,同時市場氛圍以發現金股利為主,合勤公司所發之現金股利足夠原告及其配偶繳交40%之綜合所得稅和現金捐贈之需求(股利發放有一年之時間差,93年9 、10月發放結算92年之股利,94年發放結算93年之股利,以此類推)。同時合勤公司股票股價逐漸下跌,股價自93年年平均收盤價一股70.99 元一路降至97年的一股27.38 元,原告先不願低價賣股,故未處分投資公司所持有之合勤公司股票。至98、99年,合勤公司不賺錢,配股利甚少或未配股利,但每年之慈善公益捐款屬持續性之捐款,仍有現金捐贈之需求,原是想處分一部分投資公司持有之合勤公司股票以獲取現金,但因股價較之前下跌,唯恐因實現虧損被指為避稅而不敢處分,被告之隨意臆測而不依法行事,實令民眾無所適從。綜上,被告對本案租稅構成要件之判斷及認定,顯非事實,基於自行臆測之基礎對原告補稅並處罰已違反租稅法律主義。 ⑺被告以投資公司與個人就股利所得適用之課稅規定不同,據此認定原告係透過捷磊公司持有合勤公司股份,旨在牟取稅率差異所帶來的租稅利益。然個人持有股票,僅就獲配之股利繳稅,若處分股票產生證券交易所得,目前則為停徵。而投資公司獲配股利雖不重複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保留前手已繳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為可扣抵稅額,但若投資公司處分股票產生證券交易所得,之後投資公司再將包含證券交易所得及股利所得之盈餘分配予個人後,分配之盈餘對個人股東而言,則為應稅之股利所得。對個人而言,以投資公司間接持有股票,取代個人直接持有,將使原本免稅的出售有價證券交易所得,轉化為應稅的股利所得。且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投資公司買賣上市櫃公司股票所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為所得基本稅額之課稅範圍,而個人買賣上市櫃公司股票所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不僅免徵綜合所得稅,亦無需課徵所得基本稅額。按現今社會對股票投資稅負不公之觀感主要為個人持有有價證券僅針對股利課所得稅,未對證券交易所得課徵所得稅。而股利僅為股票獲利之小宗,富人股票投資獲利之最大宗為買賣有價證券交易所得之資本利得。個人透過投資公司持股,在股票增值的情況下,將使原本免稅的大宗出售有價證券交易所得轉成股東之應稅股利所得,最終應稅所得可能遠較個人直接持有股票所獲配之應稅股利所得為高。被告稱此間接持股方式有租稅利益故核屬租稅規避等語,實係片面擷取事實,作出對課稅有利之解釋,但對納稅義務人不利之部分則避而不談,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 條:「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規定,顯失衡平自不足採。茲舉例說明如次。某甲以10元投資A 股票1 股,經過五年後,累積配有10元現金股利及90元股票股利,持股合計增加為10股,假設此時每股市價為100 元,某甲在市場上將其賣出。則其應稅所得僅有現金股利加股票股利共100 元,稅務上的證券交易所得900 元則為免稅。(900 元=10股×100 元/ 股-10元原始投資成本-90 元股票股利(註:因股票股利已課稅,故於稅務上計算證券交易所得時應將已完稅的股票股利列為出售成本))。惟若某甲透過投資公司持股,投資公司於持有期間獲配10元的現金股利及90元股票股利(90元的股票股利非為現金收入,依財會公報第5 號,投資公司僅註記股數增加,為資產之增加,平均每股成本降低,不計為股利所得),並於每股100 元時出售A 公司股票,獲取1,000 元的現金收入並記錄990 元的證券交易利得(990 元=10股×100 元/ 股-10元原始投 資成本)。投資公司並將全部投資收益1,000 元(1,000 元=990 元證券交易利得+10 元現金股利)分配給個人股東,此時個人股東獲配的股利所得1,000 元全部為應稅收入。與上述以個人持有股票僅有100 元股利所得為應稅收入相較,個人透過投資公司持有股票應稅收入增加10倍。 ①情況一: 股價增值 ┌─────────────┬─────────┐│以個人持股 │總應稅所得 │├────┬────────┼─────────┤│股利所得│10元+90元= │ 100元(應稅) ││ │100元(應稅) │ │├────┼────────┤ ││證券交易│1,000元(10股× │ │ │所得 │100元/股)- 1 │ ││ │00元- 100元( │ ││ │稅務會計之投資 │ ││ │成本)=900元 │ ││ │(停徵) │ │├────┴────────┼────┬────┤│以投資公司持股 │ │總應稅所││ │ │得 │├────┬────────┼────┼────┤│ │投資公司階段應稅│個人階段│ ││ │所得 │應稅所得│ │├────┼────────┼────┼────┤│股利所得│現金股利:0元+ │1,000元 │1,000元 ││ │股票股利:0元( │(應稅)│(應稅)││ │股利因所得稅法第│註1 │ ││ │42條規定不計入所│ │ ││ │得課稅,應予帳外│ │ ││ │調整減除) │ │ │├────┼────────┼────┼────┤│證券交易│1,000元(10股× │ 0元 │0元 │ │損益(資│100元/股)-100 │ │ ││本利得)│元(稅務會計上投│ │ ││ │資成本)=900元 │ │ ││ │(停徵) │ │ │├────┴────────┴────┴────┤│註1:投資公司分配盈餘1,000元(=10元股利收入+││1,000元售股收入-10元成本) │└───────────────────────┘惟倘若某甲以個人持有A 公司股票,而股票出售時市價已跌成每股0.1 元,則某甲的100 元股利收入為應稅。惟若某甲透過投資公司投資A 公司,投資公司則因股利收入10元減除證券交易損失9 元(10股×0.1 元/ 股-10元原始 投資成本)後僅有1 元盈餘可供分配予個人股東,故某甲之應稅所得僅有1 元。 ②情況二:股價下跌 ┌─────────────┬─────────┐│以個人持股 │總應稅所得 │├────┬────────┼─────────┤│股利所得│10(現金股利) │ 100元(應稅) ││ │+90(股票股利) │ ││ │=100元(應稅) │ │├────┼────────┤ ││證券交易│1元(售股收入) │ ││損益 │-100元(稅務會計│ ││ │之投資成本)= │ ││ │-99元(停徵) │ │├────┴────────┼────┬────┤│以投資公司持股 │ │總應稅所││ │ │得 │├────┬────────┼────┼────┤│ │投資公司階段應稅│個人階段│ ││ │所得 │應稅所得│ │├────┼────────┼────┼────┤│股利 │現金股利:0元+股│1元(應 │1元(應 ││ │票股利:0元(股 │稅)註2 │稅) ││ │利因所得稅法第42│ │ ││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 │ ││ │課稅,應予帳外調│ │ ││ │整減除) │ │ │├────┼────────┼────┼────┤│證券交易│1元(售股收入) │ 0元 │0元 ││損益 │-100元(稅務會計│ │ ││ │之投資成本)= │ │ ││ │-99元(停徵) │ │ │├────┴────────┴────┴────┤│註2:投資公司分配盈餘1元(=10元股利收入+1元售 ││股收入-10元成本) │└───────────────────────┘③觀察上兩表可知:(1 )透過投資公司持股,將使原本停徵的證券交易所得,轉化為應稅的股利所得,課稅機制已與個人直接持股不同。(2 )透過投資公司間接持有股票,僅在證券交易發生損失時,終局稅負較低。若證券交易產生利得,以投資公司持有股票之終局稅負將較個人持有股票為高。證券交易虧損時,最多僅把股利的盈餘抵銷,少繳股利的稅,但當證券交易有利得時,可能產生多倍於純股利之稅負。原告配偶選擇持有合勤公司的股票,即是預期合勤公司股價會票會增值(包含股數的增加或股價的上漲),而不預期股票貶值。而如前述,在股票增值的情形下,透過投資公司持有股票的最終稅負將較個人持有股票的最終稅負為高,故由此可證明原告配偶透過投資公司持股並非為規避稅負。被告據之指稱系爭事實屬不實安排等推論即屬無據;且系爭事實等同原告選擇將證券交易損益一併納入課稅範圍,租稅客體已與個人直接持有不同,被告僅比較股利所得即稱原告配偶透過投資公司即有節省稅負之效果,實有斷章取義之錯誤。 ⑻投資公司以出售有價證券交易所得與股利所得合併計算總投資獲利為盈餘而就此盈餘課稅,以實質課稅而言,這是最合理的就實際所得課稅。以實際總投資獲利課稅就可能因出售股票之資本利得而大增,也可能因售股虧損而減少,被告不能事後視有無資本利得而推斷應對投資公司之總投資獲利課營利事業所得稅或主張將投資公司所獲配之股利視同直接發放予個人股東以課徵綜合所得稅。股票增值有資本利得時,以投資公司持有股票終局稅負較高。倘現今捷磊公司持有之合勤公司股票增值而有龐大之資本利得,就像握有稍早期之合勤公司股票或現今之宏達電股票一樣,被告必不會主張將投資公司之股票回歸股東個人持有而僅課較低之個人股利所得稅。個人選擇直接持有股票或透過投資公司持有股票,即已選擇不同的課稅方式,何者稅負較高不可預知,但此為不可逆之選擇,個人不能事後視何者稅負較高而回復調整持有方式避稅,被告也不能事後主張何種選擇為避稅。不論以個人或公司持股,選擇持有股票就是相信或期望股票會繼續增值,否則就會賣出股票保有現金,在股票增值的情況下以投資公司持有股票終局稅負較高,而在股票虧損時,則以個人持有股票終局稅負較高,惟此時不可謂以投資公司持有股票即為避稅。由前述證物11號之合勤公司歷年股利分配表及證物21號之合勤公司年平均股價可看出,合勤公司93年以前穩定每年配股,而股價也穩定在60-70元之上,股票是穩定增值,是以原告配偶93年申報轉讓3,000 張合勤公司股票,其中2,606 張由捷磊公司承接,即是認為還不到用錢的時候就繼續由投資公司保有股票繼續增值,要到用錢時才賣。於預期股票增值時仍選擇以稅負較高的方式,即透過投資公司持股,即可證明其未有避稅之企圖。如原告配偶預知股價將來會跌價,就會出售股票,直接保有現金,不會由投資公司再接回部份股票。原告配偶斷不可能為了節稅而保有預期未來會跌價的股票,因為跌價所產生的損失將遠大於被告所稱可能的節稅效益。故原告配偶持有合勤公司的股票,即是預期合勤公司股價會上漲,而不預期股價會下跌。而如前段所述,在股票上漲的情形下,透過投資公司持有股票的最終稅負將較個人持有股票的最終稅負為高,故由此可證明原告透過投資公司持股並非為規避稅負。 ⑼由於原告配偶選擇以投資公司間接持有股票時,可以合理預期稅負將較個人持有高,則被告稱其動機顯在逃避稅捐自非允當,被告據之指稱系爭事實屬不實安排等推論即屬無據;且系爭事實等同原告選擇將證券交易損益一併納入課稅範圍,租稅客體已與個人直接持有不同,被告不宜片面僅就股利所得衡酌。 ⑽原告94年度申報綜合所得稅總額約2 億1 千萬元,被告核定增加投資公司股利所得約為1 仟餘萬元,經核算該股利所得僅占原告94年度申報所得總額4.4 %,此比例稍高係因為原告配偶於94年度捐贈現金3000萬元成立公益慈善之教育基金會,致當年申報所得較低所制,原告配偶倘如被告所稱,藉由股權移轉,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原告配偶何需僅為移轉佔所得總額不到5 %之所得而如此大費周章?是原告配偶移轉股份目的乃係一次申報轉讓股份之便利性,乃事實所然,未有規避稅捐意圖。被告以其他投資公司透過作帳造成虧損之案例,臆測原告配偶透過捷磊公司之投資行為即有規避規稅捐之事實,並巧用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抽象概念加以涵攝本案件,出發點僅純粹為課徵稅捐為目的,實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36條證據調查原則而不足採。 ⑾捷磊公司93年度至97年度間,僅93年度結算申報帳載自結數為虧損外,其他年度均有盈餘。93年度至9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全年所得額分別為-1,024,404 元、1,418,454 元、1,483,077 元、4,415,952 、2,226,001 元。至於被告稱投資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為0 元,實因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而捷磊公司以投資控股為本業,獲配國內公司之股利所得,依該條文規定,本不計入捷磊公司之所得額所致,非原告配偶可蓄意規避或可自由選擇。蓋此規定實因公司股利收入於被投資公司階段已課徵過營利事業所得稅,為避免重複課稅,於公司階段不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惟此收入仍會併入計算公司盈餘,保留盈餘未分配時,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規定要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公司就盈餘分配股利予股東時,股東仍需就此收入申報綜合所得稅,並非免稅。 ⑿捷磊公司於保留盈餘未分配時皆已繳納未分配盈餘稅額,至於被告於答辯書指稱捷磊公司93年至97年之未分配盈餘小於同期間原告配偶轉正後之營利所得,顯有應納稅負減少之實益…等語,實為似是而非,故意混淆視聽之辭而不足採。按營利所得含可扣抵稅額而未分配盈餘不含,兩者已有不同,另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第2 項及財會準則公報第5 號第47段規定,若投資公司獲配公司之股票股利,投資公司帳上只會註記股數增加,不作任何分錄。惟若個人獲配公司之股票股利,需依股票股利面額(即一股10元)計算營利所得。由於合勤公司93年至96年每年皆有分配股票股利,而該股票股利依上開會計準則,無需計入投資公司之損益及未分配盈餘,故捷磊公司93年至97年帳上的未分配盈餘小於同期間原告轉正之營利所得,實因稅法及現行會計準則之規定所致。惟捷磊公司獲配股票股利雖只註記股數增加,不作任何分錄,但因股數增加,總持股成本不變,故捷磊公司帳上所持有之合勤公司股票每股成本會下降,未來若捷磊公司出售合勤公司股票,將會增加捷磊公司的證券交易所得及所得基本稅額。倘未來捷磊公司將證券交易所得分配給個人股東,個人股東仍需就獲配股利計算營利所得並繳交綜合所得稅。故雖捷磊公司帳上的未分配盈餘小於原告配偶轉正後的營利所得,僅為股利不含資本利得部分,最多也僅生遞延稅負的效果,不會有減少應納稅負之實益。且該遞延稅負之效果亦是稅法設計之本意。故被告所稱實乃似是而非、混淆視聽之辭而不足採。捷磊公司93年持有合勤公司股票2,606,000 股,後賣出30,000股,經歷年獲配股票股利註記股數增加,至97年累積有股票3,996,500 股,如股價維持不變,處分會有大量之證券交易所得列入公司盈餘並增加捷磊公司的所得基本稅額,此盈餘分配給個人股東,個人股東需就獲配之大量資本利得轉換而來之投資公司股利繳交綜合所得稅,被告必不會堅持原告只要回歸個人持股僅就獲配之合勤公司股利繳稅。歸根究底,原告以投資公司持股,因產業變遷,合勤公司股價下跌,捷磊公司持股是處於虧損狀態,沒有產生較高之稅負,被告就回溯稱原告以投資公司持股為避稅。設若合勤公司股價這兩年有到50元以上,原告必不會與被告打官司,直接把捷磊公司持股都賣了,產生資本利得,然後詢問被告要以何種方式繳稅。查捷磊公司持股之盈虧,為其投資控股本業之盈虧,並無藉合併其他營業操縱「帳列虧損」之情事。原告配偶從無故意以坊間常用之併購虧損公司及虛增費用等會計手法操弄捷磊公司損益,以達到免納稅捐之意圖;原告配偶投資之捷磊公司目的,本於初衷仍係一次申報轉讓股份之便利性,實應再次敘明。被告怠以審查上開案情之諾大差異,強指原告配偶亦可透過會計操作手段規避稅捐,以莫須有之事實冠以原告,屬魚目混珠之舉,實不可採。 ㈢罰緩部分: ⒈原告因被告逕行調整增加之所得額,無申報可能,屬客觀上事實不能,不應適用所得稅法第110 條第1 項規定: ⑴按司法院釋字第657 號解釋理由書揭櫫課稅要件應屬明確,方符租稅法律主義。倘課稅主體在經濟實質上與法律形式上發生不同者,仍應有法律明定納稅主體,始符合法治國精神,此觀我國所得稅法第3 條之2 及第3 條之4 之規定,立法者即對信託所得於形式上與實質上之不同享有者之納稅方法做出規範,並明確課予各自該當之申報義務即可得知。反觀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則對於申報義務人之規定闕乏。 ⑵被告主張本件適用所得稅法第110 條第1 項之規定,被告應先提示所得稅法或其釋令,有關私募基金及投資公司獲取之所得,應直接歸屬為基金投資人及投資公司股東之所得並由投資人及股東申報之相關規定,方得核認原告配偶有未盡申報義務之事實。然被告係依據實質課稅原則認原告配偶有此所得,並未提出將系爭所得直接歸屬為原告配偶所得,並應申報之稅法法令,即擴大適用實質課稅原則,又在納稅方法要件不明確時,課予原告配偶申報義務並據此稱違反所得稅法第110 條之規定,亦違反處罰法定主義禁止類推適用原則。 ⑶被告指稱短漏報之營利所得,系爭股權既已移轉予兆豐投信所成立之私募基金及捷磊公司,按所得稅法應履行申報系爭所得義務之行為人,依法自應為兆豐投信及捷磊公司(另查兆豐投信公司及捷磊公司確已申報此一所得),合勤公司亦係將股利憑單發予前開納稅義務人,然所得與憑單既非交付原告之配偶,則原告之配偶自無從履行就系爭營利所得為申報之義務,併予指明。是母法既無明文規定應予處罰,而原告之配偶依法就系爭所得亦無申報義務;在當年度申報時,又已履行法定應有之揭露說明義務,並無隱瞞稽徵機關或使其陷於錯誤的情形,即非屬於違章短漏報行為,則被告逕予裁處罰鍰之舉,其正當性即有欠缺,自應予以撤銷。 ⑷原告配偶之私募基金受益憑證為於95年贖回,依行為時法律已將證券交易所得納入95年度基本所得額申報基本稅額,未有短漏報。 ⒉對依實質課稅原則予以調整補稅之案件,所得稅法既未課予納稅義務人有作為義務,復未明定應予處罰,按處罰法定主義,被告不應恣意擴張解釋以違反所得稅法第110 條第1項 而逕予處罰。 ⑴按諸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行政罰法第4 條及司法院釋字第313 號、394 號解釋,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以法律明定或明確授權處罰時,始得加以處罰。國內學者洪家殷亦主張:「人民對於處罰之要件及處罰之種類必須從法律中即可預見,而不是直到依據法律而訂定之命令始可知悉。」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僅規範依實質課稅原則加以調整補稅,並未規定稅局可以於補稅後再加以裁罰,雖該條文之立法理由提及裁罰之規定,惟立法理由僅係對法條之解釋,僅有法律解釋之功能,要不能以立法理由取代法條本身而引以為裁罰之授權依據。 ⑵次按法務部95年6 月法律字第0950018449號函:「…惟若與各相關稅法處罰規定之構成要件不符,稅捐稽徵機關倘僅以抽象之實質課稅原則加以處罰,即與前開處罰法定原則相違,難認適法。」另參照學者陳清秀之見解:「在實質課稅原則下,納稅人按照所選擇的法律行為方式申報繳納稅捐,可能嗣後被認定為法律行為類型或方式之濫用(稅捐規避)而加以否認,並予以調整補稅,致嗣後發生不可預測的稅捐負擔,蒙受無法回復的損害。…因此,稽徵機關對於濫用法律行為方式的否認,必須加以嚴格控制,尤其是否濫用法律形式,更應審慎查核其有無合理的正當理由,不宜草率認定。在構成法律行為方式濫用的情形,稽徵機關或許可以調整補稅,但應考量其原則上屬於稅捐規避行為,不宜動輒認定為逃漏稅行為,遽以科處罰鍰。」末按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2150號判決略以:「…罰鍰部分…在目前學理上已接受『稅捐規避』與『稅捐逃漏』在法律概念上與法律效果上之區別,前者之定義為:在不隱瞞或偽造事實之情況下,濫用私法之形成自由或稅捐稽徵機關之錯誤法律見解,而運用法律形式上之安排,意圖減免稅捐。而其法律效果則是:運用實質課稅原則,將扭曲不自然之私法安排,透過稅法之獨立觀點,將之矯正成『符合經濟實質』之原始面貌,而對之加以補稅。但因為其無違反誠實義務,所以也不對之課予漏稅罰。後者則是違反誠實義務,隱瞞及偽造事實,而意圖逃稅,其法律效果則為『補稅並課予漏稅罰』。…」申之,「稅捐規避」與「稅捐逃漏」構成要件及效果各有所別。被告既先將事實認屬「租稅規避」,後續卻以「稅捐逃漏」裁罰,顯示其核認結果前後矛盾,實不足採。綜上可知,稽徵機關尚不得以依實質課稅原則調整之結果為處罰依據。 ⒊縱本案依實質課稅原則應予以調整補稅,惟原告配偶行為時未有相關解釋函令明定為屬違反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而應加以處罰,依司法院釋字第394 號並考量行政罰法之行政命令之授權明確性原則,亦不應對原告加以裁罰。 ⑴「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予以裁罰性之行政處分,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處分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應由法律定之,法律雖得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惟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必須具體明確,然後據以發布命令,方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係大法官釋字第394 號解釋文所明示。另,參照國內學者洪家殷之見解:「二、行政命令之授權明確性此外,若有明確之授權時,此種處罰亦得出於法規命令或自治規章,故明確性之要求,不只在授權規範本身,也及於被授權之規範。此涉及行政罰空白構成要件之容許,故在授權其他法規訂定構成要件,同樣亦須十分明確,因此,此項要求也會延伸到相關規範,亦即被授權訂定之法規,皆須符合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⑵依上述大法官解釋文及學者見解,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予以裁罰性之行政處分,雖得以命令為補充規定,惟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必須具體明確,然後據以發布命令,方符憲法第23條之旨意。由於原告之配偶於應募該基金及投資捷磊公司時,並未有任何解釋函令或行政命令明確指出該等投資行為違反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而應加以處罰。故依上開大法官解釋文及行政罰法之行政命令之授權明確性原則,亦不應對原告加以處罰。 ⒋原告配偶並無故意或過失之責任,而自不應受罰。 ⑴按之行政罰法第7 條之立法理由,行政罰法公佈施行後,基於有責任始有處罰原則,違反秩序行為人之處罰,須以其主觀上有可歸責性為要件。若行為人於行為時因未有法律明確規定某項行為已違反行政義務,致行為人無法預知其行為將有違反行政義務之可能性,由於該行為人主觀上並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而無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此時該行為人則不應受罰。 ⑵被告於訴願決定書第3 頁及第13頁引用之財政部98年7 月7 日台財稅字00000000000 號及97年4 月30日台財稅字第09700196750 號解釋令(下稱98年函令及97年函令)對原告加以補稅並處以裁罰。惟上述二則解釋令皆為原告配偶行為後財政部始為發佈,原告配偶於行為時並無法預知其投資行為有違反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之實質課稅原則之情事,更遑論會受到裁罰。依行政罰法第4 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原告及其配偶實不應受罰。 ⑶次按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258 號判決:「觀察上開規定之裁罰構成要件以發生漏稅之實害結果為必要,係屬漏稅罰性質……,漏稅罰以發生實害為必要,於責任要件上並無過失推定之適用,仍須由稅捐機關就申報義務人之行為符合處罰構成要件,包括客觀上事實合致及主觀上具有故意過失負證明責任。……」(請詳證物16號)職是,被告認定原告之配偶行為屬「租稅規避」之行為,並未有其他證據可進一步證明,原告之配偶未申報之情形即有逃漏稅之故意存在,不得再論以漏稅之裁罰,本屬當然之理。 ⒌行政法規之解釋或適用上錯誤可因無期待可能性而構成阻卻責任事由: ⑴按司法院釋字第685 號解釋林錫堯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茲以行政法規複雜性、行政法法理具有高度爭議與不斷演進等特徵,行政法上之法律見解不僅難免有『見仁見智』之不同,亦常見有『昨日之是,今日之非』之情形,呈現高度不穩定之法律狀態,執法機關本於依法行政,取其確信之法律見解而為行政決定或行政裁判,固可發揮逐步釐清或導正之功能,而貫徹依法行政原則,但亦不免使人民之權益在法律見解之探討與演變過程遭受不利,因而有依信賴保護原則予以保護之必要。然就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施予行政罰方面而言,如行政法規規定不明確而於法規之解釋與適用上容許有不同見解(如學說上有不同見解、法院判決有採不同見解等),且行政實務或司法實務尚未形成通說,亦尚無行政釋示、判例、大法官解釋或以其他方式表達(如決議、行政慣例等)可作為標準而據以遵行之見解,甚至雖已形成相關見解,但於某種情形,法規之解釋與適用上仍有其不明確之處,而就此不明確處亦容許有不同見解,於此等情形下,行為人於行為時採取某一見解而為其行為時,如其所持見解在法理說明上具有相當合理之理由,縱該見解偏向行為人之利益,行為人選擇該見解,乃屬合乎人性之舉,故雖嗣後行政釋示、判例、大法官解釋或以其他方式形成之見解,認為應採另一不同見解,從而認行為人行為時所採之見解有誤,進而認定其行為係屬違法而予以糾正,此固屬依法行政原則之貫徹。但因行為人行為時有上述『法律見解錯誤』之情形,對行為人而言,避免此種『法律見解錯誤』而採取合法之見解係屬無期待可能,亦即對行為人之合法行為無期待可能,自應認有『超法定之阻卻責任事由』之存在。是故,行為人雖依行政罰法第8 條前段:『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之規定,不能因此種『法律見解錯誤』而認定其無故意或過失,但仍因其具有阻卻責任事由,而不受行政罰。綜上所述,簡約敘述如下: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處罰,倘因行政法規之解釋或適用(涵攝)容有不同見解,而司法或行政實務上尚無大法官解釋、判例、行政釋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可資遵行之見解,且行為人於行為時所依據之見解於法理上具有相當合理之理由者,縱行為後司法或行政機關認另一見解為適法,仍可因對行為人之適法行為無期待可能而阻卻其責任。」 ⑵職是,被告雖逕行認定原告配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而為處罰,然因原告配偶於行為時,對於移轉股權於投資公司或私募基金,司法或行政實務上尚無大法官解釋、判例、行政釋示可資遵行之見解,且原告配偶之移轉股權行為乃係依據法律所為,縱嗣後司法或行政機關認另一見解,仍為適法。被告雖主張財政部98年函令已明示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範圍,並得逕行調整原告配偶所得額。然上開函釋係屬原告配偶行為後所發布,原告配偶行為乃基於信賴行為時之法律,本為適法行為,縱使被告認原告配偶行為違法,因無期待可能而本得阻卻其責任,被告所為裁罰性之行政處分,顯屬違法而應予撤銷。 ⒍退步言,被告以實質課稅為由拒絕承認捷磊公司法律主體而對原告補稅並加以處罰,惟於計算本稅及罰鍰金額時又以捷磊公司與原告為不同主體,主張捷磊公司已繳納之未分配盈餘稅不得抵減補稅金額,而逕以合勤公司發放之股利及股東可扣抵稅額設算原告補稅及罰鍰金額,實已違反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台財稅字第10000076610 號函令之規定及實質課稅原則,並顯有恣意割裂法律適用之情形而不足採。原審判決未予指摘,實有行政訴訟法第243 條第1 項判決法規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事由,而應予以廢棄。 ⑴「核釋個人簽訂孳息他益之股票信託相關課稅規定:一、委託人經由股東會、董事會等會議資料知悉被投資公司將分配盈餘後,簽訂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或委託人對被投資公司之盈餘分配具有控制權,於簽訂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後,經由盈餘分配決議,將訂約時該公司累積未分配之盈餘以信託形式為贈與並據以申報贈與稅者,該盈餘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尚非信託契約訂定後,受託人於信託期間管理受託股票產生之收益,則委託人以信託形式贈與該部分孳息,其實質與委任受託人領取孳息再贈與受益人之情形並無不同,依實質課稅原則,該部分孳息仍屬委託人之所得,應於所得發生年度依法課徵委託人之綜合所得稅;嗣受託人交付該部分孳息與受益人時,應依法課徵委託人贈與稅。二、上開信託契約相關課稅處理原則如下:(一)綜合所得稅部分:委託人未申報或短漏報前開孳息者,稽徵機關計算委託人應補稅額及漏稅額時,除該所得及相對應之扣繳或可扣抵稅額應自受益人轉正歸戶委託人外,尚應扣除以各受益人名義溢繳之稅額,加計以各受益人名義溢退之稅額,再據以發單補徵並依所得稅法第110 條規定辦理;各受益人申報地稽徵機關不另就該筆所得之溢繳稅款或溢退稅款作處理。…」係為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台財稅字第10000076610 號函令所明定(下稱100 年函令)。 ⑵上開函令係規範有關納稅義務人於知悉公司分配股利後始以股票設立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之信託,而稅局依實質課原則將嗣後公司分配予信託的股利視同發放予委託人並課徵綜所稅之規定。依上開函令精神,稅捐稽徵機關於計算委託人應補繳之稅額時,除應扣除該股利相關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外,亦應扣除信託受益人因該筆股利所得所繳納之稅捐,再依所得稅法第110 條規定辦理。且稽徵機關不再另就信託受益人因該筆所得所繳納之稅捐作退稅之處理。 ⑶依被告審核二科審查報告,被告以合勤公司95年度發放予捷磊公司之股利總額10,041,772元設算為原告之股利所得,乘以原告綜所稅稅率40%並減除合勤公司發放之股東可扣抵稅額451,692 元計算原告補稅金額為3,565,017 元,並依該補稅金額之0.5 倍計算罰鍰1,782,508 元。 ⑷惟捷磊公司於獲配合勤公司股利後,已因該筆股利繳交94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稅451,692 元。依上開100 年函令之精神,被告縱依實質課稅原則設算該筆股利所得應補繳金額,亦應扣除因該筆股利而繳納之所有稅捐,包含股東可扣抵稅額及捷磊公司因該筆股利而繳納之未分配盈餘稅。且被告既然以實質課稅為由拒絕承認捷磊公司法律主體,而主張合勤公司發放予捷磊公司之股利應歸屬原告個人之所得,並對原告補稅並加以處罰,則被告又主張因捷磊公司與原告為不同法律主體,故捷磊公司因該筆股利所得而繳納之未分配盈餘稅不得用以抵減原告之補稅金額,實為前後矛盾,並為選擇性課稅,違反實質課稅原則並顯有恣意割裂法律之適用而不足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之請求,於情有理,於法有據等語。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配偶朱順一於94年間,將持有合勤公司股票轉讓予兆豐投信經理之系爭私募基金。另查獲原告與其配偶朱順一以資本額10,100,000元,於93年7 月14日成立捷磊公司,朱順一係合勤公司負責人,其分別於93年8 月5 日及9 日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以每股67元及70.5元賣出合勤公司股票1,500,000 股及1,500,000 股合計3,000,000 股,金額合計206,250,000 元。捷磊公司亦於93年8 月5 日及9 日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以每股67元及70.5元買進合勤公司股票1,117,000 股及1,489,000 股合計2,606,000 股,金額合計179,813,500 元。嗣捷磊公司自合勤公司分別獲配93年度至97年度股利為8,342,802 元、10,118,839元、11,021,069元、6,261,687 元及879,623 元。捷磊公司支付93年間購入合勤公司股票股款係向原告及配偶分別借款51,000,000元及131,000,000 元,並帳列股東往來,嗣後再以自合勤公司獲配股利償還。原查以原告出售合勤公司股票,涉有藉股權之移轉,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情事,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規定,報經財政部核准後,按原告實際應獲配之股利核定調增94年度營利所得10,041,772元,通報被告所屬新竹市分局歸課原告綜合所得稅。 ㈡有關轉正原告配偶之兆豐國際精選優質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營利所得: ⒈有關所得人以私募基金規避稅負,經稽徵機關報經財政部核准按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規定,依實質課稅原則,轉正其營利所得。與本件案情相同之訴外人朱品磊、朱品潔、朱好一、徐麗玲及陳鳳等私募基金受益人對轉正渠等之營利所得並無不服,僅對罰鍰提起行政救救濟,其中朱好一罰鍰案件,已於100 年1 月27日復查階段行政救濟確定。朱玲對私募基金受益人轉正之營利所得及罰鍰不服,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561 號判決駁回,復經最高行政法院100 年度判字第930 號判決駁回確定。合先陳明。 ⒉查合勤公司於94年6 月3 日召開股東會決議發放股利股息;兆豐投信公司於94年7 月26日經理系爭私募基金,契約第3 條明定應募人不得超過35人,而實際應募人僅有朱順一(合勤公司之董事長)、原告(朱順一之配偶)、朱好一(朱順一之弟)、李麗雯(朱好一之配偶)、朱品潔(朱順一之女)、朱品磊(朱順一之子)、朱玲君(朱順一之兄朱忠一之妻)、徐麗玲(合勤公司之職員)、陳鳳(合勤公司之職員)及白常生(朱順一之妻舅)等10人,渠等亦為系爭私募基金受益人,彼此為手足、親屬、長官部屬關係,既為合勤公司股東、亦為私募基金之受益人,足見私募基金實為合勤公司所掌控之基金,渠等在明知合勤公司獲利分配股息之情形下,於94年7 月至同年8 月17日(股利發放基準日為94年8 月18日)移轉持有合勤公司股票合計16,435,000股予兆豐投信公司,另再申購系爭私募基金,由私募基金94年9 月29日取得合勤公司配發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再由原告配偶事後向私募基金買回合勤公司股票9,079,000 股,實係將合勤公司原應分配予原告配偶之股利、股息透過私募基金回歸原告配偶之行為。 ⒊原告配偶於合勤公司配發股利前,轉讓該公司股票予私募基金,並為該基金之受益人,該基金因而獲配合勤公司發放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然因該私募基金約定,不分配收益予受益人,僅將收益併入基金資產作為投資標的;故原告配偶等原應獲配股利所產生之所得稅負,由私募基金參與公司股票除權、除息,轉由無須負擔營業所得之私募基金受益人,所獲配之股利毋須計入受益人之營利所得,達成規避稅負目的。是原告配偶顯透過移轉股權申購私募基金,以股權形式移轉之安排,將合勤公司股份移轉予私募基金,再向私募基金買回自合勤公司獲配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之股票,實際達成股東獲配股利之目的,其交易顯為蓄意安排於除權除息前出售股票,為規避個人營利所得,減少納稅義務。 ⒋次查系爭私募基金信託契約第15條規定,得投資之標的,包含公司股票(含上市櫃及未上市櫃)、債券(含政府公債、公司債等)、臺灣存託憑證及其他各種受益憑證,其種類及數量眾多,且投資標的選擇,關係基金經營成績之良窳,進而影響基金之淨值。系爭私募基金自94年7 月29日成立至95年3 月22日清算止之投資組合有 ┌─────┬───┬───┬────┬───┐ │投資組合 │股數 │投資股│金額 │投資金│ │ │ │數百分│ │額百分│ │ │ │比(%│ │比(%│ │ │ │) │ │) │ ├──┬──┼───┼───┼────┼───┤ │1301│台塑│13,000│0.0691│645,316 │0.0527│ ├──┼──┼───┼───┼────┼───┤ │1303│南亞│13,000│0.0691│523,359 │0.0427│ ├──┼──┼───┼───┼────┼───┤ │2002│中鋼│16,000│0.0851│446,116 │0.0364│ ├──┼──┼───┼───┼────┼───┤ │2323│中環│3,000 │0.016 │41,620 │0.0034│ ├──┼──┼───┼───┼────┼───┤ │2325│矽品│3,000 │0.016 │100,649 │0.0082│ ├──┼──┼───┼───┼────┼───┤ │2350│環電│3,119 │0.0166│44,422 │0.0036│ ├──┼──┼───┼───┼────┼───┤ │2391│合勤│18,735│99.658│122,706,│99.790│ │ │ │ │9 │046 │4 │ ├──┼──┼───┼───┼────┼───┤ │6505│台塑│13,000│0.0691│766,479 │0.0626│ │ │化 │ │ │ │ │ ├──┼──┼───┼───┼────┼───┤ │ │合計│18,800│ │1,225,27│ │ │ │ │,019 │ │4,007 │ │ └──┴──┴───┴───┴────┴───┘ 由上表可知,系爭私募基金投資合勤公司股票比例高達99.66 %、投資金額高達99.79 %,又參以系爭私募基金應募人間之特殊關係,足證系爭私募基金之成立、募集及投資標的之選定,係原告配偶等基金受益人所策劃及安排之結果,對系爭私募基金有絕對之控制權。末查,系爭私募基金信託契約第18條、第23條及第25條規定,上開約定賦予受益人買回受益憑證、更換經理公司及終止信託契約之權利;原告主張無法控制私募基金之說詞,顯與事實不符,所述委無足採。⒌查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明定自95年1 月1 日施行,本件為94年度案件,核無該條例之適用。又查原告配偶在系爭私募基金法律關係終止結算(95年3 月22日)後,對其應屬合勤公司分配股票、股利之實質受領人,也知之甚詳,其於95年5 月1 日至5 月31日法定綜合所得結算申報期間,自應誠實申報,乃竟猶將上開營利所得匿而不報。原告自不得以事後95年實施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主張證券交易所得稅非停徵,及卸免誠實申報義務。又原告配偶於94年12月12日縱有買回系爭私募基金(詳卷編第136 頁),私募基金雖有課徵證券交易稅,然屬免徵之證券交易所得。綜觀原告配偶應募系爭私募基金之目的,仍係規避所得稅法甚明,原告主張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為不足採。 ⒍兆豐投信公司係因無法對主管機關陳明其成立基金之投資策略及營運方向,而遭質疑上開私募基金之目的唯在為原告配偶等特定人避稅而已,與開放私募基金宗旨不符,要求兆豐投信公司協調清算或修正契約;原告配偶等人亦可修正契約分配收益,然此與渠等應募系爭私募基金規避稅負之目的相違,始有終止契約之情。而本件原告配偶原應受獲分配股利所產生之所得稅負,卻轉由無須負擔營業所得之私募基金受益人,所獲配之股利毋須計入受益人之營利所得,可見已達成原告配偶規避稅負之目的。 ⒎被告依查得資料,以原告配偶藉股權移轉,不當規避或減少94年度原應獲配之股利納稅義務之情事,依所得法第66條之8 規定,報經財政部核准後,按原告配偶實際應獲配之股利調增94年度營利所得25,600,000元,歸課原告綜合所得並無不合。 ㈡有關轉正原告配偶之捷磊公司之營利所得: ⒈原告配偶係合勤公司負責人,該公司於93年5 月27日股東會決議分配盈餘,盈餘分配基準日93年8 月11日,原告旋於配發股利前與配偶朱順一於93年7 月14日成立捷磊公司,資本額10,000,000元,原告配偶分別於93年8 月5 日及9 日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賣出合勤公司股票計3,000,000 股,捷磊公司同時於93年8 月5 日及9 日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買進合勤公司股票計2,606,000 股。又捷磊公司支付93年間購入合勤公司股票股款,係向股東原告及朱順一分別借款51,000,000元及131,000,000 元(8 月2 日15,000,000元、8 月3 日19,500,000元、8 月5 日14,500,000元、8 月10日82,000,000元),並帳列股東往來,已違一般投資公司交易常情,嗣再以自合勤公司獲配股利償還朱順一合計28,100,000元(93年:4,500,000 元、94年:11,500,000元、95年:4,100,000 元、96年:5,000,000 元、97年:3,000,000 元),惟並無償還對原告之借款,顯見捷磊公司並無資力支付上開股款;又自93年成立後,除於93年8 月間買入合勤公司股票2,626,000 股(原告配偶2,606,000 股+ 93年8 月6 日20,000股)及96年3 月2 日賣出合勤公司股票30,000股外,再無買賣合勤公司股票或從事其他商業活動賺取利益,凸顯捷磊公司異於常情,唯可證原告不惜損失93年至97年之股款利息,將合勤公司股票,移轉給捷磊公司,是除規避稅捐之理由外,並無移轉股票經濟上理由,其目的僅在於透過上開股權移轉,致使其原本應分配予個人股東歸課綜合所得稅之營利所得,轉換為證券交易所得免稅,仍透過捷磊公司間接持有合勤公司股票。 ⒉至原告主張捷磊公司93年至97年營業所得稅申報書全年所得額分別為-1,024,404 元、1,418,454 元、1,483,077 元、4,415,952 元、2,226,001 元,並未如被告所述透過帳列虧損規避稅負之情事乙節,查原告所述為各年度捷磊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帳載結算金額之全年所得額,惟其自行依法調整後分別為-364,121 、-529,143 、-656,436 、-874,496 、-852,504 ,且各年度應納稅額皆為0 元,又捷磊公司93至97年度結算之未分配盈餘金額7,476,693 元、354,591 元、5,192,154 元、3,510,567 元、1,687,451 元,皆小於93至97年度轉正至原告配偶營利所得8,279,262 元、10,041,772元、10,973,130元、6,213,445 元、4,779,950 元,另捷磊公司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第1 項規定未分配盈餘加徵10%稅率皆較原告配偶40%綜合所得稅率低。⒊原告主張因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獲配股利所得,不計入捷磊公司非原告規避乙節,查捷磊公司成立之時序、公司資力、營運及投資標的等異於常情之情事,已如前述,原告及配偶製造外觀上或形式上存在之法律關係或法律狀態,使之不具備課稅構成要件,以減輕或免除其應納之租稅,捷磊公司取得之股利收益,依所得稅法第42條第1 項之規定,並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而不致產生稅負之增加,達到規避稅負之目的,將原應課徵其個人之營利所得轉為捷磊公司不計入之課稅所得,參諸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之立法理由(詳後述),渠等規避稅負之舉甚明,所述委無足採。 ⒋捷磊公司於93年8 月間買入合勤公司股票2,626,000 股(原告配偶2,606,000 股+ 93年8 月6 日20,000股)及96年3 月2 日賣出合勤公司股票30,000股外,再無買賣合勤公司股票或從事其他商業活動賺取利益,原應歸屬原告配偶93至97年度合勤公司營利所得8,279,262 元、10,041,772元、10,937,130元、6,213,445 元及4,779,950 元,原告配偶卻將之轉換為捷磊公司93至97年之未分配盈餘7,476,693 元、354,591 元、5,192,154 元、3,510,567 元、1,687,451 元,且由應課40%之個人綜合所得稅率轉而適用較低稅率之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又依兩稅合一制度基本規定,營利事業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得由股東或社員依規定扣抵其應納之綜合所得稅。本件捷磊公司93年買進合勤公司股票,縱該股票價格上漲,捷磊公司將之出售後所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款於將來盈餘分配予原告配偶,原告配偶可將捷磊公司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在個人綜合所得稅中扣抵,是原告配偶透過投資公司持有合勤公司股票所繳納稅款,不會較直接持有合勤公司股票應繳稅款高,故為避稅所成立投資公司須另外負擔租稅成本為0 ,況本件原告配偶為避稅成立捷磊公司,捷磊公司並未出售合勤公司之股票,即毋庸慮及出售股票之利得產生之所得稅問題。又原告行政訴訟補充狀(三)第3 頁舉例說明為假設情形,係假設投資公司出售全部股票獲利,而本件捷磊公司僅於96年3 月2 日賣出合勤公司股票30,000股〔佔全部持股0.011 (30,000/2,626,000)〕,並未全部出售持股,該假設情形實際並未發生,所述合不足採。 ⒌有關主張被告單以捷磊公司僅繳納10%保留盈餘稅即據此稱原告配偶短繳稅捐,而未將原告配偶及投資公司視為一個整體考慮稅賦乙節。查捷磊公司於財政部賦稅署94年12月19日通報被告查核原告配偶涉有逃漏稅情事前,捷磊公司未曾分配盈餘,是以原告行政訴訟補充狀(三)第10頁股利流向圖,主張應比較A 點及B 點之最終稅負,始為公平云云,惟本件僅有合勤公司股利流向投資公司(C ),並無投資公司(C )將股利流向個人股東(A )之情形(捷磊公司盈餘未曾分配),原告所為圖示與實情不符,所述合不足採。又主張「其他公司獲配股利而未分配予股東,皆僅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未見財政部以實質課稅原則重新核課稅額……有違行政程序法第6 條規定之行政行為平等原則」乙節,查以捷磊公司成立之時序、公司資力、營運及投資標的等異於常情之情事,原告及配偶製造外觀上或形式上存在之法律關係或法律狀態,使之不具備課稅構成要件,以減輕或免除其應納之租稅,捷磊公司取得之股利收益,依所得稅法第42條第1 項之規定,並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而不致產生稅負之增加,達到規避稅負之目的,將原應課徵其個人之營利所得轉為捷磊公司不計入之課稅所得,參諸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之立法理由,規避稅負之舉甚明,被告依法歸課其應負之綜合所得稅,並未違反行政程序法第6 條平等原則,又原告僅敘述「其他公司」未明確指出係何投資公司,況公司營運情形各異,本應就各各情形予以查核,原告主張委無足採。 ⒍綜上,被告以原告配偶涉有藉股權之移轉,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情事,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規定,報經財政部核准後,按原告實際應獲配之股利核定調增94年度營利所得10,041,772 元並無不合,請續予維持。 ㈢罰鍰: ⒈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71條第1 項前段及98年5 月27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110 條第1 項規定,並參諸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之立法理由,可知,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係透過法律之明文規定,授予財政部權限,將藉由形式上合法,而實質上為利用兩稅合一制度,進行租稅規避或逃漏之行為,本於實質課稅原則,否定或變更原形式上之經濟行為安排,並按原實際情形進行調整之明文規範。且依本條規定所為按原實際情形進行之調整,並非即當然不構成租稅之違章,即其事實若有合致所得稅法第110 條規定之漏稅罰,仍應按該條規定處以罰鍰。 ⒉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行政罰法第7 條定有明文,即就行政罰之主觀責任條件,固不採推定過失。原告配偶身為科技公司之負責人,為高階管理人員,原告夫妻2 人自有相當之財務知識,對於前揭安排足以漏報原告配偶所有之營利所得,應具有明知並蓄意使其發生之故意,原告難以卸免其故意短漏之違章責任;其故意濫用違反租稅法之立法意旨,濫用法律上之形式或法律行為,製造外觀上或形式上存在之法律關係或法律狀態,使之不具備課稅構成要件,以減輕或免除其應納之租稅,為求租稅公平,除應以其實質上已具備課稅構成要件之經濟事實加以課稅外,其因而致生漏稅之結果,亦符合前揭所得稅法第110 條第1 項之構成要件,自應論罰。被告按所漏稅額12,656,599元處0.5 倍罰鍰6,328,299 元,係已考量原告違章情節而為適切裁罰,並無違誤。 ⒊至原告主張漏報之所得係屬已填報股利憑單之所得,依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被告亦應僅處罰所漏報稅款0.2 倍乙節,查本件營利所得係依實質課稅原則及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轉正應屬原告配偶之營利所得,非屬漏報已填報原告配偶股利憑單之所得,原告主張係屬誤解。 ㈣綜上論述:原核定及復查、訴願決定並無違誤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94年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原告94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書、金管會證券期貨局4 年12月7 日證期四字第0940005783號函、私募基金與其受益人進行鉅額交易成交資料一覽表、私募基金契約書、集保分類帳、94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系爭裁處書、訴願決定等附卷可稽,洵堪認定。本件兩造之爭點為:原告有無藉移轉其持有合勤公司股權至系爭私募基金,及透過捷磊公司間接持有合勤公司股份,規避原告94年度取自合勤公司獲配股利應歸課之稅捐?被告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規定調整,進而對原告補徵系爭綜合所得稅並處罰鍰處分是否合法? 五、按: ㈠「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1 類:營利所得: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個人或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個人或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如有藉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應納稅金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依查得資料,按實際應分配或應獲配之股利、盈餘或可扣抵稅額予以調整。」分別為行為時所得稅法第2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第1 類及第66條之8 所明定。又「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復為司法院釋字第420 號解釋所明揭。再按「租稅法所重視者,應為足以表徵納稅能力之經濟事實,而非其外觀之法律行為,故在解釋適用稅法時,所應根據者為經濟事實,不僅止於形式上之公平,應就實質上經濟利益之享有者予以課稅,始符實質課稅及公平課稅之原則。」「有關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判斷及認定,應以其實質上經濟事實關係及所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為準,而非以形式外觀為準,否則勢將造成鼓勵投機或規避稅法之適用,無以實現租稅公平之基本理念及要求。」亦有改制前行政法院81年判字第2124號判例及82年度判字第2410號判決可資參照。 ㈡租稅規避與合法規劃節稅不同,節稅係依據稅捐法規所預定之方式,規劃減少稅捐負擔之行為,如申報列舉扣除額等以降低綜合所得淨額及應納稅額;反之,租稅規避則是利用稅捐法規所未預定之異常的或不相當的法律形式,意圖減少稅捐負擔之行為,亦即利用民法上私法自治,特別是契約自由原則,如故意藉股權之移轉或不合常規之安排,不當為自己或他人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以減輕稅捐負擔,取得租稅利益,但實質上卻違反稅法立法者租稅負擔之意旨,兩者有顯著的不同。是對於在經濟實質上已具備課稅構成要件者,雖行為人蓄意使外在之外觀或形式不具備課稅要件,該規避行為因有違租稅公平原則,故於效果上,應本於實質課稅原則,就該經濟實質予以課稅。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規定,即本此意旨並授予財政部權限,將藉由形式上合法,惟實質上進行租稅規避等行為,本於實質課稅原則,否定或變更原形式上之經濟行為安排,並按原實際情形進行調整之明文規範。六、有關投資私募基金之營利所得部分: ㈠查合勤公司於94年6 月3 日召開股東會決議發放股利股息,訴外人兆豐投信公司於94年7 月26日經理系爭私募基金,契約第3 條明定應募人不得超過35人,而實際應募人僅有10人,即原告及配偶朱順一(合勤公司之董事長)、朱順一之弟朱好一及其配偶李麗雯、朱順一之兄朱忠一之妻朱玲、朱順一之子女朱品磊及朱品潔、朱順一之妻舅白常生、合勤公司職員徐麗玲及陳鳳,渠等亦為系爭私募基金受益人(見原處分2 -1 卷第155 至155 -11頁),彼此間為手足、親屬、長官部屬關係,既為合勤公司股東、亦為私募基金之受益人。原告配偶在明知合勤公司獲利分配股息之情形下,於93年8 月10日至17日間,經由臺灣證券交易所以鉅額買賣交易方式,移轉其所有之合勤公司股票8,000,000 股予系爭私募基金,而成為該私募基金受益人,另再申購系爭私募基金(原處分2 -1 卷第95-98頁),由私募基金於94年9 月29日取得合勤公司配發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則獲配之股利毋須計入原告配偶朱順一之營利所得。嗣朱順一再於95年2 月20日至同年3 月7 日向私募基金買回合勤公司股票9,079,000 股(原轉讓8,000,000 股加計配發之股票股利1,120,000 股合計9,120,000 股,差額41,000股少買回股數)(同上2 -1 卷第100 頁),兩造對此並無爭執。 觀此過程,即明朱順一先將合勤公司原應分配予原告配偶之股利、股息,由私募基金取得,再經由私募基金如數贖回,故系爭私募基金所獲股利股息實質上應屬原告配偶所得。雖原告主張投資系爭私募基金意在分散資本及投資等語,惟查原告配偶等基金受益人將其名下合勤、臺塑、南亞、中鋼、矽品及臺塑化等股票,移轉兆豐授信公司,再由系爭私募基金參與公司除權、除息,於除權、除息後,原告配偶再予贖回,取得原有股票之配股配息,其將相同標的由原告配偶等受益人持有狀態轉由渠等持有之系爭私募基金持有,且系爭私募基金持有合勤股票99.66 %、投資金額高達99.79 %,已如前述,投資風險幾無差異,原告主張自無可採。而原告配偶如不移轉合勤公司股票予系爭私募基金,其基於合勤公司之股東身分,本應於94年8 月24日獲配股利,而有相當於所得稅法第14條第1 項第1 類之營利所得,其將所持有之合勤公司股票經由公開市場之鉅額買賣移轉予私募基金,使私募基金本於股東身分於94年8 月24日參與合勤公司發放股利,得以規避股利分配於其名下之營利所得,堪予認定。從而被告以原告配偶藉股權移轉,不當規避或減少94年度原應獲配之股利納稅義務,依所得法第66條之8 規定,報經財政部核准後,按原告配偶實際應獲配之股利核定調增94年度營利所得25,600,000元,依原告與配偶係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歸課原告綜合所得,並無不合。 ㈡次查系爭私募基金成立目的乃「針對高配息之個股操作,為長期持有大量高配息股票之客戶,有效大幅降低所得稅賦」「本基金除權除息總所得為...若以個人之總營利所得來看,累進稅率為40% ,扣除累進差額...本基金可節省之稅額為...」(本院卷2 頁13、14);系爭私募基金信託契約第15條:「一、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將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櫃(含未上市、櫃)股票、承銷股票……及經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前述之上市、櫃股票、精選國內電子類及其上、下游週邊設備之個股。」可知系爭私募基金得投資之標的多樣性。惟系爭私募基金自94年7 月29日成立至95年3 月22日清算止,系爭私募基金投資合勤公司股票比例高達99.66%、投資金額高達99.79%,又實際應募人彼此為手足、親屬、長官部屬關係,足證系爭私募基金之成立、募集及投資標的之選定,係原告配偶等基金受益人所策劃及安排之結果,對系爭私募基金有絕對之控制權。又查系爭私募基金信託契約第18條:「本基金自成立起30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投資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代理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第23條:「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一)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第25條:「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本契約終止……(七)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本契約者。」則受益人有買回受益憑證、更換經理公司及終止信託契約之權利,且原告與配偶以外8 名受益人有親屬、長官部屬關係,原告主張系爭私募基金非受益人所能控制,委無足採。再系爭私募基金投資合勤公司股票比例高達99.66 %、投資金額高達99.79 %(同上2 -1 卷第128 至135 頁及被證1 -兆豐投信公司100 年10月3 日傳真文件),再系爭私募基金應募人間之特殊關係,益證系爭私募基金之成立有特定目的,募集及投資標的之選定亦經安排,否則基於基金分散風險不可能單一持股高達99.66%。又移轉股票及原告配偶於94年12月12日買回系爭私募基金,亦繳納千之之三證券交易稅,惟按「凡買賣有價證券,除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外,悉依本條例之規定,徵收證券交易稅。」證券交易稅係向出賣有價證券人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依千分之三課徵之,證券交易稅條例第1 條第1 項、第2 條第1 款定有明文,此證券交易稅性質與所得稅不同,原告據以主張無規避稅負,亦無可取。再者私募基金雖課徵證券交易稅,然屬免徵所得稅之證券交易所得。故原告配偶藉應募系爭私募基金以規避所得稅。 ㈢有關原告主張「因金管會證期局施壓兆豐投信結清該基金,而非出於原告配偶主觀之意願」乙節,查系爭私募基金係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查核私募基金時,發現原告配偶等系爭私募基金之受益人以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以鉅額買賣交易方式,將持有之公司股票於公司配發股利前轉讓予私募基金,而渠等亦為該私募基金之受益人,該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信託契約規定不分配收益,私募基金買入之股票所分配之股利則毋須計入基金受益人之股利所得,金管會乃要求該基金陸續辦理清算或修正契約分配收益,有金管會證期局94年12月7 日證期四字第0940005783號函可稽(詳2 -1 卷第46頁,本院卷2 頁1 至15)。依上可知,兆豐投信公司係因無法對主管機關陳明其成立基金之投資策略及營運方向,而遭質疑上開私募基金之目的唯在為原告配偶等特定人避稅,與開放私募基金宗旨不符,乃通知兆豐投信公司協調清算或修正契約;原告配偶等受益人亦可修正契約分配收益,惟系爭私募基金若分配收益予各受益人,將無法達到以系爭私募基金規避稅負之目的,始終止契約清算系爭私募基金,故原告此部分主張,為不可採。又系爭私募基金雖經兆豐投信公司與原告配偶等人協調終止,但原告配偶原應受獲分配股利所產生之所得,經上開過程,業已不當規避或減少94年度原應獲配之股利所負納稅義務,依法應予歸課原告綜合所得。 ㈣至原告主張依財政部94年12月28日頒布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明定自95年1 月1 日起,買賣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證券交易所得要納入個人基本稅額課稅,非被告所稱為證券交易所得適用停徵證所稅乙節。查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明定自95年1 月1 日施行,而系爭所得屬94年度所得,自應適用94年度所得稅相關規定。且就系爭屬94年度之所得,原告配偶在系爭私募基金法律關係終止結算(95年3 月22日)後,其於95年5 月1 日至5 月31日法定綜合所得結算申報(94年度所得)期間,明知外觀其為系爭合勤公司分配之股票股息、股利之實質所有人,應申報而未申報,故原告主張依自95年1 月1 日起實施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證券交易所得稅並非停徵,本件情形不構成稅捐規避,並非可取。 七、有關捷磊公司之營利所得部分: ㈠原告配偶朱順一係合勤公司負責人,該公司93年5 月27日股東會決議分配盈餘,盈餘分配基準日93年8 月11日,原告與配偶旋於股利前,於93年7 月14日成立捷磊公司,資本額10,000,000元,原告配偶分別於93年8 月5 日及9 日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以每股67元及70.5元之價格,各賣出1,500,000 股,計3,000,000 股,金額合計206,250,000 元。同日由捷磊公司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買進合勤公司股票計2,606,000 股,金額計179,813,000 元,有大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98年5 月7 日(98)華證(法務)字第00689 號函附資料可稽(見原處分卷2-1 頁164 )。嗣捷磊公司獲配94年度股利10,118,839元。查捷磊公司就上開93年間購入合勤公司股票股款,係向股東原告及其配偶朱順一分別借款51,000,000元及131,000,000 元(分別為8 月2 日15,000,000元、8 月3 日19, 500,000 元、8 月5 日14,500,000元、8 月10日82,000,000元),並帳列股東往來(見原處分卷2-1 頁171 ),並未實際支付款項,而捷磊公司資本額10,000,000元,亦不足以支付系爭股款。嗣捷磊公司以其取自合勤公司獲配股利償還朱順一合計28,100,000元(93年:4,500,000 元、94年:11,500,000元、95年:4,100,000 元、96年:5,000,000 元、97年:3,000,000 元)(詳2 -1 卷第171 、186 、219 、221 、223 、225 、229 、231 頁),惟並無償還對原告之借款,至97年度仍帳列股東往來154,001,000 元(同上卷第242 頁);益見捷磊公司並無資力支付上開股款;又自93年成立後,除於93年8 月間買入合勤公司股票2,626,000 股(原告配偶2,606,000 股+93 年8 月6 日20,000股)及96年3 月2 日賣出合勤公司股票30,000股外,再無買賣合勤公司股票或從事其他商業活動賺取利益,捷磊公司之營業異於常情,足徵其設立有特定目的,系爭移轉合勤公司股票並無經濟上理由。綜上,原告於合勤公司93年盈餘分配基準日前以鉅額交易方式,移轉合勤股票予捷磊公司,使原應由朱順一受配之股利,轉由捷磊公司獲配,致系爭獲配股利應適用之綜合所得稅稅率40% ,轉由適用較低稅負之捷磊公司負擔,則原告與配偶合併申報於各該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相對減少;而捷磊公司取得之股利收益,依所得稅法第42條第1 項:「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應依第66條之3 規定,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之規定,並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而不致產生稅賦之增加。且嗣後再將形式上歸屬捷磊公司之獲配盈餘再藉由免稅之股東往來(借款)名目取回,自屬逃漏個人之營利所得之稅捐之規避行為。 ㈡查捷磊公司之股東僅有原告及其配偶二人,是捷磊公司之經營方式完全取決於原告及其配偶,則朱順一將原本應稅之合勤公司盈餘分配,轉讓給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捷磊公司,而由捷磊公司以取回借款之方式,將應稅轉為免稅就是稅捐規避,合於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立法理由所稱「由於不同身分納稅義務人間,有關稅額扣抵與退還之規定各不相同,為防杜納稅義務人藉投資所得適用稅率高低之不同,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減損政府稅收,並破壞兩稅合一制度,爰參酌紐西蘭及新加坡立法例,規定稽徵機關得按納稅義務實際應獲配之股利、盈餘或可扣抵稅額,分別予以調整。」按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規定,係針對兩稅合一制度之施行,將形式上合法之規避稅捐行為,本於實質課稅原則,就刻意安排之行為,按原實際情形進行調整,就「應分配」或「應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或可扣抵稅額予以調整,與實際操作是否獲利無涉,故原告主張個人透過投資公司間接持股之最終稅負不一定較個人直接持股為低等語,並不可取。況本件經上開安排,捷磊公司93年買進合勤公司股票,若股票價格上漲,捷磊公司將之出售後所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款於將來盈餘分配予原告配偶,原告配偶可將捷磊公司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在個人綜合所得稅中扣抵,是原告配偶透過投資公司持有合勤公司股票所繳納稅款,不會較直接持有合勤公司股票應繳稅款高,故捷磊須另外負擔租稅成本為0 ,況本件捷磊公司並未出售合勤公司之股票,即毋庸慮及出售股票之利得產生之所得稅問題,至於原告行政訴訟補充狀(三)第3 頁舉例說明各假設情形,係假設捷磊公司出售全部股票獲利,惟本件捷磊公司僅於96年3 月2 日賣出合勤公司股票30,000股〔佔全部持股0.011 (30,000/2,626,000)〕,並未全部出售持股,原告假設情形不存在,此部分主張自無可取。 又查捷磊公司於財政部賦稅署94年12月19日通報被告查核本件所涉逃漏稅前,捷磊公司未曾分配盈餘,是以原告行政訴訟補充狀(三)第10頁股利流向圖,主張應比較A 點及B點 之最終稅負,始為公平等情,因本件僅有合勤公司股利流向捷磊公司(C ),尚無捷磊公司(C )將股利流向個人股東(A )之情形,原告所為圖示與事實不符,自難為其有利認定。原告又主張本件與「其他公司」處理方式不同未明確指出係何投資公司,違反行政程序法第6 條平等原則,惟又原告僅敘述「其他公司」未明確指出係何投資公司,況公司營運情形各異,本應就各各情形予以查核,原告主張委無足採。從而被告報經財政部核准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規定辦理,按朱順一應獲配之股利調增9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10,041,772元及可扣抵稅額451,692 元,核無不合。 八、罰鍰: ㈠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為行政罰法第7 條第1 項所明定。又「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 月1 日起至5 月31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應依其全年應納稅額減除暫繳稅額、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而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2 倍以下之罰鍰。」分別為行為時所得稅法第71條第1 項前段及現行同法第110 條第1 項所明定。 ㈡次按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立法理由第1 點後段:「至於營利事業或相關納稅義務人之行為涉及漏稅罰或行為罰部分,則依本法(例如第110 條)或稅捐稽徵法(例如第41條或第43條)相關規定處罰。」可見納稅義務人如有藉投資所得適用稅率高低之不同,將高稅率者應獲配之股利、盈餘及可扣抵稅額,移轉為低稅率或免稅者所有,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情形,稅捐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應納稅額,除得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規定,報經財政部核准後,依查得資料按納稅義務人實際應獲配之股利、盈餘或可扣抵稅額予以調整外,對於納稅義務人之行為涉及漏稅罰或行為罰部分,仍應依所得稅法或稅捐稽徵法相關規定處罰。正因為相關行為涉及漏稅罰或行為罰,仍依相關漏稅罰或行為罰之明文處罰規定,予以審查成立與否,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㈢原告之配偶藉由股權移轉,使自己獲配之合勤公司之股利形式上由第三人取得,而達到漏報其個人營利所得之目的。即透過捷磊公司及系爭私募基金,移轉合勤公司股票,製造外觀上或形式上存在之法律關係或法律狀態,透過捷磊公司當年度不分配盈餘之方式,以減輕其應納之租稅(由個人綜合所得稅之40% 減輕為投資公司未分配盈餘之稅捐10% ),私募基金不分配盈餘之方式,使不具備盈餘課稅之要件,本件經上開安排,移轉應獲配合勤公司之股利25,600,000元及10,041,772元,係已其規避或減少稅捐,致生漏稅之結果,符合所得稅法第110 條第1 項之構成要件,被告予以裁罰,自屬有據。經查,依財政部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違反所得稅法第110 條第1 項規定以漏報之所得有無填報扣繳憑單分處0.2 倍或0.5 倍罰鍰。按有填報扣繳憑單者,因違章事證為稅捐機關所得明確掌握,違章情節較輕微,是處0.2 倍罰鍰,至漏報未填報扣繳憑單之所得,因需由稽徵機關蒐集資料查核始得查獲,違章情節較嚴重,是處0.5 倍罰鍰。本件非屬漏報之所得係屬已填報股利憑單之所得,被告依查得資料按原告配偶朱順一實際應獲配之股利予以調整核定取自合勤公司營利所得25,600,000元及10,041,772元外,並按所漏稅額12,656,599元處以0.5 倍之罰鍰計6,328,299 元,經核係已考量渠等違章情節而為適切之裁罰,並無不妥。 九、綜上,本件原告9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被告核定原告未申報取自合勤公司營利所得25,600,000元及10,041,772元,併同查獲漏報配偶朱順一執行業務所得1,980 元,歸課核定原告94年度綜合所得總額246,537,785 元,補徵應納稅額12,656,599元,並處以0.5 倍之罰鍰6,328,299 元,於法並無違誤,復查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1 月 17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 本 仁法 官 蘇 嫊 娟法 官 林 妙 黛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1 月 17 日書記官 蔡 逸 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