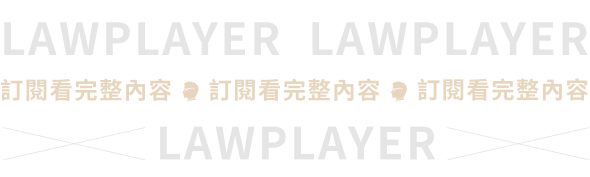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庭(含改制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718號
關鍵資訊
- 裁判案由贈與稅
- 案件類型行政
- 審判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庭(含改制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 裁判日期103 年 10 月 09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3年度訴字第718號 103年9月2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俊瑩 訴訟代理人 賴明陽 會計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慶華(局長) 訴訟代理人 梁忠森 上列當事人間贈與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103 年3 月24日台財訴字第10313908710 號(案號:000000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99年5 月10日與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訂立1 年期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將其所有華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擎公司)股票680,000 股信託予受託人,並以其父李啟南、姊李季蓁、李克玲、姨楊秀芬、岳母黃小玉及姻親親屬池佳盈6 人為信託孳息受益人,並依信託關係申報贈與稅,被告初查核定贈與總額新臺幣(下同)744,473 元,應納稅額0 元。嗣經被告查得,原告將訂約時該信託財產可得確定之盈餘(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藉信託形式贈與信託孳息受益人,乃就受益人實際取得股利價值,依實質課稅原則,重行核定99年度贈與總額為6,460,000 元,應納稅額426,000 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原告仍表不服,提起訴願,遭經駁回,遂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原於99年4 月8 日將其持有之華擎公司股票680,000 股交付信託,約定就該信託財產之孳息贈與特定受益人,委託人不保留變更受益人及分配、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本金自益、孳息他益方式信託與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並依法於同年4 月間向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申報贈與稅(原證二)。惟因該局遲未能審定,又適逢原告搬家遷移戶籍至新北市,並因此另於99年5 月10日以除更新委託人戶籍地址外,完全相同之信託內容與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簽訂信託契約,再持向被告申報「信託贈與」,經被告核定發給贈與稅免稅證明書在案,已合於稅捐稽徵法第34條第3 項第1 款所明定,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案件,納稅義務人未依法申請復查,而為「核課確定」之案件,合先敘明。 二、如前揭所述,本案既已為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 所稱之「核課確定案件」,則之後若有不利於納稅義務人的解釋函令,應不予適用。復參酌改制前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2467號判決:「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而經該管稅捐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案件,如經法定期間而納稅義務人未申請復查或行政爭訟,其審定處分即告確定。嗣稽徵機關如發見原處分確有錯誤短徵情事,為維持課稅公平原則,並基於公益上之理由,雖非不可自行變更原確定之查定處分,而補徵其應徵稅額(本院58年判字第31號判例參照),然此之所謂發見確有錯誤短徵,應係指原處分確定後發見新事實或新課稅資料,足資證明原處分確有錯誤短徵情形者而言。如其課稅事實資料未變,僅因嗣後法律見解有異,致課稅之標準有異時,按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從新從優原則之法理,即不得就業經查定確定之案件,憑藉新見解重為較原處分不利於當事人之審定處分。」。因此,被告是否得自行變更原確定之查定處分,需視原處分確定後發見新事實或新課稅資料,足資證明原處分確有錯誤短徵情形者而言。 三、本案原處分所為重新核定之理由,依復查決定書及訴願決定書所載,無非係被告稱「經查華擎公司於99年2 月5 日董事會已提請承認98年度盈餘分配案」,因而指摘原告於99 年5月10日簽訂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時,實已明確得知將獲配98年度盈餘之事實,自應按實質上經濟事實關係及所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為準……。惟查,被告所指稱之華擎公司99 年2月5 日董事會已提請承認98年度盈餘分配案一事,根本是指鹿為馬,事實上提請承認98年度盈餘分配案之董事會係99年4 月20日才對。因此,原告原已早於99年4 月8 日簽訂原信託契約自不生所謂簽訂信託契約時,可藉由公開資訊觀測站上之資訊而得知盈餘將分配之事實及其具體金額等。 四、依公開資訊觀測站華擎公司99年2 月5 日董事會公告(原證三)所示,當天之董事會係決議通過召開99年度股東常會相關事宜公告,除揭示股東會召開日期、地點外,亦揭示其召集事由,其中召集事由的第六項為「本公司98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僅為一般上市櫃公司例行於股東會召開前公告召集股東會相關事由及議程,並非董事會已就98年度之盈餘分派案作出擬議。再依公開資訊觀測站華擎公司99年4 月20日董事會公告(原證四)所示,當天之董事會才是決議通過盈餘分派案,並決定發放股利種類及金額等資訊。豈可由被告機關一再指鹿為馬,不經調查事實(假如被告看不懂公告內容,亦可行文給華擎公司調閱董事會記錄)即以臆測作為處分之重要依據。 五、再檢附原證五,華擎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自97年至100 年公告事項查詢列表結果所示,華擎公司董事會歷年來對於股東會召集及盈餘分派擬具議案之公告均分為兩次進行決議及公告,並無例外,其中第一次公告僅為召集股東會之公告;第二次公告始為盈餘分配案經董事會通過擬具議案之公告。惟被告不查,且仍一再執財政部100 年5 月6號 台財稅字第10000076610 號令(下稱100 年5 月6 日函)及「經查華擎公司於99年2 月5 日董事會已提請承認98年度盈餘分配案」等語,為其處分及訴願決定之重要依據。因此,被告就事實認定部分已顯有違誤。 六、查適用信賴保護原則有以下要件: (一)須有信賴之事實:釋字第525 號解釋:「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公權力行使涉及人民信賴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者,不限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行政程序法第119 條、第120 條及第126 條參照),即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亦有其適用。行政法規公布施行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因此,參照前揭解釋意旨,遺產及贈稅法第5 條之1 、第10條之2 、所得稅法第3 條之4 、財政部94年函釋,自得作為本件信賴保護之基礎。 (二)信賴表現:人民只要信賴行政行為之存續,此信賴心理狀態存在,其個人之生活關係並已依此建立,即符合信賴表現之要件,即人民不必藉由特定的信賴行為對外加以證實,若國家存有疑義,則應由國家依職權進行調查,以證明人民之信賴不存在。本件原告依照行為時有效之遺產及贈稅法相關規定,及財政部94年函釋,業已於委託人及受託人簽訂信託契約時,即依據遺產及贈稅法第10條之2 規定,計算贈與價值,據以申報贈與,並經被告核發贈與稅繳款書後,繳納贈與稅後始辦理有價證券移轉過戶,且被投資公司所實際分配之任何股息紅利,均依所得稅法第3 條之4 規定,由受益人併入受託人取得年度之所得額申報納稅,故原告之信賴表現實足堪認定。 (三)信賴值得保護:遺產及贈稅法第5 條之1 、第10條之2 、所得稅法第3 條之4 、財政部94年函釋,均行之有年,並無重大明顯違反上位規範之情形,且非原告以不正當或提供不正確資料所促成,故本案原告並無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再者,稅務旬刊第2216期社論亦著有:「各種解釋性及裁量性之稅捐解釋函令,若非係當事人自己之過失或誤認,而是基於國家之具體行為,且相沿成習所造成之法律狀態,則不管行政機關之決定是否合法,除重大且明顯之瑕疵或其違法係可歸責於納稅者外,行政機關之行為一經表露於外,人民通常會對其所造成『法律狀態』之存續寄以依賴,並依之作為行為依據。此種依據之信賴,仍應受保護,否則人民將生活於不確定之法律狀態中。」,同樣支持本案確有信賴值得保護之情形。 七、財政部於94年2 月23日與信託公會、各區國稅局官員研商訂定「研商信託契約形式態樣及其稅捐審查、核課原則」(即財政部94年2 月23日台財稅第09404509000 號函,下稱94年2 月23日函),以委託人「保留指定受益人或分配、處分信託利益權利」之有無,作為認定自益信託或他益信託的基準;換句話說,信託契約內容,雖明訂有委託人自身以外的受益人;但經委託人「保留指定受益人或分配、處分信託利益權利」者,仍然是先以自益信託看待。信託契約成立時,不課徵贈與稅,信託期間信託財產之收益,課徵委託人之所得稅,嗣後委託人如將已實現之信託孳息,贈與其指定之受益人,屬以自己之財產無償贈與他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下稱遺贈稅法)第4 條規定,課徵贈與稅。相反的,信託契約明訂有委託人自身以外的受益人,而且委託人「未保留指定受益人或分配、處分信託利益權利」者,即依遺贈稅法第5 條之1 規定,成立他益信託,依同法第10條之2 規定,計算信託贈與額,並依同法第24條之1 規定,決定贈與日。按遺贈稅法第5 條之1 ,是有關贈與信託權利的構成要件規範、第10條之2 ,是有關應課徵贈與稅權利價值(即贈與稅稅基)的計算規範、而第24條之l ,是對信託權利成立贈與的時點規範,規範非常清楚、明白,沒有模糊的空間。前揭94年度函釋,以受益人不特定性太強為由,先以自益信託看待的解釋,勉強還算符合目的解釋。本件有價證券信託契約的內容,是約定就信託財產之孳息,贈予委託人自身以外的受益人,受益人特定而明確,而且委託人「未保留變更、指定受益人及分配、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依前揭94年2 月23日函,本件有價證券信託是他益信託,復查決定書並未否認,故無爭議。被告於99年時,即依前揭法律規定及函釋精神,依法審核,認定成立「孳息他益信託贈與」,核定贈與稅,已於前述。既然本案是他益信託,贈與客體是未來發放股利的股息請求權;因此,受託人依信託契約,交付信託股票所衍生的股利予受益人的時點,很清楚是履行信託債務、滿足受益人股息請求權的物權行為;絕不是「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被告自不應違背前揭法律規定及函釋精神,將本案以自益信託看待,把原來受託人履行信託債務的物權行為,當作是委託人贈與契約的債權行為,依遺贈稅法第4 條規定,課徵贈與稅。 八、100 年5 月6 日函,核釋個人簽訂孳息他益之股票信託相關課稅規定,認為「委託人經由股東會、董事會等會議資料知悉被投資公司將分配盈餘後,簽訂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或……該盈餘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者,尚非契約訂定後,受託人於信託期間管理受託股票產生之收益……」之規定,認為「…委託人以信託形式贈與該部份孳息,其實質與委任受託人領取孳息,再贈與受益人之情形並無不同,依實質課稅原則,該部分孳息仍為委託人之所得,…嗣受託人交付該部份孳息與受益人時,應依法課徵委託人贈與稅。」 (一)在100 年5 月6 日函中,對於經由股東會、董事會等會議資料知悉被投資公司將分配盈餘,且該盈餘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者,認定孳息仍為委託人所得;也就是將訂約時,稅基是否「明確或可得確定」?作為認定為自益信託或他益信託的基準。這樣的信託定性,與前揭94年度函釋,以委託人「保留指定受益人或分配、處分信託利益權利」之有無,作為認定為自益信託或他益信託的基準,是完全不同的。也等同於,將適用94年度函釋之條件,增列盈餘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者等條件,當然是變更原來的函釋與法律見解。 (二)照理說,究竟是自益信託或他益信託?應取決於信託契約簽訂時,受益人是否已經有跡可循?只有在受益人不特定性太強(即根本看不出該受益人長成什麼樣子),才會先以自益信託看待,這也是前揭94年度函釋的精神所在。依法務部93年法律字第0930010466號函釋,對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的解釋,只要有一個明確的辦法,以備在信託期限內,得以確定;或是在信託設立之時,受益對象尚未出生(自然人)或尚未設立完成(法人),都還算是他益信託。因此,只有在受益人不特定性太強,才會先以自益信託看待;94年度函釋要求下面三種狀況,應先以自益信託看待。1 、未明定特定之受益人,亦未明定受益人之範圍及條件者。2 、雖未明定特定之受益人;惟已明定受益人之範圍及條件,但委託人保留指定受益人或分配、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3 、明定有特定之受益人;但委託人保留變更受益或分配、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至於受益人已特定而明確者,再怎麼說,都是他益信託;絕不可能因為信託契約訂約時,「股息明確或可得確定」,即可變性為自益信託。 (三)信託契約訂約時,是否「股息明確或可得確定」,至多只會影響到贈與額(即俗稱的稅基),並不會影響到孳息他益或自益的認定,依遺贈稅法第10條之1 有明文規定: 1、股息明確或可得確定者:依該條文第3 款但書及第4 款規定「但該孳息係給付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或其他約載之固定利息者,其價值之計算,以每年享有之利息,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年複利折算現值之總和計算之。」、「四、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為按期定額給付者,其價值之計算,以每年享有信託利益之數額,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年複利折算現值之總和計算之…」,也就是將「明確或可得確定的股息」,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折算現值至信託契約訂立日。 2、股息尚不明確或未得以確定者:依該條文第2 款及第3 款前段規定「二、享有孳息以外信託利益之權利者,該信託利益為金錢時,以信託金額按贈與時起至受益時止之期間,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計算之…」、「三、享有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以信託金額或贈與時信託財產之時價,減除依前款規定所計算之價值後之餘額為準。」也就是先將成立信託時的本金或時價,當作是信託期滿的本金或時價,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折算現值至信託契約訂立日,再以前揭成立信託時的本金或時價,減去該折算現值,推計「尚不明確或未得以確定的股息」。(四)綜上,信託契約訂約時,「股息是否明確或可得確定?」只會影響到推計的贈與額(即稅基)。遺贈稅法第10條之1 訂有詳細的明文規定,足供適用。至於受益人已特定而明確者,委託人對該部份明確或可得確定的股息,早已失去控制權及支配權,怎麼可以說,該股權信託期間孳息,仍屬委託人所有?課徵委託人之所得稅,嗣後受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將股權信託孳息,交付予受益人時,反而變成委託人委由受託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贈與他人?依遺贈稅法第4 條規定,課徵贈與稅。完全背離量能課稅,矛盾至極。 (五)參照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1 年度訴字第470 號判決(參原證六)之判決理由載有「細繹遺贈稅法第10條之2 第3 款『享有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以信託金額或贈與時信託財產之時價,減除依前款規定所計算之價值後之餘額為準』之本文,及『但該孳息係給付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或其他約載之固定利息者,其價值之計算,以每年享有之利息,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年複利折算現值之總和計算之。』之但書之法律文義、意義關聯及立法目的,顯見其法律規範意旨,係將享有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權利,劃分為不固定孳息及固定孳息兩種類型,並依其事物之本質而異其權利價值之推計估算方式,以符合量能課稅原則。」及「顯見孳息他益信託契約訂定時,孳息權利價值是否已明確、可得確定或不固定,要與認定信託行為是否屬於租稅規避行為無關。」(六)再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度判字第824 號判決(參原證七)之判決理由載有:「實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之2 第3 款前段與但書之規定,已按未來孳息之實證特徵差異(即數量及時間是否特定)在規範上予以合理之差別處遇,因此理解該條款之規定時,不應拘泥其文字,而應穿透文字字義,瞭解其背後之規範本旨,視信託契約訂立時點,原始信託財產中構成他益孳息部分,其金額及實現時點是否(可得)確定,以決定其應適用之量化規定。此等重要事實對法律之正確適用具有關鍵作用……。」;及認定贈與日為簽約信託契約訂日(於該案為95年6 月14 日 ),而非股東會決議日、股利分派日、實際撥付日等。據此,被告於本件所做之處分顯然與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有別。首先要指出的是,簽訂信託契約日原始信託財產中構成他益孳息部分,其金額及實現時點是否(可得)確定,必須確實由被告依法舉證其事實,始可以實質課稅原則介入,因為那是對法律之正確適用具有關鍵作用的重要事實,自然應課予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之舉證責任。再者,贈與日既然應該是簽約信託契約訂日(本案為99 年4月8 日或99年5 月10日)則有關贈與額之計算必須回到簽訂信託契約日以原始信託財產(本金)扣除已確定之權息(於本案因尚未經董事會決議,故已確定之孳息為零)後所剩之餘額,因其對應之未來孳息之現金流量之時間及金額均不確定,應依遺贈稅法第10條之2 第3 款前段之規定計算贈與總額。因此,顯然被告誤以不適當之100 年5 月6 日函改以實際交付股利之日(於本案為99年9 月10日)重新核定本件贈與總額之處分,顯有違誤。 (七)前述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1 年度訴字第470 號判決理由亦認為「當租稅規劃行為符合『規避意圖』、『法律事實形成之濫用』及『減免租稅效果』之要件時,始得認定為租稅規避行為,進而才有適用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1項 、第2 項規定之實質課稅原則,予以否定其法律形式並核實認定其課稅構成要件事實之問題,要非謂所有租稅規劃行為,只要有節稅意圖或享有減免租稅利益之結果,皆得據以否定其法律形式而逕依實質課稅原則認定其課稅之構成要件事實。」而本案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1 年度訴字第470 號判決之型態完全相同,同樣「係以直接明確單一之孳息他益信託契約之法律形式為信託利益之移轉,並非利用迂迴複雜之法律關係之設計組合而為之,且其實質經濟事實關係係使受益人取得該信託利益,亦與遺贈稅法第5 條之1 第1 項將其擬制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贈與他益受益人」之規範意旨並無不符,足認原告所為系爭信託契約形式上之法律行為安排與實質上之經濟利益歸屬與享有並無不合,則於法律評價上,自難認係租稅規避行為。」及「原告選擇其認為租稅負擔較輕之信託契約方式為財產之移轉,應屬理性之租稅規劃行為,並未濫用法律關係之形成自由,自亦難評價為非常規交易安排之租稅規避行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1 年度訴字第470 號判決理由並因此認為「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釋顯已誤解遺贈稅法對一般贈與行為及信託行為之租稅法律構成要件之規範意旨,僅側重贈與標的價值之估算事項,卻疏未細究租稅規避行為應具備之要件之一之『法律事實形成之濫用』,而限縮租稅法律之適用範圍,自難予以援用。」 九、100 年5 月6 日令中所提:「……委託人以信託形式贈與該部份孳息,其實質與委任受託人領取孳息再贈與受益人之情形並無不同,依實質課稅原則,該部分孳息仍為委託人之所得,……嗣受託人交付該部份孳息與受益人時,應依法課徵委託人贈與稅。」按信託是英美法產物,所有權、受益權、使用權是可以分離的,一碼歸一碼。信託行為以契約方式成立者,只要受益人已特定而明確,或是受益人已經有跡可循,在委託人「未保留變更受益人或分配、處分信託利益權利」情形下,受益人在信託行為成立後,即享有信託利益,委託人已喪失對信託財產或孳息之控制權、支配權,受益人享有對信託財產或孳息之受益權,換句話說,已發生財產移轉之效果,所以遺贈稅法規定契約簽訂日即為贈與行為發生日,良有以也;今100 年5 月6 日函,反向規範該部分孳息仍為委託人之所得,完全背離量能課稅原則;嗣後以受託人依信託契約,交付孳息予受益人日為贈與日,更是完全與贈與的構成要件不合,已如前述。 十、再參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度判字第824 號判決之判決理由亦載有:「則前開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釋意見謂:『……該(股票)盈餘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尚非信託契約訂定後,受託人於信託期間管理受託股票產生之收益……』云云,其規範正當性即值得懷疑。若採此標準,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之2 第3 款但書規定之適用範圍即大幅度縮小,而有固定收益報酬之債券是否能成為他益信託之信託財產,恐怕也會產生爭議。何況未來現金流量時點及金額固定之孳息,一樣可以經由信託安排,由受託人本諸專業,出售再買入而賺取價差,而提升孳息金額。因此認為未來現金固定之孳息,即一定不能成為信託標的,也是錯誤之觀念。本院前已一再強調:信託契約之原始標的與信託人及受益人透過信託契約終局所能獲得之信託利益,無論在規範概念上,或與社會實證上,均可明確區分。」據此,訴願及復查決定所稱之:「尚非該信託契約訂定後,受託人於信託期間管理受託股票產生之收益……」云云,其規範正當性不但值得懷疑,與社會一般通念亦有違背。 十一、98年5 月13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前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即實質課稅原則。再參照102 年5 月14日立法院第8 屆第3 會期第12次會議通過修正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3 款明文規定「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因此,啟動實質課稅一定要有「規避意圖」及「法律事實形成之濫用」;必須要有濫用私法形成自由,規避稅捐的主觀意圖及客觀行為。回歸本案探究,孳息他益股票信託,自始即被定位為「擬制贈與」,遺贈稅法第5 條之1 明文規定在案;為落實此「擬制贈與」,遺贈稅法還以第10條2 及第24條之l ,規範課徵贈與稅權利價值(即贈與稅稅基)的計算方式以及信託權利成立「擬制贈與」的時點。本案原告以贈與(信託孳息他益)之名,依稅法「擬制贈與」規定,繳納贈與稅之實,根本不發生濫用私法形式,規避稅負之問題。尤其本案原於99年4 月8 日第一次簽訂信託契約及原向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申報贈與時均在99年4 月20日董事會之前,即應無「規避意圖」;又在依法申報,經被告依法核定後,才完稅繳納之行為,自然也無「法律事實形成之濫用」,被告竟主張以「藉信託之名,行贈與之實」,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所以本案是直接適用遺贈稅法「擬制」規定,課徵贈與稅,根本與實質課稅無關。部函稱此類案件為「藉信託之名,行贈與之實」,似乎只是一個口號或結果定位,至於本案有何規避稅捐的主觀意圖及客觀行為,都僅以其他與本案無關之其他同事亦有類似之信託契約,即輕率認定原告有「規避稅捐意圖」。依前揭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3 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因此,包括原告如何在第一次簽訂信託契約時已明確得知將獲配98 年 度盈餘之事實,及僅以公開資訊觀測站的公告,被告如何能夠證明原告有參與董事會或內部有關盈餘分配會議?並進而推論原告知悉華擎公司將分配多少盈餘?再推論股東會一定會依照董事會擬具之議案通過?及原申報贈與時有何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一一舉證,以服民心。 十二、100 年11月23日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 修正規定「…財政部發布解釋函令,變更已發布解釋函令之法令見解,如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自發布日起或財政部指定之將來一定期日起,發生效力;於發布日或財政部指定之將來一定期日前,應核課而未核課之稅捐及未確定案件,不適用該變更後之解釋函令。(第1 項)本條中華民國100 年11月8 日修正施行前,財政部發布解釋函令,變更已發布解釋函令之法令見解且不利於納稅義務人,經稅捐稽徵機關依財政部變更法令見解後之解釋函令核課稅捐,於本條中華民國100 年11月8 日修正施行日尚未確定案件,適用前項規定。(第3 項)…」。100 年5 月6 日函,將受益人已特定而明確,而且委託人「未保留指定受益人或分配、處分信託利益權利」者,只因為信託契約訂約時「股息明確或可得確定」為由,即將本件課稅主體及課稅客體均以變更,換句話說是變更了前揭94年2 月23日函,這樣的變更,增加了原告應納之贈與稅,當然是不利於本案原告,依新修訂的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 第2 項及第3 項規定,自發布日起或財政部指定之將來一定期日起,發生效力,也就是不溯及適用於本案。因此,本案原告,原於99年4 月8 日及99年5 月10日兩度所簽定之孳息他益股票信託,仍應適用94年之函釋。而前揭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並無拘束適用本案餘地。 十三、司法院釋字第287 號解釋「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惟在後之釋示如與在前之釋示不一致時,在前之釋示並非當然錯誤,於後釋示發布前,依前釋示所為之行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釋示確有違法之情形外,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應不受後釋示之影響。」其解釋理由書謂:「行政機關基於法定職權,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性質上並非獨立之行政命令,固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因此前揭100 年5 月6 日函,其內容涉及變更人民課徵贈稅及所得稅之權利義務關係,絕非單純之行政規則,而係具有法規性質之法規命令,故100 年5 月6 日函變更94年2 月23日函應至為明確,依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 之規定,後法優於前法、從新從優及不溯及既往等原則,100 年5 月6 日函應就其發布生效後產生的案件適用,始符租稅法定主義。 十四、按憲法第23條所定法律保留原則,係指與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有關之事項,應以法律或法律授權命令加以規範,主管機關於無法律授權的情形下不得自行發布職權命令定之。法律保留原則落實在租稅課徵的領域,則為憲法第19條的租稅法律主義,「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明文規定。」,是應以法律明定的租稅構成要件,自不得以命令為不同規定,或逾越法律,增加法律所無的要件或限制,而課人民以法律所未規定的租稅義務,否則即有違租稅法律主義。 十五、前述對於股利贈與價值的爭議,其產生原因,與信託贈與課稅相關規定立法的時空背景有關。參考立法當時(即90年5 月29日)的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4.05% 。可知其基本假設為,在市場上股票投資報酬率,約與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相當。因此,以此作為計算贈與價值的基礎,並無不公。然而,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自91年以後大幅下滑,遠低於許多股票的投資報酬率,使得孳息他益的股票信託合約,若採取此種計算公式,其所贈與股利的課稅價值將低於實際價值許多。如此一來,就形成法律規範上的漏洞,而產生租稅規劃的空間,惟對於此種立法漏洞的填補,因涉及對於贈與價值(稅基)的計算,其正本清源之道,實應透過法律規範的修正為之,而不宜以發布解釋函令的方式替代,否則,即與租稅法律主義有違。據此,財政部以100 年5 月6 日函作成對此類信託贈與課稅案件的規範,即有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處。 十六、信託課稅方式是立法者的選擇,若因經濟環境的改變,仍應以修法解決:孳息他益信託衍生的稅捐爭議,係源自於90年研議信託課稅修正規定時,立法決策有誤判之處,為遷就租稅經濟原則,採取信託成立時視同贈與及按折現值計算之法律上擬制性規定,再加上立法後利率反轉形成低利率環境,所形成的節稅空間。應屬立法抉擇形成的「法外空間」,100 年5 月6 日函增列課稅要件,回歸現金贈與來矯正此立法瑕疵,自當已違反租稅法律主義。況且,司法院釋字705 號釋示財政部對於捐地申報列舉扣除額金額認定標準所發布之六號解釋令違憲,其理由書載明「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稅基、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定之;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行政規則為必要之規範。」。因此,100 年5 月6 日函顯然也是重新界定租稅主體及租稅客體,並改變原信託贈與的稅基及納稅方法等租稅構成要件,則同屬違憲的行政解釋。 十七、查本件原告從事銷售工作,且並非上述華擎公司之董、監事、經濟部登記之經理人,依台北市國稅局100 年1 月28日財北國稅審二字第1000210894號函說明二所述:「……。惟信託契約若係於被投資公司股東常會(委託人如為被投資公司之內部人則為內部會議或董事會)決議分配盈餘後所訂定,因該決議分配之盈餘於訂約時已明確……」。經查,原告因工作職掌有別,並未參與、也無權參與任何董事會及內部有關財務或盈餘分配議案之會議,又華擎公司99年度董事會決議擬具盈餘分配議案係於99年4 月20日舉行,並於該日公告,蓋盈餘分配係專屬於股東會之決議事項,董事會不得代為決定,經濟部79年5 月4 日商第207413號函釋已訂有明文解釋:「股東會得據以決議分派股息及紅利(公司法第184 條第1 項)。盈餘及股東紅利之分派,乃專屬於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性質上為強制規定,應不得以章程變更為授權董事會辦理事項。」。換言之,凡股東會尚未決議之盈餘分配事項,均非屬明確。況查本件信託契約之委託人(即原告),於99年4 月8 日及99年5 月10日兩度簽訂信託契約係早於董事會決議日及早於股東會決議日(於本案為99年6 月15日),非但沒有參與、也無權參與董事會等內部會議得知是否有盈餘分配及分配數額,即使事後99年4 月20日董事會就盈餘擬具分配議案有發布訊息,原告並非財務會計部門人員,也從未查詢該等訊息,亦無法確知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是否得以通過,故不符合台北市國稅局100 年1 月28日財北國稅審二字第1000210894號函說明二之情形至明。 十八、參酌最高行政法院98年判字第828 號判決「……依土地稅法第49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先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移轉現值,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土地增值稅額並填發稅單送達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依該法第50條規定於收到繳納通知書後30日繳納。此「先核定,後繳納」的流程與所得稅「申報一併繳納,之後核定」並不相同,且稽徵機關調查之事項亦較為簡略,自然得為完整之調查,因此稽徵機關核課土地增值稅處分,自足以形成信賴基礎……」。故本件贈與稅案,與核課土地增值稅處分同為「先核定,後繳納」的流程,自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被告自行以多年後之見解變更,創設違反法律條文之計算贈與稅價值方式,重為核定,顯屬違法處分。 十九、稅捐核課除考量租稅公平以外,法安定性也是必須考慮的一環,尤其針對已核定案件的補徵稅捐,因涉及對納稅義務人的信賴保護,更是如此。於解釋函令有增訂或變更之情形,若該函令的適用將變動納稅義務人的納稅義務,應自公布日後始生效力,否則,將導致納稅義務人之納稅義務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與法治國家所應遵循之法安定性原則相悖,此見解亦為司法實務所採行,如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520 號判決即以:「『財政部依本法或稅法所發布之解釋函令,對於據以申請之案件發生效力。但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之。』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 定有明文。依此規定,財政部新發佈之解釋函,如不利於納稅義務人,則對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自無適用之餘地。」 二十、查被告答辯狀所述,本件被告無非係依據以下幾點做為實質課稅之依據:1 、華擎公司於99年4 月20日董事會已提請承認98年度盈餘分配案,原告於99年5 月10日始與兆豐銀行簽訂股票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實已明確得知將獲配98年度盈餘之事實。2 、原告為公司主要股東第六大股東,又為華擎公司業務部協理,……且對於該公司之營運決策顯有相當之影響力。3 、與華擎公司其他同仁同樣簽訂股票孳息他益信託契約。 (一)惟被告上述論點,不但錯認董事會議案之內容,也僅以錯誤臆測的方式推論原告涉及租稅規避,原告回覆如下: 1、既然被告於答辯狀第22頁第4 行末載明:「查華擎公司99年4 月20日召開之董事會中既已就98年度盈餘分配案,提出擬分配股利之討論案,並將董事會決議通過之盈餘分配案訊息依公司法規定,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據此,所謂該公司之盈餘分配可得確定之最早日期應為被告答辯狀中所說的99年4 月20日,而非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所述之:「99年2 月5 日先行召開董事會承認98年度盈餘分配案。」。此外,華擎公司於99年2 月5 日董事會所提之議案依據原證三號公告所載,清楚表示係決議召開99年度股東常會相關事宜公告,其相關事宜,包括了「4.召集事由」中的「四. 本公司98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顯然只是例行公告召開股東會及其召開日期、地點、事由等內容。而真正由董事會決議盈餘分派案依據原證四號之公告所示,清清楚楚是在99年4 月20日,因此原告提出原證二號原於99年4 月8 日與兆豐銀行簽訂之信託契約及原申報贈與稅等資料,即可證明原告在不能確定當年度盈餘是否分配及其分配數額前,即有明確的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簽訂之意思表達,僅因為戶籍遷移之故,改於99年5 月10日以更新戶籍地址後向所轄被告申報贈與稅,因此可證原告簽訂之信託契約早於華擎公司99年4 月20日之董事會,並無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所稱:「委託人經由股東會、董事會等會議資料知悉被投資公司將分配盈餘後,簽訂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之情形,怠無疑義。 2、查華擎公司主要股東一直都是由華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華毓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所控制,依據公開資訊觀測站99年4 月內部人資料及99年第一季財報(原證八)所示,兩家主要法人股東合計持股為60,008,754股佔當期已發行股份115,041,629 股之52.16%。換言之,已有過半股份是有該兩家法人股東控制。反觀原告持股則只有760,931 股,僅佔已發行股份115,041,629 股之0.66% ,如此低的持股,主要還是來自員工分紅配股,對於公司之營運決策顯無相當之影響力。 3、查原告同事陳○光及沙○旭等人於97年及98年度雖與原告同時簽有股票孳息他益信託契約,未改以一般贈與重新核定其贈與稅。顯然本件純係被告出於誤解華擎公司之董事會決議內容所作出之錯誤處分,繼而訴願會受被告之誤導,仍作出之錯誤決定。此外,被告推論其他同事亦有類似之簽訂信託契約行為,惟也同樣的沒有證明其他同事是否知悉華擎公司之盈餘分配議案,更沒有證明其他同事是否告知原告該等根本尚未確定之事項,更遑論原告簽訂信託契約當時,是否知悉對於該等盈餘是否分配在申報贈與稅時有何差別?因此,被告僅以錯誤臆測及空泛之推論重行核定,顯有疏漏率斷之嫌。 (二)被告答辯狀第27頁中提及數個判決查與本件截然不同,其中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判字第281 號競國公司董事長(其妻為董事)自己主持董事會決議分配股利後再簽訂信託契約之情形,董事長為具有控制或主導盈餘分配,並知悉盈餘分配;而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判字第79號、102 年判字第160 號,委託人為杰鑫公司(非公開公司)之董事長及董事(夫妻),主持董事會決議分配股利後再以夫妻互為受託人簽訂信託契約之情形,為具有控制及主導董事會並知悉盈餘分配等,又再以夫妻互為委託人及受託人;另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判字第46號,委託人為東丕公司公司負責人主持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分配股利後再以其妻為受託人簽訂信託契約之情形,為具有控制或主導董事長並已經股東會決議盈餘分配後,再以妻為形式上之受託人。均顯與本件事實情況完全不同,自當不得援引。 (三)復查被告答辯狀第23頁倒數第7 行中:「原告於簽訂信託契約當日,華擎公司對於盈餘分配之具體金額尚非確定……」。顯然被告肯認原告於原簽訂信託契約時並不知悉董事會是否就盈餘分配進行討論及決議,所以原告當然不會知道會不會有盈餘分配,也就不會知道其具體金額。再查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應符合訂約時已「知悉」之要件始有適用,此亦與財政部100 年8 月23日台財稅字第 10004525991 號函:「主旨:貴會所提本部100 年5 月6 日台財稅字第10000076610 號令之適用疑義乙案,……(三)旨揭部令無追溯既往課稅之問題,上開盈餘於訂約時是否已明確或可得確定,繫於委託人於訂約時是否「知悉」或「具有控制權」,稽徵機關須詳為調查相關事證後,始得處理。」之規定相符。因被告為財政部之下屬機關自當受其拘束,且本案與被告一般裁處實務相違,縱本件已進行至行政訴訟,惟被告仍可採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之方式,自行撤銷原處分或復查決定,以符合上級之指示及人民對政府施政一致性之期待等情。並聲明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復查決定)。 參、被告則以: 一、原告原於99年4 月8 日與兆豐銀行訂立3 年期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將其所有華擎公司股票680,000 股作為信託財產,以李季蓁等6 人為信託孳息受益人,原告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 條之1 及第10條之2 第3 款規定於99年4 月間向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申報贈與稅,嗣經原告以信託契約第4 條第6 款未獲該局審核通過為由撤銷贈與。原告復於99年5 月10日與兆豐銀行訂立1 年期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原告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 條之1 及第10條之2 第3 款規定向被告所屬淡水稽徵所申報贈與稅,經該所依信託財產時價按信託期間及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孳息部分信託利益,核定贈與總額744,473 元在案,合先陳明。 二、按「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為102 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1 項至第3 項所明定。次按行為時司法院釋字第420 號解釋(86年1 月17日公布)已明示:「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98年5 月13日增訂公布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1 項同此意旨),故納稅義務人不選擇通常之交易形態,而迂迴採取通常不會使用之行為模式,藉以達成與選擇通常交易形態相同之經濟效果,並適用可以免除或減輕租稅負擔的法律,而規避通常行為模式所該當之課稅要件,然依該免除或減輕租稅負擔的法律的規範目的,並未預期將其稅捐優惠給予系爭非通常交易行為者,因其規劃安排的表徵行為與其經濟實質不相當,且法律對於該不相當的安排行為,並未預期給予稅捐利益,基於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即應使該經濟實質回歸其所對應之稅法構成要件課稅,亦即在租稅法之適用上,得無視於當事人所採取之行為形式,而將之視為係採取通常行為,並以該通常行為所該當之稅法構成要件,計算其所應負擔之租稅,以維護租稅公平。揆諸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 條之1 所謂「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贈與該受益人,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且依同法第24條之1 「以訂定信託契約之日為贈與行為發生日」,顯然具有擬制贈與稅客體(因他益信託法律行為形式上有別於民事贈與),及使該稅捐客體提前於信託契約成立時即實現的法律效果。然而,在未來的信託利益實現前即擬制課徵贈與稅,該利益於課稅時之價值如何估算(折算現值),宜有一致的標準,以節省逐案查估的稽徵勞費,且因他益信託之受益人享有之信託利益,無論係於信託存續期間取得信託財產所生之孳息,或於信託關係消滅(包括期間屆滿)時取得孳息以外之信託財產,該信託利益除其孳息係給付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或其他約載之固定利息外,均屬不明確(尤以投資股利或天然孳息為然),故立法者乃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之2 第2 款、第3 款規定,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的方法,設算信託利益於信託契約成立時的價值,具有實質類型化的擬制效果。由此可見,如果受益人得享有之信託利益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者,即無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之2 第2 款、第3 款規定之設算方法擬制其贈與時價之必要,而應依實質課稅原則,回歸同法第3 條第1 項、第4 條第2 項規定,認受益人於實際取得信託利益時,實質上的贈與行為成立,依法課徵贈與稅。此乃依上開遺產及贈與稅法條款之規範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就各該條款所涉及贈與稅要件與效果的涵攝範圍為體系性之解釋。故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釋係基於中央財稅主管機關職權,為闡明行政法規(即贈與稅法第4 條第2 項)之原意,就具形式之消極信託契約者適用實質課稅原則所為之通案解釋,符合立法意旨,並無濫用實質課稅之情事(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度判字第46號判決參照)。 三、次按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惟課稅對象的經濟活動多端,難以法律鉅細靡遺規定,為防止納稅人透過迂迴之安排規避租稅,以確保租稅之課徵,在租稅法之解釋及課稅構成要件之認定上,如發生法律形式、名義或外觀與真實之事實、實態或經濟負擔有所不同時,則租稅之課徵基礎,應著重於事實上存在的實質,非以形式外觀為準,否則無以實現租稅公平之基本理念及要求,此為實質課稅原則之意涵,司法院釋字第420 號解釋已闡明在案,亦為98年5 月13日增訂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1 項所規定。是以,對於經濟實質上已具備課稅構成要件者,雖行為人蓄意使外在之外觀或形式不具備課稅要件,仍應將不合常情之稅捐扭曲安排予以導正,對其課稅。 四、又按100 年11月25日修正生效之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 第2 項規定,旨在明定解釋函令之見解涉有變更時,如後釋示變更前釋示之見解且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應有從新從優原則之適用,惟查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係闡明委託人就其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之盈餘,藉孳息他益之信託形式贈與受益人,其實質與委託他人領取股利後再為贈與並無不同,應就其實質贈與之股利依法課徵贈與稅,其認定之課稅事實係贈與「股利」而非「孳息他益之信託利益」,故不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之2 第3 款規定之複利現值折算課稅,應依同法第4 條第2 項規定課徵委託人贈與稅。是本件並無涉及解釋函令變更,致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而有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 第2 項規定之適用,原告訴稱容有誤解。 五、另按司法院釋字第287 號解釋謂:「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即解釋函令乃未經立法程序,而僅由行政機關本諸職權之規定或對於租稅法律、規章適用性上發生疑義時,為闡明其真意,所為正確適用之釋示。其主要在說明法條真意,使條文能正確使用,本身並無創設或變更法律之效力,亦無溯及既往之問題。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意旨,係就個人簽訂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之股票信託契約,有無實質課稅原則之適用所為之釋示,未逾所得稅法暨遺產及贈與稅法課稅之範圍,為闡述該等法規適用之原意,核係財政部就行政法規所為之解釋,依前揭司法院解釋之意旨,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被告予以援用,並無違誤。又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係闡明委託人就其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之盈餘,藉孳息他益之信託形式贈與受益人,其實質與委託他人領取股利後再為贈與並無不同,應就其實質贈與之股利依法課徵贈與稅,其認定之課稅事實係贈與「股利」而非「孳息他益之信託利益」,故不適用本法第10條之2 第3 款規定之複利現值折算課稅,應依本法第4 條第2 項規定課徵委託人贈與稅。而財政部94年2 月23日函釋,係就信託契約之記載是否涉及未明定特定之受益人,或雖有特定之受益人但保留變更受益人等權利,據以認定信託之本質係「自益信託」或「他益信託」,該函釋非屬上開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令釋之核釋範圍。是以,上開2 函令所規範課稅事件之本質及範圍本即不同,自不生見解變更。從而,財政部就類此課稅事實案件,並未發布與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不同之解釋函令,尚無「變更已發布解釋函令之法令」或「不適用該變更後之解釋函令」之問題,核無違反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 規定情事。 六、再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 條之1 規定之意旨,係鑑於信託契約之受益人因信託行為而享有信託利益,屬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第1 項所稱「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故明定他益信託應課徵贈與稅,惟就贈與價值之估算,因考量信託之期限利益,故於同法第10條之2 以複利折現之計算方式明確規範他益信託課稅的計算基準,利率水準的波動並非立法者當時所能預見,但究其立法目的,絕非容讓一般人於實質贈與財產明確可知時,藉由訂立信託之舉,將信託行為淪為降低計算稅賦之避稅工具。 七、節稅係依據稅捐法規所預定之方式,意圖減少稅捐負擔之行為;反之,租稅規避則是利用稅捐法規所未預定之異常或不相當之法形式,意圖減少稅捐負擔之行為。又所謂租稅規避係指納稅義務人在以消滅或延緩稅捐為其主要意圖之情況下,濫用私法之形成自由,刻意進行「人為」且「不自然」之私法行為規劃,使得原本存在(或預計將發生)之稅捐,因此得以消滅或延緩,而此等消滅或延緩稅捐之結果即被認為違反稅捐法制之規範規劃(最高行政法院100 年度判字第726 號判決參照)。況一個法律形成衡諸其所追求之目標,乃屬不相當,並以減輕稅負為目的,且不能經由經濟上或其他值得注意的稅負以外之理由加以正當化時,則構成法律形成之濫用。又不相當的法律形成經常是繁鎖的、複雜的、笨重的、不經濟的、做作的、不自然的、奇特的、部分多餘的、矛盾的、不合理的、不透明的。換言之,濫用法律關係之形成自由,並不以多重的法律關係設計組合為限,縱當事人僅採取單一法律關係,但只要其選擇之法律行為與經濟實質相比較,明顯係多餘的,即可謂該規劃安排的表徵行為與經濟實質不相當,而可認定為法律形成自由之濫用。從而,被告認為本件原告係出於稅捐規避,於法並無不合。 八、原告雖以本件信託契約簽訂日(99年4 月8 日,正確應為99年5 月10日) 係在華擎公司99年4 月20日召開董事會決議盈餘分配案前,認未違反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應無實質課稅原則之適用,惟查:1.本件系爭信託契約簽訂日應為99年5 月10日已如前述;查華擎公司99年4 月20日召開之董事會中既已就98年度盈餘分配案,提出擬分配股利之討論案,並將董事會決議通過之盈餘分配案訊息依公司法規定,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供投資人瀏覽,顯見原告於董事會會議後已明確知悉華擎公司將分配盈餘之事實,此有董事會議事錄及「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可稽。原告於99年5 月10日與兆豐銀行簽訂股票孳息他益信託契約時,該信託孳息已屬受益人可得確定之孳息利益,尚非該信託契約訂定後,受託人於信託期間管理受託股票始產生之收益,亦即其贈與價額英惟該已確定之孳息,原告卻以信託形式將贈與價額轉換成僅按實價折算之現值,使得原本應承認之贈與稅捐因此得以大幅減少,依首揭實質課稅原則,自應以其實質上之經計事實關係及所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為課稅之基礎。2.依社會一般常情,投資人通常對被投資公司之各項訊息會特別注意,而上市或上櫃公司之各項公開資訊,投資人本可自「公開資訊觀測站」輕易查得,原告總持股名列該公司主要股東第6 大股東(為自然人股東之第2 大股東),又為華擎公司業務部協理,負責該公司產品之全球銷售及行銷業務,為該公司之創始元老及核心成員,亦為專業經理人,其對華擎公司經營狀況應知之甚詳,且對於該公司之營運決策顯有相當之影響力。再查原告於96年間即與同為華擎公司創始元老及核心成員,亦為專業經理人之資材中心暨總管理處副理許○隆、研發處MB研發部協理陳○光、沙○旭、周○新、研發處BIOS技術部暨品質測試部協理游○濱與參與96年4 月19日董事會總經理吳○ꆼ,同時於96年6 月21日與兆豐銀行簽訂股票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另97年間原告復與協理陳○光與參與97年3 月26日董事會提請承認96年度盈餘分配案總經理吳○ꆼ,同時於97年3 月31日與兆豐銀行簽訂股票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又98年間原告再與協理陳○光及沙○旭,與參與98年3 月26日董事會提請承認97年度盈餘分配案之華擎公司之總經理,同時於98年3 月31日與兆豐銀行簽訂股票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再依華擎公司歷年來股利情形(94、95、96、97及98年度分別為12元、20.37 元、15.5元、8.5 元及9.5 元)及經驗法則,原告於簽訂信託契約當日,華擎公司對於盈餘分配之具體金額尚非確定,但就華擎公司即將分配98年度盈餘之事實,難謂不知,此有華擎公司91年度至98年度稅後淨利比較表及股利政策與分配情形表可稽。3.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為信託法第1 條所明定。另依法務部101 年5 月17日法律字第10100042190 號函說明「如委託人僅為使他人代為處理事務(例如代為繳納稅金或代為處理共有物事宜等),而將其財產權轉於受任人,自己仍保有實際支配或收益之權利者,其移轉縱以『信託』之名,因受託人並無管理或處分權限而僅為信託財產之形式上所有權人,屬於消極信託,尚非信託法上所稱之信託。」本件信託契約中有關孳息他益部分,即華擎公司之股票孳息(98年度盈餘分配),實質上係在系爭信託契約成立時,業已附隨於自益信託財產即華擎公司股票之利益,原告既明確得知即將獲配98年度股利已如前述,信託期間又僅為1 年,顯見本件受益人所取得之信託孳息(即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並非屬原告99年9 月10日交付信託財產予受託人兆豐銀行,而經受託人於信託期間本於系爭信託契約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所產生之收益,核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 條之1 及第10條之2 之規定有別,受託人兆豐銀行除代收代付華擎公司之股利外,並無其他積極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作為,此觀諸受託人兆豐銀行分別於99年9 月10日交付受益人現金股利後,旋即於100 年3 月2 日將信託財產返還原告並提前終止契約,以及兆豐銀行受託管理有價證券信託專戶結算報告書所載「本行依委託人指示於信託目的已完成下提前終止本信託契約」即明。換言之,原告無須透過受託人兆豐銀行即可達成使受益人取得信託孳息之目的,其經濟實質與原告先取得華擎公司股利後,再將股利贈與受益人之結果並無不同。爰此,原核認原告藉信託之法律形式,將訂約時實已明確得知98年度將獲配盈餘(股現金股利)之事實,卻基於租稅規避之意圖,將實質上應按時價課徵贈與稅之贈與標的「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蓄意安排以信託之名,將贈與標的轉換成僅按信託標的時價與現值差額課徵之「信託孳息」,使得原本存在之稅捐因此得以大幅減少,依上開司法院釋字第420 號解釋及首揭財政部令釋規定,依實質課稅原則,核定原告將其99年度實質可獲配之股利6,460,000 元贈與李季蓁等6 人,課徵贈與稅,並無不合。 九、末按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公權力行使涉及人民信賴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適用信賴保護原則,應有信賴基礎、信賴表現行為及信賴值得保護等情,始足當之。原告雖自行就「信託孳息」申報贈與稅並經被告淡水稽徵所核定在案,惟其申報時並未揭露就該盈餘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之重大事項,致稽徵機關依其申報資料作成核課處分,未包含實際贈與股利之價值,屬行政程序法第119 條第2 款「對重要事項……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之情形,應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稽徵機關既於核課期間內依實際查得事實,認有應行課稅事項,依法即得為補徵。 十、按司法院釋字第420 號解釋及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1項 規定之立法意旨,係租稅法所重視者,應為足以表徵納稅能力之經濟事實,非僅以形式外觀之法律行為或關係為依據。故在解釋適用稅法時,所應根據者為經濟事實,不僅止於形式上之公平,應就實質經濟利益之享受者予以課稅,始符合實質課稅及公平課稅之原則,否則勢將造成鼓勵投機或規避稅法之適用,租稅公平之基本理念則無由實現。經查,原告於訂約後申報並經被告核定之贈與總額為744,473 元,其應負擔之贈與稅僅有0 元,倘若與未藉「信託契約」方式而將財產贈與他人,照一般贈與課徵贈與稅者比較其稅負,原告實際規避之贈與稅金額為5,715,527 元(6,460,000 ─744,473 ),顯見原告利用現行稅法有關受益權價值計算無法真實反映實質價值(以郵政儲金偏低之利率計算之贈與價額亦偏低),藉由簽訂信託契約之迂迴方式將已預知短期內可得之孳息贈與其父親等,以規避贈與稅之課徵,被告於核課期間內依職權查得課稅之事實,並就已具備課稅構成要件之實質經濟行為加以課稅,符合前揭法令規定,並無違誤。是原告藉由簽訂信託契約之迂迴方式規避其應實際負擔之贈與稅,顯已違反稅法之誠實申報繳納稅款義務,而有行政程序法第119 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已無信賴保護原則及行政程序法第8 條規定之適用,原告訴稱適用信賴保護原則乙節,核難有據。 十一、原告援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1 年度訴字第470 號判決,主張該判決之實體案情與系爭情形相同,本件非屬濫用法律事實形成自由之租稅規避行為乙節,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2 年4 月30日101 年度訴字第470 號判決,僅係單一個案,且該案當事人業已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2 年度判字第152 號判決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更審,亦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1 年度訴字第470 號判決惟為最高行政法院所不採,自難援引,且依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度判字第281 、160 、79及46號判決,均一致認為訂立股票「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就孳息他益相類似之情狀,應適用實質課稅原則,顯見司法實務最新見解,與上開原告所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1 年度訴字第470 號判決見解亦不同。因此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能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十二、至原告訴稱在事實沒有變動之情形下,二次核定贈與稅,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且有違背法令之虞云云,查本件原告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雖已申報贈與稅,且經核定,惟申報時並未提示該盈餘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之重大事項,致被告依提供之申報資料作成核課處分,則原告於董事會決議分配盈餘後,以簽訂信託契約之迂迴方式贈與股票孳息,藉由信託之法律行為形式及現行稅法有關信託受益權價值計算無法真實反映實質贈與價值之漏洞,達成贈與孳息及規避贈與稅與所得稅負之真意,實有違反稅法誠實申報及繳納稅款之義務,按納稅義務人依規定辦理申報而經該管稅捐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案件,稅捐稽徵機關如發現原處分確有錯誤短徵,為維持課稅公平之原則,基於公益上之理由,要非不可自行變更原查定處分,而補徵其應繳之稅額(改制前行政法院58年判字第31號判例可資參照) ,又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2 項所謂「另發現應徵之稅捐」,不以「新事實」、「新證據」存在為必要,只須其事實不在行政救濟裁量範圍內者均屬之,包括原認定事實錯誤之情形(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8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是稅捐稽徵機關如發現原處分確有錯誤短徵,為維持課稅公平之原則,要非不可自行變更原查定處分,而補徵其應繳之稅額,本件被告依據實質課稅原則,依原告實質贈與之股利依法課徵贈與稅,於法尚屬無違,請續予維持。 十三、至最高行政法院少數判解(102 年度訴字第810 及102 年度訴字第824 號判決) 固認贈與日應為簽訂信託契約日,惟本件個案事實與該等判決個案未盡相同,且上開少數判決見解。「課稅構成要件事實實現時,其課稅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利益歸屬,暨課稅法律之立法目的為依據,始合於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l 第1 、2 項所規定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納稅義務人將股票交付信託,簽訂『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其中以信託契約訂立時確定或可得確定之股利(股息、紅利)為他益信託之標的,由受託人於股利發放後交付受益人,因該股利並非受託人本於信託法所規範管理或處分信託股票之信託本旨而孳生,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 條之1 第1 項條針對信託法規定之信託而為『視為贈與』規範之意旨不合。觀其經濟實質,乃納稅義務人將該股利贈與受益人而假受託人之手以實現,並因於受益人受領時始該當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第2 項所規定『他人允受』之要件,而成立該條項規定之贈與,故稽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第2 項及第10條計徵贈與稅,並無不合。至納稅義務人上開行為涉有租稅規避情事者,亦應調整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第2 項及第10條計徵贈與稅,自不待言。」復經最高行政法院103 年度5 月份第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在案。 十四、綜上,系爭信託契約中有關孳息他益部分,即華擎公司之股票孳息(98年度盈餘分配),實質上係在系爭信託契約成立時,即已經附隨於信託財產即華擎公司股票之利益,而非信託契約訂立後,由受託人本於系爭信託契約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所孳生,核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 條之1 及第10條之2 之規定無涉,被告以原告迂迴藉由系爭信託契約孳息他益信託方式,以達實質贈與其華擎公司股票所分配股利,並依實質課稅原則,就受託人99年9 月10日交付受益人系爭股票孳息(現金股利),認屬原告對李啟南等6 人之贈與,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第2 項規定,重行核定99年度贈與總額6,460,000 元,並計算應補稅額426,000 元,揆諸首揭規定,尚無不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被告99年度贈與繳款書(原處分卷第84頁)、復查決定書(原處分卷第169-180 頁)、訴願決定書(本院卷第26-34 頁)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一、原告是否藉由股票孳息他益信託之形式為租稅規避,迂迴減輕其原應負擔之贈與稅負?原告(委託人)是否經由董事會知悉被投資公司將分配盈餘後,簽訂系爭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 二、原處分有無違反租稅法定主義(稅捐稽徵法第11條之3 )及法律不溯及既往(稅捐稽徵法1-1 條)、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信賴保護原則?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規定:「(第1 項)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第2 項)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 條第1 項規定:「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之財產為贈與者,應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規定:「(第1 項)本法稱財產,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第2項 )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 (四)行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第1 項規定:「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時價為準。……」 (五)行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28條第1 項規定:「凡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下稱上市)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下稱上櫃)之有價證券,依……贈與日該項證券之收盤價估定之。……」 二、原告藉由股票孳息他益信託之形式為租稅規避,迂迴減輕其原應負擔之贈與稅負: (一)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 條之1 規定「……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贈與該受益人,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及同法第24條之1 規定「以訂定信託契約之日為贈與行為發生日」,具有擬制贈與稅客體(因他益信託法律行為形式上有別於民事贈與),及使該稅捐客體提前於信託契約成立時即實現的法律效果。蓋因未來的信託利益實現前即擬制課徵贈與稅,該利益於課稅時之價值如何折算現值,其估算宜有一致的標準,以節省逐案查估的稽徵勞費,且他益信託之受益人享有之信託利益,無論係於信託存續期間取得信託財產所生之孳息,或於信託關係消滅(包括期間屆滿)時取得孳息以外之信託財產,其信託利益均屬不明確(尤以投資股利或天然孳息為然,但孳息係給付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或其他約載之固定利息者除外),故立法者乃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之2 第2 款、第3 款規定,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的方法,設算信託利益於信託契約成立時的價值,具有實質類型化的擬制效果。反面觀之,如果受益人得享有之信託利益「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者」,即無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之2 第2 款、第3 款規定之設算方法擬制其贈與時價之必要,此時該信託利益,應依實質課稅原則,回歸同法第3 條第1 項、第4 條第2 項規定,認受益人於實際取得信託利益時,實質上的贈與行為才成立,依法課徵贈與稅。若納稅義務人為規避通常行為模式所該當之課稅要件,刻意不選擇通常之交易形態,迂迴採取無經濟實質之行為模式,藉以達成與選擇通常交易形態相同之經濟效果,以適用可以免除或減輕租稅負擔的法律,因該免除或減輕租稅負擔的法律的規範目的,並未預期將其稅捐優惠給予系爭非通常交易行為,則因其規劃安排的表徵行為與經濟實質不相當,基於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即應使該經濟實質回歸其所對應之稅法構成要件課稅。亦即在租稅法之適用上,得無視於當事人所採取之行為形式,而將之視為係採取通常行為,並以該通常行為所該當之稅法構成要件,計算其所應負擔之租稅,以維護租稅公平。此乃依上開遺產及贈與稅法條款之規範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就各該條款所涉及贈與稅要件與效果的涵攝範圍為體系性之解釋(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度判字第46號判決參照),又最高行政法院103 年度5 月份第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稱:「「課稅構成要件事實實現時,其課稅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利益歸屬,暨課稅法律之立法目的為依據,始合於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l 第1 、2 項所規定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納稅義務人將股票交付信託,簽訂『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其中以信託契約訂立時確定或可得確定之股利(股息、紅利)為他益信託之標的,由受託人於股利發放後交付受益人,因該股利並非受託人本於信託法所規範管理或處分信託股票之信託本旨而孳生,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 條之1 第1 項條針對信託法規定之信託而為『視為贈與』規範之意旨不合。觀其經濟實質,乃納稅義務人將該股利贈與受益人而假受託人之手以實現,並因於受益人受領時始該當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第2 項所規定『他人允受』之要件,而成立該條項規定之贈與,故稽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第2 項及第10條計徵贈與稅,並無不合。至納稅義務人上開行為涉有租稅規避情事者,亦應調整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第2 項及第10條計徵贈與稅,自不待言。」,亦同此意旨,並已就之前不同之法律見解作成決議,本院自應參考,原告仍引決議前之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度判字第824 號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1 年度訴字第470 號判決之不同法律見解,主張「系爭股權於信託期間孳息,已屬受託人所有,原告(委託人)對系爭可得確定的股息,已失去控制權及支配權,受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將所信託之股權孳息,交付予受益人時,並非委託人(委由受託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贈與他人」云云,尚不足採。 (二)本件被投資公司華擎公司於99年4 月20日召開董事會決議98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每股9.5 元,股利總額為1,092,895,476 元,見原處分卷第45頁公開觀測站資料),後原告於96年5 月10日與兆豐銀行簽訂1 年期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將其所持有華擎公司股票68,000 股 移轉予兆豐銀行(即受託人),作為信託之原始信託財產,並以其父李啟南(受益權比例18% )、姊李季蓁(受益權比例10% )、李克玲(受益權比例12%)、姨楊秀芬( 受益權比例15% )、岳母黃小玉(受益權比例23%)及姻 親親屬池佳盈(受益權比例22% )6 人為信託財產孳息之共同受益人,有信託契約書附卷可稽(見原處分卷59頁至67頁)。又依「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股利分派情形」記載,華擎公司於99年4 月20日董事會決議、99年6 月15日股東會決議盈餘分配前揭現金股利,並依公司法規定於股東會後將訊息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供投資人瀏覽(見原處分卷第71頁),足見原告訂約時已經知悉該公司已分派98年度股利總額,上開信託契約(99年5 月10日簽訂)既係於華擎公司於99年4 月20日召開董事會決議分配98年度盈餘後始簽訂,系爭股票盈餘於訂約時已可得確定,系爭股票之孳息尚非該信託契約訂定後,受託人於信託期間管理受託股票產生之收益。委託人即原告本可將現金股息直接贈與李啟南等6 人即可完成,卻於被投資公司董事會決議分配盈餘日後,藉信託之名,以孳息他益方式改由李啟南等6 人受領,其實質與委任受託人領取孳息再贈與受益人之情形並無不同,亦即原告採迂迴信託方式將應課贈與稅之贈與標的由應按時價課徵之「股利」轉成僅按「信託標的時價與現值差額」課徵之「信託孳息」以規避贈與稅,在稅法上自應課以與無信託狀態時相同之稅捐,原告實質上經濟事實關係及所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應按實際移轉之股利價值核定贈與額,原告主張伊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之2 第2 款、第3 款規定選擇信託契約之方式,並非規避贈與稅云云,尚不足採。 (三)原告復主張伊第一次係於99年4 月8 日將系爭股票交付信託,並於同年4 月間向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申報贈與稅,惟因該局遲未能審定,又適逢原告搬家遷移戶籍至新北市,因此另於99年5 月10日以完全相同之信託內容(只更新委託人戶籍地址)與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簽訂信託契約,再持向被告申報「信託贈與」,被告應舉證原告如何在第一次(99年4 月8 日)簽訂信託契約時已明確得知將獲配98年度盈餘之事實?如何能以公開資訊觀測站的公告,證明原告有參與董事會或內部有關盈餘分配會議?如何推論股東會一定會依照董事會擬具之議案通過云云。 (四)惟查原告雖係於99年4 月8 日第一次將系爭股票交付信託,並於同年4 月間向被告申報贈與稅,惟經原告贈與稅案件更正(撤銷)申請書以信託契約第4 條第6 款未獲該局審核通過為由撤銷贈與(見本院卷第52頁)。原告復於99年5 月10日與兆豐銀行訂立1 年期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信託契約,系爭信託契約之訂立時點自為99年5 月10日而非99年4 月8 日。且通常股東會不可能大幅增加或減少董事會已決定之應分派盈餘,此為一般經驗法則,原告於訂約時為華擎公司協理(見原處分卷第69頁之董監事持股餘額明細資料),總持股為華擎公司第6 大股東(為自然人股東之第2 大股東)其對於自己擔任大股東及協理之華擎公司盈餘發放,遠較一般民眾(非經營者)為敏感,華擎公司99年4 月20日董事會決議既通過每股盈餘9.5 元,已依規定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見本院卷第54頁),故原告於訂立信託契約時(99年5 月10日)當然已知悉華擎公司將會發放每股大約9.5 元之股利,而有規避贈與稅之意圖,原告主張尚不足採。 三、原處分未違反租稅法定主義(稅捐稽徵法第11條之3 )及法律不溯及既往(稅捐稽徵法1-1 條): (一)原告雖主張依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 第2 項規定:「財政部發布解釋函令,變更已發布解釋函令之法令見解,如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自發布日起或財政部指定之將來一定期日起,發生效力;於發布日或財政部指定之將來一定期日前,應核課而未核課之稅捐及未確定案件,不適用該變更後之解釋函令。」原告早於99年即已簽訂信託契約,並依遺產及贈與稅法10條之1 及所得稅法第3 條之4 申報完稅在案,財政部以100 年5 月6 日函釋變更財政部94年2 月23日函釋之見解,且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並非我國立法機關所制定之法律,被告依財政部事後頒布之解釋,據以作為本件處分,不僅違反租稅法定原則,更違法律不溯既往原則云云。 (二)惟查: 1、按「(第1 項)財政部依本法或稅法所發布之解釋函令,對於據以申請之案件發生效力。但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之。(第2 項)財政部發布解釋函令,變更已發布解釋函令之法令見解,如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自發布日起或財政部指定之將來一定期日起,發生效力;於發布日或財政部指定之將來一定期日前,應核課而未核課之稅捐及未確定案件,不適用該變更後之解釋函令。(第3 項)本條中華民國 100 年11月8 日修正施行前,財政部發布解釋函令,變更已發布解釋函令之法令見解且不利於納稅義務人,經稅捐稽徵機關依財政部變更法令見解後之解釋函令核課稅捐,於本條中華民國100 年11月8 日修正施行日尚未確定案件,適用前項規定。……」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 第1 項至第3 項定有明文。可知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 第2 項之適用,必係財政部就相同租稅爭議,曾先後發布不同之解釋函令,後者之解釋函令變更前者解釋函令之法令見解,而屬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始對於未確定案件,不適用該變更後之解釋函令。 2、查關於信託契約之課稅問題,財政部94年2 月23日函釋曾表示:「主旨:檢送『研商信託契約形式態樣及其稅捐審查、核課原則』會議紀錄乙份。該會議紀錄載明:一、信託案件應由稽徵機關依下列原則核課稅捐:( 一) 信託契約未明定特定之受益人,亦未明定受益人之範圍及條件者不適遺贈稅法規定課徵贈與稅;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屬委託人之所得,應由委託人併入其當年度所得額課徵所得稅。俟信託利益實際分配予非委託人時,屬委託人以自已財產無償贈與他人,應依遺贈稅法第4 條規定課徵贈與稅。( 二) 信託契約明定有特定之受益人者:1.受益人特定,且委託人無保留變更受益人及分配、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依遺贈稅法第5 條之1 (自然人贈與部分)或所得稅法第3 條之2 (營利事業贈與部分)規定辦理。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依所得稅法第3 條之4 規定課徵受益人所得稅。2.受益人特定,且委託人僅保留特定受益人間分配他益信託利益之權利,或變更信託財產營運範圍、方法之權利者:依遺贈稅法第5 條之1 (自然人部分)或所得稅法第3 條之2 (營利事業贈與部分)規定辦理。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依所得稅法第3 條之4 規定課徵受益人所得稅。3.受益人特定,但委託人保留變更受益人或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不適用遺贈稅規定課徵贈與稅;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屬委託人之所得,應由委託人併入其當年度所得額課徵所得稅。俟信託利益實際分配予非委託人時,屬委託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贈與他人,應依遺贈稅法第4 條規定課徵贈與稅。( 三) 信託契約雖未明定特定之受益人,惟明定有益人之範圍及條件者:1.受益人不特定,但委託人保留指定受益人或分配、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不適用遺贈法規定課徵贈與稅;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屬委託人之所得,應由委託人併入當年度所得額課徵所得稅。俟信託利益實際分配予非委託人時,屬委託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贈與他人,應依遺贈稅法第4 條課徵贈與稅。2.受益人不特定,且委託人無保留指定受益人及分配、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依遺贈稅法第5 條之1 (自然人部分)或所得稅法第3 條之2 (營利事業贈與部分)規定辦理。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依所得稅法第3 條之4 第3 項規定課徵受託人所得稅。」顯見該函釋意旨乃就信託契約之約定內容是否明定或未明定特定之受益人,或雖有特定之受益人但保留變更受益人等權利之情形,而據以認定信託契約之性質,係屬「自益信託」或「他益信託」,而異其適用法條。 3、而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釋係核釋:「一、委託人經由股東會、董事會等會議資料知悉被投資公司將分配盈餘後,簽訂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或委託人對被投資公司之盈餘分配具有控制權,於簽訂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後,經由盈餘分配之決議,將訂約時該公司累積未分配之盈餘以信託形式為贈與並據以申報贈與稅者,該盈餘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尚非信託契約訂定後,受託人於信託期間管理受託股票產生之收益,則委託人以信託形式贈與該部分孳息,其實質與委任受託人領取孳息再贈與受益人之情形並無不同,依實質課稅原則,該部分孳息仍屬委託人之所得,應於所得發生年度依法課徵委託人之綜合所得稅;嗣受託人交付該部分孳息與受益人時,應依法課徵委託人贈與稅。二、上開信託契約相關課稅處理原則如下:…。」足見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釋,係就委託人經由股東會、董事會等會議資料知悉被投資公司將分配盈餘後,簽訂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或委託人對被投資公司之盈餘分配具有控制權,於簽訂孳息他益之信託契約後,經由盈餘分配之決議,將訂約時該公司累積未分配之盈餘以信託形式為贈與者,該盈餘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之情形為解釋,其解釋內容與94年2 月23日函釋顯有不同,自無所謂「函釋變更」之問題,原處分適用該解釋,與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 之規定並無牴觸。 4、又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釋,係財政部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及認定事實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核其性質係屬行政程序法第159 條第2 項第2 款所稱統一解釋法令之行政規則,且為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依司法院釋字第287 號解釋意旨,財政部就行政法規所為之解釋,為闡明法規之原意,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該函示係解釋96年間即已存在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第5 條之1 、第10條之2 規定」之實質與稅捐規避,前揭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於96年簽訂之系爭信託契約亦有適用,尚非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釋溯及既往,原告主張「100 年5 月6 日函釋變更財政部94年2 月23日函釋對於信託類型課稅之見解,當自發布日起始有其適用,否則即屬溯及既往」云云,尚不足採。又依司法院釋字第685 號解釋「惟主管機關於職權範圍內適用之法律條文,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規定予以闡釋,如係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為之,即與租稅法律主義無違」,故被告以財政部100 年5 月6 日函釋適用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規定核課贈與稅,並無違背租稅法律主義,原告主張違反租稅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既往原則云云,尚無可採。 四、原處分未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信賴保護原則: (一)原告復主張依照行為時有效之遺產及贈稅法相關規定,及財政部94年函釋,業已於委託人及受託人簽訂信託契約時,即依據遺產及贈稅法第10條之2 規定,計算贈與價值,據以申報贈與,並經被告核發贈與稅繳款書後,繳納贈與稅後始辦理有價證券移轉過戶,且被投資公司所實際分配之任何股息紅利,均依所得稅法第3 條之4 規定,由受益人併入受託人取得年度之所得額申報納稅,故原告之信賴表現實足堪認定,且原告業已有信賴之具體表現,自足形成「信賴基礎」,當有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云云。 (二)惟財政部94年2 月23日函釋只是該函釋意旨乃就信託契約之約定內容是否明定或未明定特定之受益人,或雖有特定之受益人但保留變更受益人等權利之情形,而據以認定信託契約之性質,係屬「自益信託」或「他益信託」,而異其適用法條,已如前述,該函釋並非如原告所述係「就個別信託契約之特殊性,採實質課稅原則,而予類型化課稅」,財政部100 年8 月23日函釋因而稱「……本部從未發布解釋明定類此情形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之2 第3 款規定折算現值課稅之適用……,不生適用信賴保護原則之問題。」,自有所據。且「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而經該管稅捐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案件,如經過法定期間而納稅義務人未申請復查或行政爭訟,其查定處分,固具有形式上之確定力,惟稽徵機關如發見原處分確有錯誤短徵,為維持課稅公平之原則,基於公益上之理由,要非不可自行變更原查定處分,而補徵其應繳之稅額。」改制前行政法院58年度判字第31號著有判例。本件原告雖曾依遺產及贈與稅法及所得稅法申報完稅在案,惟係因原告於申報時未陳明「於信託行為前華擎公司已召開董事會議確認股利總額」所致,致被告誤認事實為「信託契約標的物之孳息來自於受託人之管理,其信託利益於信託當時尚不明確」,嗣原處分機關於核課期間內,另行發現「信託契約標的物之孳息並非來自於受託人之管理,其信託利益於信託當時已經可得確定」之事實,而有另應補徵之稅捐,為維持課稅公平之原則,基於公益上之理由,自可變更原核定,不受之前已確定核課處分之拘束,亦難謂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再者行政程序法第119 條規定:「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2、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3、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上市櫃股票眾多,被告於核定信託契約稅前,若欲查主動查悉上市櫃公司之董事會、股東會是否已決議盈餘分配,勢必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而原告就其信託前華擎公司已召開董事會議確認股利總額之重要事項,則知之甚詳,本有協義務主動陳明,不因被告(因不知情)未令其補正而有不同,且本件並無信託實質內容,僅用以稅捐規避,原告明知(或因重大過失不知)該稅捐規避行為係違法,其信賴尚不值得保護,原告主張尚不足採。 五、被告以信託孳息「交付日」為所贈與之現金股利實現之日,尚無違誤: (一)原告雖主張贈與日應該是簽約信託契約訂日(本案為99年4 月8 日或99年5 月10日),有關贈與額之計算必須回到簽訂信託契約日以原始信託財產(本金)扣除已確定之權息(於本案因尚未經董事會決議,故已確定之孳息為零)後所剩之餘額,因其對應之未來孳息之現金流量之時間及金額均不確定,應依遺贈稅法第10條之2 第3 款前段之規定計算贈與總額。被告以100 年5 月6 日函改以實際交付股利之日(本案為99年9 月10日)重新核定本件贈與總額之處分,顯有違誤云云。 (二)惟查系爭信託契約雖成立在「股東會決議」前,信託標的形式上看來雖是「不含權股票」,但原告於董事會決議分配盈餘後,已然知悉盈餘之大致分配,系爭信託標的實質上與含權股票並無二致,非不得評價(擬制)為一般贈與,則自經濟實質觀之,贈與標的物於「實際交付」予受贈人時之價值,最足以表彰「當年度之贈與總額」,原處分故而依受贈人所實際收受利益之總額,來計算贈與金額,自無違誤。 (三)本件依兆豐99年9 月10日華擎整批匯款資料(見原處分卷第35頁),受託人於99年9 月10日交付受益人系爭現金股利6,460,000 元,被告因而重行核定99年度贈與總額為6,460,000 元,應納稅額426,000 元,減除前次核定贈與總額744,473 元及應納稅額0 元,本次核定贈與總額5,715,527 元,應補稅額426,000 元,即無違誤。 六、綜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尚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屬正確,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9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秋鴻 法 官 陳金圍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代理人之情形 │ │├─────────┼────────────────┤│ꆼ符合右列情形之一│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者,得不委任律師│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為訴訟代理人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利代理人者。 │├─────────┼────────────────┤│ꆼ非律師具有右列情│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形之一,經最高行│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政法院認為適當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亦得為上訴審訴│ 。 ││ 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ꆼ、ꆼ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ꆼ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9 日書記官 簡若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