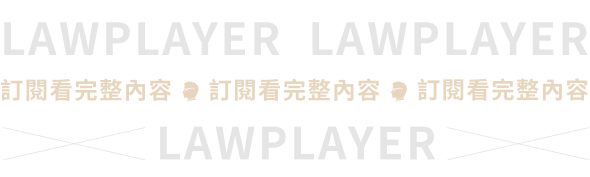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軍上重訴字第1號
關鍵資訊
- 裁判案由殺人等
- 案件類型刑事
- 審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 裁判日期104 年 09 月 08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軍上重訴字第1號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麟凱 指定辯護人 林彥苹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年度軍重訴字第 1號,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2年度軍偵字第 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黃麟凱於年僅 1歲餘時生父即過世,由其母陳金美獨力扶養,嗣就讀新北市立○○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名詳卷)期間,結識同窗王○○(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A女),進而於民國99年間交往成為男女朋友,直至102年7月間協議分手後,仍有聯繫、互動,黃麟凱亦常接送 A女上、下班及上、下課,試圖挽回雙方之情感關係。然因黃麟凱與 A女交往期間,A 女將打工所得薪資轉帳帳戶即華南商業銀行北蘆洲分行帳戶之提款卡交付黃麟凱保管,並授權黃麟凱從中提領款項供A女日常花費之用,迨同年9月間發覺該帳戶款項竟遭黃麟凱提領殆盡,所剩無幾,亟欲取回款項,適逢黃麟凱於同年9月17日入伍服常備士兵役,為現役軍人,A女與其母周○○(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A母)乃於翌日(即同年月18日)急洽陳金美索討新臺幣(下同)20萬元,惟雙方對於應否扣除黃麟凱與A女交往期間A女個人花費部分有所爭議,而陳金美僅允諾返還10萬元。嗣黃麟凱於同年月29日至同年10月3日休假,於同年9月29日下午4、5時許離營返回新北市○○區○○路00號4樓之1住處後,即與A女聯絡,並於當晚7、8 時許與A女及其雙胞胎姊王○○(真實姓名詳卷,下稱B女)在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某萊爾富便利商店內討論還款事宜,A女要求黃麟凱返還20萬元,然黃麟凱認A女已與陳金美達成返還10萬元之協議,故只願返還10萬元,雙方因而多所爭執,後黃麟凱簽發面額10萬元之本票 1紙交付A女,A女並要求黃麟凱當晚即返還10萬元,黃麟凱在 A女催促下,以電話聯絡陳金美商討還款事宜,因A女催逼索款甚急,深覺A女對金錢錙銖必較,未念舊情,態度極差,又對陳金美不同意全額資助金錢供其返還 A女乙事甚感憤怒,然亦覺愧對陳金美,而無法面對 A女離去所帶來之痛苦及陷於緊張之母子關係,產生極大壓力,未能自我反省,竟對 A女極為怨憤,因而萌生以殺害A女之方式解決上述問題之意念,旋於當晚8時36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0○000號「豐京生活館有限公司」(起訴書及原判決誤載為「豐京生活館股份有限公司」)購買棉被收納袋及手電筒之同時,尚購買童軍繩 3條,備供日後下手殺害 A女之用。復於當晚10時許,聯絡其胞姊、姊夫、陳金美、A女、B女等人,在上開便利商店內會面協商還款事宜,雙方達成從10萬元中再扣除黃麟凱前曾為 A女繳付之部分大學學費、而由黃麟凱返還9萬元予A女之協議,黃麟凱與A女並書立協議書1紙為憑,同時由黃麟凱之姊夫簽發面額9萬元之支票1紙交付A女收執。惟因A女事後仍透過電話或網路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黃麟凱返還其餘11萬元,此舉加深黃麟凱無法面對與 A女間情感破裂及與陳金美間母子關係緊張之壓力與憤怒,促使黃麟凱決心殺害 A女。黃麟凱隨即基於無故侵入住宅、殺人之犯意,於同年10月 1日下午4時許,身著白色上衣、黑色長褲及拖鞋,攜帶先前與A女交往期間曾陪同 A女搬家、打新家鑰匙之際所留存、原備供A女忘帶鑰匙時可向其取用之A女位於新北市○○區○○街○號2樓住處(地址詳卷)鑰匙2支,並以提袋裝盛前開童軍繩 3條及其所有之頭套1個、黑色長袖高領上衣1件及手套、襪子各1雙等物,攜往上址A女住處,先持鑰匙開啟該址 1樓樓梯間大門,再於 2樓樓梯間戴上頭套、穿著黑色長袖高領上衣以隱藏身分,並戴上手套、穿著襪子俾免留下指紋及腳印,復以鑰匙開啟上址 A女住處大門,並將所著拖鞋置入隨身提袋,再進入該址屋內,而無故侵入 A女與其父王○○(真實姓名詳卷,下稱A父)、A母、大姊王○○(真實姓名詳卷,下稱C女)、二姊王○○(真實姓名詳卷,下稱D女)、三姊 B女等人共同居住使用之住宅。先至C女、D女共用之房間內拿取長褲1件,備供套住A女頭部之用,再沿屋內走道欲前往位於走道底之A女與B女共用之房間時,行經 A母房門口,為在房內躺椅上休憩之A母發覺,詎黃麟凱一見A母,即激起其主觀上認 A母瞧不起其單親家庭出身及過往對其態度冷漠之仇恨心理,非但未放棄原先欲殺害 A女之犯意而離去,甚且萌生殺害A 母之犯意,上前以雙手掐住A母頸部、阻止A母出聲呼救,A 母亦徒手反抗而抓傷黃麟凱之右臉頰,黃麟凱復以手肘壓制A母雙手後,順勢取出童軍繩1條,纏繞 A母頸部1圈再使力勒緊,A母無力掙脫,因而遭黃麟凱勒頸致呼吸性休克窒息死亡。黃麟凱將 A母勒斃後,至屋內浴室拿取紅色長方巾1條,擦拭A母手指甲縫,以去除 A母生前因抓傷其右臉頰而殘留在手指甲縫之皮屑、血跡,後潛伏在屋內廚房,等待A女現身。嗣於同日下午5時20分許,見 A女下班返回住處,欲進入其與 B女共用之房間內,旋即戴上頭套,自後尾隨,並以上開自C女、D女房間內取用之長褲罩住 A女頭部,再徒手制伏A女,警告A女勿動,將A女帶入A女與 B女共用之房間內,喝令A女趴在床上,並以同一童軍繩反綁A女雙手,隨即步出該房間,至廚房拿取隨身提袋,並將大門反鎖以防止他人入內,再返回 A女房門口放置該提袋,前往客廳飲水之際,A 女掙脫套住其頭部之長褲,下床踢翻置於其房門口之上開提袋,發覺內有黃麟凱之皮夾、其中並有 A女與黃麟凱之合照,因而獲悉該穿戴頭套之人為黃麟凱,故呼喊其名,黃麟凱聞言,返回A女房內,脫除頭套,並應A女要求,將A女鬆綁後,主觀上明知其與A女間因財務糾葛,感情已難回復,而 A女亦因突遭侵入住處之不明人士自後偷襲、綑綁雙手,後又發覺該名刻意穿戴頭套之人竟係黃麟凱,而極為恐懼,自由意志已遭黃麟凱壓制,黃麟凱竟萌生強制性交之犯意,利用 A女因遭其上述作為而陷於極度恐懼、無助、難以逃脫、不敢反抗、性自主決定權受侵害之狀態,親吻並撫摸A女,再將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違反 A女意願之方法,對 A女為性交行為得逞後,為免東窗事發,即承原先殺害 A女之犯意,以同一童軍繩,纏繞A女頸部1圈再使力勒緊,A 女無力掙脫而倒地,鼻孔流血,黃麟凱遂在房內拿取紅色無袖上衣1件擦拭A女鼻血,A 女隨後亦因呼吸性休克窒息死亡。嗣為掩飾罪行而清理現場時,在A女與B女共用之房間內發現書架上之紙盒內有 1萬元現金,竟另萌生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基於竊盜之犯意,竊取 B女所有之該筆款項,同時竊取上開用以擦拭A母手指甲縫之紅色長方巾1條、擦拭A女鼻血之紅色無袖上衣1件、A女身著之女用內褲1件、置於A女與B女共用房間垃圾桶內已遭撕毀之上開協議書殘片等物,並將前開用以殺害A母及A女之童軍繩 1條、紅色長方巾、紅色無袖上衣、女用內褲連同與 A女性交後擦拭精液用之衛生紙團等物置入一黃色塑膠袋內,再將該塑膠袋置於其隨身提袋內。嗣A父於當晚6時40分許返回住處,持鑰匙欲開啟大門未果,深感有異,遂下樓以電話聯絡 C女,黃麟凱旋利用A父在樓下等候C女之際離開該址,前往頂樓藏匿,並將上開頭套、手套、襪子、黑色長袖高領上衣一併置入該黃色塑膠袋內,再將之連同未使用之童軍繩 2條暫置於頂樓角落。迨 C女偕同其男友返回上址,由其男友攀爬屋簷上陽台鐵窗,進入屋內開啟大門讓A父與C女入內,A父旋於A母房內發覺A母倒臥躺椅上,C女隨即報案,經警到場處理後,發覺 A女亦躺臥於其房內床上。嗣為警循線於當晚11時許在上址頂樓查獲黃麟凱,並扣得黃色塑膠袋1個(內有上開用以殺害A母及 A女之童軍繩1條、頭套1個、手套1雙、襪子1雙、黑色長袖高領上衣 1件、紅色長方巾1條、紅色無袖上衣1件、女用內褲 1件、衛生紙團及遭撕毀之協議書殘片等物)及未使用之童軍繩2條,另於黃麟凱身上查獲前開鑰匙2支及現金 1萬元等物。 二、案經 A父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據以認定被告黃麟凱犯罪之供述證據,其中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在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非供述證據亦查無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事,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第 159條至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時、地無故侵入上址住宅、以童軍繩1條勒斃A母、與A女性交後以同一童軍繩勒斃A女、復竊取B女所有之現金1萬元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犯行,辯稱:A 女要求伊鬆綁,並稱「有話我們可以好好說」,伊將A女鬆綁後,A女即主動抱伊,並稱「還好是你,我還以為是之前的小偷」,伊即親吻並撫摸A女,A女詢問伊「是想那個嗎」,伊稱「我們很久沒有那個了」,之後 A女即主動撩起伊上衣,伊亦脫去 A女衣服,在A女床上與A女發生性行為,伊與A女係合意性交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 A女原為男女朋友,於102年7月間協議分手後,被告即於同年10月1日下午4時許,身著白色上衣、黑色長褲及拖鞋,攜帶先前與A女交往期間曾陪同A女搬家、打新家鑰匙之際所留存、原備供A女忘帶鑰匙時可向其取用之A女位於新北市○○區○○街○號2樓住處鑰匙2支,並以提袋裝盛童軍繩3 條及其所有之頭套1個、黑色長袖高領上衣1件及手套、襪子各1雙等物,攜往上址A女住處,先持鑰匙開啟該址 1樓樓梯間大門,再於 2樓樓梯間戴上頭套、穿著黑色長袖高領上衣以隱藏身分,並戴上手套、穿著襪子俾免留下指紋及腳印,復以鑰匙開啟該址大門,並將所著拖鞋置入隨身提袋,再進入屋內,而無故侵入A女與A父、A母、C女、D女、B女等人共同居住使用之住宅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偵審中坦承不諱,並有在被告身上查獲之該址住宅鑰匙 2支扣案可證(照片見軍偵卷第36頁);又被告供稱:之前A女搬家時,伊陪同A女打住家鑰匙,將多出的鑰匙留在身邊,以備 A女忘記帶鑰匙時,可向伊拿鑰匙,伊曾將此事告知A女,但A女忘記了等語(見軍偵卷第8頁反面至第9頁、第98頁),足見被告雖取得上址住宅鑰匙,惟未獲 A女或其同居家屬同意或授權得任意入內,是被告於前揭時、地無故侵入 A女與其父母、胞姊共同居住使用之住宅,應堪認定。 ㈡前揭被告變裝、侵入上址住宅後,先至C女、D女共用之房間內拿取長褲1件,備供套住A女頭部之用,再沿屋內走道欲前往位於走道底之A女與B女共用之房間時,行經 A母房門口,為在房內躺椅上休憩之A母發覺,被告即上前以雙手掐住A母頸部、阻止A母出聲呼救,A母亦徒手反抗而抓傷被告之右臉頰,被告復以手肘壓制A母雙手後,順勢取出童軍繩1條,纏繞A母頸部1圈再使力勒緊,A 母無力掙脫,因而死亡。被告將A母勒斃後,至屋內浴室拿取紅色長方巾1條,擦拭 A母手指甲縫,以去除 A母生前因抓傷其右臉頰而殘留在手指甲縫之皮屑、血跡,後潛伏在屋內廚房,等待 A女現身。嗣於同日下午5時20分許,見A女下班返回住處,欲進入其與 B女共用之房間內,旋即戴上頭套,自後尾隨,並以上開自C女、D女房間內取用之長褲罩住A女頭部,再徒手制伏A女,警告 A女勿動,將A女帶入A女與B女共用之房間內,喝令A女趴在床上,並以同一童軍繩反綁 A女雙手,隨即步出該房間,至廚房拿取隨身提袋,並將上址大門反鎖以防止他人入內,再返回A女房門口放置該提袋,前往客廳飲水之際,A女掙脫套住其頭部之長褲,下床踢翻置於其房門口之上開提袋,發覺內有被告之皮夾、其中並有 A女與被告之合照,因而獲悉該穿戴頭套之人為被告,故呼喊其名,被告聞言,返回 A女房內,脫除頭套,並應A女要求,將A女鬆綁後,親吻並撫摸 A女,再將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對A女為性交行為後,以同一童軍繩,纏繞A女頸部1圈再使力勒緊,A 女無力掙脫而倒地,鼻孔流血,被告遂在房內拿取紅色無袖上衣1件擦拭A女鼻血,A女隨後亦死亡。嗣為掩飾罪行而清理現場時,在A女與B女共用之房間內發現書架上之紙盒內有1萬元現金,遂竊取B女所有之該筆款項,同時竊取上開用以擦拭A母手指甲縫之紅色長方巾1條、擦拭A女鼻血之紅色無袖上衣1件、A女身著之女用內褲1件、置於A女與 B女共用房間垃圾桶內已遭撕毀之上開協議書殘片等物,並將前開用以殺害A母及A女之童軍繩1條、紅色長方巾、紅色無袖上衣、女用內褲連同與A女性交後擦拭精液用之衛生紙團等物置入一黃色塑膠袋內,再將該塑膠袋置於其隨身提袋內。嗣A父於當晚6時40分許返回住處,持鑰匙欲開啟大門未果,深感有異,遂下樓以電話聯絡C 女,被告旋利用A父在樓下等候C女之際離開該址,前往頂樓藏匿,並將上開頭套、手套、襪子、黑色長袖高領上衣一併置入該黃色塑膠袋內,再將之連同未使用之童軍繩 2條,置於頂樓角落等情,迭據被告於警偵審中供承明確,並有現場圖、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轄內初步勘察報告、現場勘察報告等在卷可稽(見相卷一第11至44頁、軍偵卷第36至39頁、第46至88頁、相卷二第18至 100頁),復有在案發現場頂樓查獲之黃色塑膠袋1個(內有上開用以殺害A母及 A女之童軍繩1條、頭套1個、手套1雙、襪子1雙、黑色長袖高領上衣 1件、紅色長方巾1條、紅色無袖上衣1件、女用內褲 1件、衛生紙團及遭撕毀之協議書殘片等物)、未使用之童軍繩2條暨於被告身上查獲之現金1萬元等物扣案可證。㈢A母經相驗後,發現頸部有「C」型勒痕,7公分長,中央寬2公分,兩緣寬1公分,左側側頸近耳下有連續勒壓痕跡(長5公分)等外傷,經解剖後發現頸部左側有披狀軟骨骨折、有壓痕上出血點於左側頸,A 母係因生前遭勒頸而呼吸性休克窒息死亡;另A女經相驗後,發現頸部有寬1.0公分索溝位於前頸水平位置,在左側成分叉(各1公分),長7公分,甲狀軟骨有骨折等外傷,經解剖後發現甲狀軟骨有出血點及骨折,A 女係因勒頸而呼吸性休克窒息死亡等情,亦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鑑定報告書、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及檢驗報告、相驗照片等在卷可參(見相卷一第52至65頁、第98至 106頁、第111至124頁、相卷二第70至77頁、軍偵卷第55頁、第63至70頁),而A母、A 女均因遭勒頸致呼吸性休克窒息死亡之結果,亦與被告供述以童軍繩先後絞殺A母、A女致死乙節互核相符,又被告於102年9月29日晚間8時36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0○000 號「豐京生活館有限公司」購買棉被收納袋及手電筒之同時,尚購買童軍繩3條,備供日後下手殺害A女之用,此亦據被告供述明確,並有在被告住處查扣之統一發票可證(見軍偵卷第37頁),凡此俱與被告所供殺害A母、A女之情節及警員於案發後在現場頂樓查扣已用以殺人之童軍繩 1條及未使用之童軍繩 2條等情相符。且在案發現場頂樓扣案之童軍繩 1條(送檢編號20-1)經鑑定結果,其上血跡檢出一混合之DNA-STR型別,不排除為A母、A女之DNA混合之結果,另一處(以膠帶黏取目視無紅色斑跡處採樣)檢出 DNA-STR主要混合型別,不排除為A女及被告之DNA混合之結果等情,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現場勘察報告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在卷可憑(見相卷二第24頁、第94至98頁),足證被告供述先後勒斃A母、A女之情節,確屬可採。又 A母遭被告勒頸後曾試圖反抗而抓傷被告之臉頰,此亦核與被告為警查獲時,其右臉頰有疑似人類手指甲抓傷痕跡等情相符,有照片在卷可參(見相卷二第82至83頁),並據被告供述 A母於反抗過程中抓傷伊右臉頰等語明確。綜觀上情,益證 A母確係遭被告先以雙手再以童軍繩勒頸、A 女則係遭被告以同一童軍繩勒頸,致呼吸性休克而窒息死亡。 ㈣又在案發現場頂樓查扣之黃色塑膠袋內之衛生紙袋 1包(內有衛生紙團6團),經鑑定結果,其中衛生紙團證物編號20-2-5,含有精液,精子細胞層檢出一男性之DNA-STR主要型別,與被告之DNA-STR型別相同,表皮細胞層檢出一女性之DNA-STR型別,與A女之DNA-STR型別相同;衛生紙團證物編號20-2-9及採自 A女陰道之棉棒,則均含有精液,精子細胞層檢出一相同之DNA-STR混合型別,不排除為A女與被告 DNA混合之結果,表皮細胞層檢出同一女性之DNA-STR型別,與A女之DNA-STR型別相同;另採自A女乳房之移轉棉棒(證物編號A3)檢出之DNA-STR型別,不排除為A女與被告 DNA混合之結果;再經警以白光及紫外燈搭配濾鏡檢視 A女房間內床上之棉被1條(證物編號21),一面疑似精液4處(證物編號21-1至21-4),另一面有疑似精液 3處(證物編號21-7至21-9)等情,亦有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現場勘察報告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可憑(見相卷二第21頁、第24至25頁、第94至98頁),足認被告供述於絞殺 A女前,曾以其陰莖進入A女陰道,對A女為性交行為乙節,亦屬非虛。 ㈤被告於年僅 1歲餘時生父即過世,由其母陳金美獨力扶養,嗣就讀新北市立○○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期間,結識同窗 A女,進而於99年間交往成為男女朋友,直至102年7月間協議分手後,仍有聯繫、互動,被告亦常接送 A女上、下班及上、下課,試圖挽回雙方之情感關係。然因被告與 A女交往期間,A 女將打工所得薪資轉帳帳戶即華南商業銀行北蘆洲分行帳戶之提款卡交付被告保管,並授權被告從中提領款項供 A女日常花費之用,迨同年 9月間發覺該帳戶款項竟遭被告提領殆盡,所剩無幾,亟欲取回款項,適逢被告於同年 9月17日入伍服常備士兵役,A女與A母乃於翌日(即同年月18日)急洽陳金美索討20萬元,惟雙方對於應否扣除被告與 A女交往期間 A女個人花費部分有所爭議,而陳金美僅允諾返還10萬元。嗣被告於同年月29日至同年10月3日休假,於同年9月29日下午4、5時許離營返回新北市○○區○○路00號4樓之1住處後,即與A女聯絡,並於當晚7、8時許與A女及其雙胞胎姊 B女在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某萊爾富便利商店內討論還款事宜,A女要求被告返還20萬元,然被告認A女已與陳金美達成返還10萬元之協議,故只願返還10萬元,雙方因而多所爭執,後被告簽發面額10萬元之本票1紙交付A女,A 女並要求被告當晚即返還10萬元,被告在 A女催促下,以電話聯絡陳金美商討還款事宜,並於當晚8時36分許購買前述童軍繩3條後,於當晚10時許聯絡其胞姊、姊夫、陳金美、A女及B女等人,在上開便利商店內會面協商還款事宜,雙方達成從10萬元中再扣除被告前曾為 A女繳付之部分大學學費、而由被告返還9萬元予A女之協議,被告與A女並書立協議書1紙為憑,同時由被告之姊夫簽發面額9萬元之支票1紙交付 A女收執,惟 A女事後仍透過電話或網路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被告返還其餘11萬元等情,除據被告於偵審中供述明確外,並經證人陳金美、B 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見原審卷二第32至40頁、第66頁反面至第75頁反面),且經原審勘驗被告與 A女於102年9月29日會面商討還款事宜之錄音內容屬實,製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76至182頁),復有協議書殘片扣案暨A女於案發前3日透過LINE與被告互傳之訊息紀錄、本票等附卷足參(見軍偵卷第38頁、軍他卷第17頁、原審卷一第135至171頁),已堪認被告係因 A女催逼索款甚急,深覺 A女對金錢錙銖必較,未念舊情,態度極差,又對陳金美不同意全額資助金錢供其返還 A女乙事甚感憤怒,然亦覺愧對陳金美,而無法面對 A女離去所帶來之痛苦及陷於緊張之母子關係,產生極大壓力,因而對 A女極為怨憤,於同年 9月29日晚間前往上開賣場購物之同時另購買扣案之童軍繩3條之際,應已萌生以殺害A女之方式解決上述問題之意念,復因 A女於協議書簽立後,仍透過電話或網路通訊軟體傳送訊息要求其返還餘款11萬元,此舉加深被告無法面對與 A女間情感破裂及與陳金美間母子關係緊張之壓力與憤怒,促使被告決心殺害 A女,是被告於案發當日侵入上址住宅前,已萌生殺害 A女之故意而預謀犯案,此情亦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是認。至關於被告殺害 A母之動機,因其等二人於案發前並無直接接觸之情形,復無確切證據足認被告於案發當日侵入A女住處之際已知悉A母人在其內,是被告供稱:伊當時沿屋內走道欲前往位於走道底之A女房間時,行經A母房門口,為在房內躺椅上休憩之A母發覺,為阻止A母出聲呼救,又憶及A女曾告以A母對單親家庭之態度及過往對其冷漠不友善,因而臨時起意殺害 A母等語,應屬可採。又人體頸部為重要且脆弱之部位,乃氣管、支氣管等呼吸系統及主要大動脈通往腦部之所在,佈滿血管及神經,如以童軍繩勒緊,將致呼吸困難而窒息死亡,此乃眾所周知之事,被告對此自難諉為不知,竟朝A母、A女頸部要害下手,益徵其殺意甚堅,A母、A女之頸部又有軟骨骨折之現象,亦如前述,顯見被告下手甚重,毫無節制,而有致人於死之意,是其於行為之際,主觀上已明知其攻擊方式、部位及所用工具,適足以造成A母、A女喪失生命之結果,並有意使其發生,其主觀上顯有戕害他人生命之直接故意至明。 ㈥被告雖辯稱: A女要求伊鬆綁,並稱「有話我們可以好好說」,伊將A女鬆綁後,A女即主動抱伊,並稱「還好是你,我還以為是之前的小偷」,伊即親吻並撫摸A女,A女詢問伊「是想那個嗎」,伊稱「我們很久沒有那個了」,之後A女即 主動撩起伊上衣,伊亦脫去A女衣服,在A女床上與A女發生 性行為云云。惟查: ⒈A女於102年7月間即與被告協議分手,而由卷附A女於案發前之同年8月22日與同學間利用LINE傳送之訊息顯示,A女向同學表示其很清楚自己沒愛被告(見原審卷一第 156頁),後於同年 9月間又發覺辛苦打工賺取之薪資竟遭被告領用殆盡,所剩無幾,其等間就被告遲未能還款及應償數額多寡等節多所爭執,A女甚且於案發前3日透過LINE傳送「我現在竟然跟傷我最深的聊天」、「現在難過比分手難過是因為覺得太笨了竟然被騙錢騙了一年,當初對你媽也是真心的好,全部都被現實吞了」、「當初如果不要戀愛就好了」、「賺的錢都被最熟的人騙光。也被隱瞞這麼久」、「如果是你不難過嗎」、「還被嗆,是我自己要把卡交給你的」、「你如果還沒私下還我五萬」、「我們還是仇人」、「現在對我來說,你還是我的仇人」、「你真的是爛人」、「花了我的錢,最後還要我自己去討回來」、「受一堆氣」、「你真的很爛」、「隨便一個人都沒有你誇張」、「之前還一直相信你拿去投資基金」、「哈哈……想起來真是傻」、「你這比我家遭小偷還可怕」、「你知道你對我的震撼,不會有人會這樣傷害我了」、「怎麼這麼不付責任,這樣丟給你媽媽」、「快把錢還我吧……最後對你的要求」、「對你和媽媽付出都是真心的,沒有想過你們會這樣對我」、「但是傷害已經造成,你現在只能把他降到最低」、「還是希望你可以趕快處理這件事情不要再拖了」等訊息予被告,此有該等訊息紀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35至151頁),被告亦自承:A 女這幾天跟伊講話的態度都很差,一直逼問伊到底要不要還錢、錢借到了沒有、什麼時候要還錢等語(見軍偵卷第98頁),足見其等間於案發前已因金錢糾紛而有不快,陷於緊張關係,感情已不復從前,實難想像 A女於案發當日自願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 ⒉又A女住處於案發前之同年9月12日深夜 4時許,遭不明男子侵入,撫摸A女,致A女驚醒,而該名男子穿戴之黑色頭套,適與A女先前贈與被告之頭套相同,A女旋利用LINE傳送訊息告知被告,並稱:「他帶黑色頭套」、「我還懷疑是不是你」等語,被告則即刻前往陪伴受驚之 A女,此除為被告所不否認外,並有 A女與被告傳送之訊息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80至88頁),且C女亦指稱:A女曾於102年9月12日凌晨 4時許熟睡中,遭戴頭套之男子趁其熟睡時撫摸身體而驚醒,該人即打開大門乘隙逃逸,家人當下立刻報警,A 女於事發後當晚 4時19分許透過LINE聯繫被告,告知遭遇小偷之情形,被告在1分鐘內馬上回覆A女,且表現出不知道此事,並表示關心,還趕過來我家樓下關心 A女,但正常人不可能在凌晨4時許還在熟睡中能馬上回覆A女的LINE聊天訊息,我懷疑被告就是在當晚偷進去我家等語(見相卷二第 4頁反面),是A女於案發前之同年9月12日遭頭戴黑色頭套之不明男子偷襲後,直至案發當日即同年10月 1日下班返回住處,欲進入其房間之際,又突遭不明人士自後以長褲罩住頭部,並遭制伏且警告勿動,再帶入房內,喝令趴在床上,並遭反綁雙手,斯時內心必定驚恐萬分,即便事後利用該人短暫離開房間之際,自行掙脫套住頭部之長褲,下床踢翻置於房門口之提袋,發覺內有被告之皮夾、其中並有 A女與被告之合照,因而發覺該人竟係熟識之被告,然見被告刻意穿戴頭套,該頭套又係 A女先前所贈,此亦為被告所是認(見原審卷二第 236頁反面),衡情其必聯想先前遭不明男子撫摸之事,而更加懷疑其人即為被告,亦必慮及自身與被告間已因金錢糾紛而有不快,感情不若以往,被告又突蒙面潛入住處,恐對己不利,於此情形下,豈有與被告合意性交之可能?是被告所辯:伊將A女鬆綁後,A女即主動抱伊,並稱「還好是你,我還以為是之前的小偷」,伊即親吻並撫摸A女,A女詢問伊「是想那個嗎」,伊稱「我們很久沒有那個了」,之後 A女即主動撩起伊上衣,伊亦脫去A女衣服,在A女床上與 A女發生性行為云云,顯與情理相違,殊難採信。況被告供稱:當下伊沒料想到A女會跟伊發生性行為,A女比較不敢有太大反抗動作,跟平常的A女不太一樣,伊抱A女、親吻A女時,A女亦未推開伊或說不要,在撫摸後有了情慾就發生性行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6頁),是由A女斯時舉止、反應不若往常乙節觀之,足見其確因突遭蒙面潛入家中之被告自後偷襲、綑綁而感驚恐,故面對被告主動親吻、撫摸,為免觸怒被告招致不測而對被告虛與委蛇,不敢反抗,此亦屬情理之常,是其自由意志已遭被告壓制,被告亦明知其與 A女間因財務糾葛,感情已難回復,竟利用 A女因其上述作為而陷於極度恐懼、無助、難以逃脫、不敢反抗之狀態,親吻、撫摸 A女進而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則其確以此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對A女為性交行為,致A女性自主決定權受侵害,亦堪認定,所辯洵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辯護人另以:A 女未採取逃離現場、大聲呼救、尋求鄰人協助等措施,且始終無反抗行為等情,謂 A女與被告係合意性交云云,亦無可採。 ⒊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於侵入住宅之際,已有強制性交之故意云云,惟被告供稱:開始犯案之際,並無強制性交犯意,係與A女親密接觸後,始生情慾等語(見軍偵卷第104頁),要難僅憑其於案發前購買童軍繩乙節,遽認其於侵入住宅之初,即有對 A女強制性交之犯意,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其於侵入住宅之際已有強制性交之意,依罪疑唯輕原則,自應認被告係於將A女鬆綁後,方萌生對A女強制性交之犯意。 ⒋辯護人另謂:被告與 A女雖已分手,關係仍相當緊密,事實上與一般男女朋友無異,且A女於案發時尚不知A母已遇害,亦不知被告有殺意,故應係與被告合意性交云云。而 A女於案發前之102年9月10日曾至被告家中烤肉,預先慶祝中秋節,並為即將入伍服役之被告送行乙節,固據證人 B女、陳金美、被告之友人蘇軒立、魏伯翰及江定達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而 A女住處前於同年月12日深夜,遭不明男子侵入並撫摸A女,致A女驚醒,旋利用LINE通知被告,被告亦立即前往陪伴,且A女與被告間曾於同年8月27日、28日、9月2日、4 日、11日、12日、17日透過LINE分別談及夢境、內衣等較為私密之話題,A 女並傳送自身照片予被告等互動,固有該等訊息紀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2至102頁)。然A女與被告交往多年,即便分手,仍保持聯繫,互有往來,被告亦常接送 A女上、下班及上、下課,試圖挽回雙方之情感關係,業如前述,是 A女或基於過往男女朋友情誼,或仍習於舊有相處模式,以致時有互動往來或會面,亦與常情無違,此觀其於案發前之同年 8月22日利用LINE向同學表示其與被告分手後,因感孤單、想有人陪伴或有講話之對象,故仍與被告藕斷絲連,但很清楚已不愛被告等情亦明(見原審卷一第156 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其等分手後,名義上雖非男女朋友,實則仍維持性關係,自難僅憑其等分手後尚有往來乙節,推論其等於案發時係合意性交,而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至A女斯時是否明知A母遇害或已悉被告有殺意,均無礙於其已因被告上述作為而陷於極度恐懼、無助、難以逃脫、不敢反抗之狀態下、違反自己意願與被告為性交行為之認定。辯護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 ㈦辯護人雖曾為被告辯稱:被告因認已為 A女繳交學費,並向友人借貸供A女花用,遂取走上開1萬元現款抵償,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意圖云云。然被告先前為 A女繳交之學費,已於案發前進行還款協議時扣除 1萬元,此為被告所明知,是辯護人謂被告因繳交 A女學費而取走該筆現款抵償云云,已非無疑。另被告雖曾於102年8、9月間以A女欲裝牙套為由,向江定達、蘇軒立分別借款3000元、5000元,復以繳納電話費為由,向魏伯翰借款3000元等情,固據證人江定達、蘇軒立、魏伯翰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然被告向其等借得之款項,究否確供 A女所用,此除被告供述外,上開證人均未能證實,從而被告是否另貸金錢供 A女花用,亦有可疑。況被告係於A女與B女共同居住使用之房間內書架上之紙盒內發覺 1萬元現金,該筆款項則為B女所有乙節,亦據證人B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屬實,被告與A女在案發前交往多時,又曾協助A女搬家,衡情必當知悉該房間為A女、B女共同居住使用,主觀上應得想見該1萬元現款亦可能為B女所有,在不確定該筆現金實際歸屬之情形下,逕行竊走,主觀上自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至明,辯護人此部分所辯,亦非可採。 ㈧至辯護人另為被告辯稱:被告當時僅單純不希望紅色長方巾、紅色無袖上衣、女用內褲等物留在現場被發覺,故而帶走該等物品,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意圖云云。惟其明知上開用以擦拭A母手指甲縫之紅色長方巾1條、擦拭 A女鼻血之紅色無袖上衣1件、A女身著之女用內褲 1件、置於A女與B女共用房間垃圾桶內已遭撕毀之上開協議書殘片等,俱屬其在上址住宅內取得之物,均非其所有,竟仍加以取走而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益徵其主觀上就該等物品確有竊盜之不法所有意圖甚明,縱係基於掩飾罪行而為,亦僅屬犯罪之動機或目的而已,無礙於竊盜犯意之認定,辯護人此部分所辯,亦無可採。 ㈨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查被告於102年9月17日入伍服役,行為時係現役軍人,此有新北市陸軍常備兵徵集令、兵(役)籍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三第99至 103頁)。核其所為擅自持鑰匙開啟門鎖侵入上址住宅部分,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住宅罪,絞殺 A母部分,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5款、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對A女強制性交並故意絞殺A女部分,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刑法第226條之1強制性交故意殺害被害人罪,竊取 1萬元現款及紅色長方巾、紅色無袖上衣、女用內褲、已遭撕毀之協議書殘片等物部分,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按強制猥褻與強制性交,係不同之犯罪行為,行為人若以強制性交之犯意,對被害人實施性侵害,先為強制猥褻,繼而為強制性交,其中強制猥褻行為係強制性交之前置行為,不容割裂為二罪之評價,則強制猥褻之階段行為自應為強制性交行為所吸收(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964號判決意旨參照)。如前所述,被告於前揭時、地係先強制猥褻 A女、繼而對 A女強制性交,其強制猥褻之階段行為,應為強制性交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公訴意旨雖以:被告基於殺人、強盜之故意,以絞殺 A女之方式,實施強暴,致A女死亡而不能抗拒後,在A女房間內翻箱倒櫃物色財物,而取走上開現金1萬元,應依刑法第332條第 1項之強盜故意殺人罪論處云云。惟查證人即查獲本案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偵查隊副隊長黃明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和隊長至命案現場初步勘查,前陽台有掛桿子,晾著女性衣物,並無遭侵入、衣物掉落之跡象,亦無破壞痕跡,女兒房間衣物也很整齊,沒有翻動跡象,故排除竊盜殺人之可能性,當時沒有做財物清點;是我們把被告帶回分局,初步查證到一段落後,因B女害怕進入現場,我們陪同A父、B女至A女房間拿一些衣物、行李要離開,B 女找放錢的位置,才發現少 1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36頁反面至第237頁、第238頁),參以證人B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後伊回家整理物品時,發現 A女皮包在地板上,而被告所簽發之本票仍在A女皮包內,除上述1萬元外,伊並無其他損失等語,苟被告於入侵之際,即有強盜殺人之故意,在其殺害 A母後等待A女返家期間,暨殺害A女後,理當仍有充分時間四處翻動、搜刮財物,豈有維持現場整齊、且遺漏上開本票未取走之可能?至被告與 A女間於案發前雖有前述金錢糾紛,然尚難執此推論被告侵入A女住宅之際,即有取財之意。再者,A女原本要求被告返還20萬元,然其等間於案發前之102年9月29日達成被告返還9萬元予A女之協議,並由被告之姊夫簽立同面額之支票交付 A女等情,業如前述,是依協議內容以觀,A女僅取回9萬元,已較原本請求之20萬元少取11萬元,該項協議形式上既對被告有利,被告似亦無潛入 A女住處盜取該協議書加以撕毀或盜回該支票之動機,從而其供稱該協議書係 A女所撕毀、棄置於垃圾桶內乙節,亦非無稽。是其於案發後離開現場之際,雖竊走該已遭撕毀之協議書之殘片,然被告供稱:該協議書為 A女所撕毀丟棄於垃圾桶內,係伊於取走垃圾桶內擦拭精液用之衛生紙團時一併取走乙節,亦非無可能。是綜觀上情,難認被告於侵入A女住處、殺害A母、A 女之際,即有以殺人為手段而強盜財物之犯意,此外,復查無證據足認其有強盜殺人之意,依罪疑唯輕法則,應認其係於殺害A女後,為掩飾罪行而清理現場之際,發現上開1萬元現金,始生竊盜故意,而竊取該筆現款及前述紅色長方巾、紅色無袖上衣、女用內褲、已遭撕毀之協議書殘片等物。公訴意旨認被告應依強盜故意殺人罪論處,尚有未洽,惟其竊盜部分與公訴意旨所指強盜部分(即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盜取 1萬元現金)之社會基本事實仍屬同一,本院自應予審理,並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㈣至A父曾具狀指述:被告侵入住宅藏匿等待A女返家後強迫 A女發生性行為,構成刑法第 222條第1項第7款之侵入住宅強制性交罪云云。而被告固係於侵入住宅後,對 A女為強制性交犯行,然查無證據足認其於著手侵入住宅之加重條件之際,即已萌生對A女強制性交之犯意,自應僅論以刑法第221條第 1項之強制性交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無從遽以侵入住宅強制性交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相繩。另公訴意旨業已敘及被告持先前取得之鑰匙,開啟 A女住處大門而侵入其內之犯罪事實,僅漏載起訴法條,此部分又已據 A父提出告訴,本院自得併予審究。 ㈤又刑法第55條明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為想像競合犯,所謂一行為,係指基於一個意思決定,實施一個自然意義上之行為而言。被告以一竊盜犯意,而在密切接近之時、地,竊取B女所有之1萬元現款、A 女所有之女用內褲及已遭撕毀之協議書殘片暨 A女其他家人所有之紅色長方巾、紅色無袖上衣等物,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其以一行為竊取前述物品,而侵害數財產法益,屬想像競合犯,應從一竊盜罪處斷。又公訴意旨雖未敘及被告竊盜紅色長方巾、紅色無袖上衣、女用內褲及已遭撕毀之協議書殘片等物,然此部分犯罪事實與前揭經論罪科刑之竊取 1萬元現款部分有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併予審究。㈥被告所犯上開無故侵入住宅、殺人、強制性交故意殺害被害人、竊盜等 4罪之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再按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減刑,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苟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犯罪嫌疑人始向之坦承犯行者,為自白,而非自首。又所謂發覺,不以有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僅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亦屬發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69號判決意旨參照)。證人即查獲本案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重陽派出所所長林宏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後我先到場,副隊長黃明福之後才到場,因黃明福詢問家屬,家屬有反應死者有一男友剛分手,且有財務糾紛,黃明福有轉告我,我們才會針對死者男友進行查緝,黃明福再帶家屬到被告家裡查,黃明福已經出去外面找人,而我們原本在案發大樓樓下做警戒,隔壁棟大樓頂樓有個住戶下來跟我們報案說他那棟大樓頂樓好像有聲音,請我們上去查看,我才去案發大樓頂樓,發現被告,被告當時趴在地上,稍微蹲下,並無戴口罩,我問被告在頂樓做何事,被告答稱他在樓下上班,上樓時樓梯被反鎖,沒有辦法下去,我對被告說「沒關係,我從隔壁樓梯帶你下樓梯」;要下樓梯時我有詢問被告身分,請被告出示證件,被告出示健保卡給我看,我就知道被告名為黃麟凱,但我當時還不知 A女男友姓名;因被告躲在頂樓,我覺得很可疑,事實上沒人會在頂樓,且被告在頂樓好像有流汗的樣子,臉上又有抓痕,蠻可疑,所以我帶被告下樓後,趕快打電話通知黃明福副隊長過來查證被告是否我們要查證的被害人男友;被告當時沒有跟我講他就是我們要找的人,我也沒有詢問被告傷怎麼來的;事後偵查隊通知我們再去頂樓搜索,查獲一包東西等語(見本院卷第232至236頁),證人黃明福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我於102年10月1日下午6時40分許,接獲110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溪尾街○號2樓有不明死亡案件,約3分鐘後林宏明打電話跟我說他那裡發生死亡案件,他在案發現場看到確定有 2人不明死亡,請我們過去支援、偵辦,我大約 7時10分許抵達現場,初步向A父瞭解狀況,A父說她太太、女兒被殺害,A 父懷疑是小偷侵入行兇、竊盜殺人,我打電話通報我們隊長,隊長抵達時,我與隊長進去現場逐一勘察,因 A父說小偷可能是由前陽台進入行兇,但我們勘察前陽台,前陽台有掛桿子,還晾著女性衣物,並沒有被侵入、衣物掉落之跡象,亦無破壞痕跡,女兒房間、衣物也很整齊,沒有翻動跡象,所以初步排除被害人家屬所提竊盜殺人之可能性,又因被害人一個是媽媽、一個是女兒,經我們向 A父瞭解,媽媽是單純家庭主婦,生活、交友狀況單純,沒有什麼外力因素,我們向A父瞭解女兒的交往狀況,A父有提到女兒有交一男友,最近剛鬧分手,所以我們懷疑是熟人所為,目標就轉移到A 女的熟人身上,我直接問A父那名與A女分手之男友是誰,但 A父因工作較忙,對女兒的生活不清楚,就跟我說另外一個姐姐B女比較清楚,當時B女陪同A母至新光醫院急診,我 們請林宏明派人去新光醫院將B女帶回現場,B女回到現場樓下後,我就跟B女表達我的懷疑,我問A女男友現在狀況如何及姓名為何,B女就說A女男友名叫黃麟凱,住址不清楚,只知道住的地方大概是三和夜市附近,但詳細地址不清楚,我當時請B女帶路,跟我一起去被告家中,大約晚間近9時許到達被告住處,我們按電鈴,被告之母在家,但剛開始都不開門,我們表達我們是警察,有事要找被告,被告之母認為可能是詐騙集團,所以不開門,後來我們請當地派出所制服員警一同前往,才到達被告樓上住處,當時只有被告之母一人在家,我告知來意說A女跟A母已被殺,因當時被告剛好當兵休假回來,我們懷疑是被告所為,同時我們害怕如果真是被告做這事,被告可能會輕生,屆時本案就無相關跡證,故請被告之母幫忙找人,被告之母說也不清楚當時被告人在何處,大約 9點半時,被告姊姊下班回家,我們也請被告姊姊聯繫被告,結果被告姊姊打電話給被告,問被告人在何處,被告答在蘆洲跟朋友吃飯,我就接過電話,向被告表達我們警方找他的用意,並告以「你女友被殺,是不是你做的,我們希望你配合警方調查,如果不是你做的,就還你清白」,請被告告訴我們人在何處,被告就說在蘆洲跟朋友吃飯,不方便與我們碰面,電話就掛了,我就請被告姊姊再打第二通電話問被告到底人在何處,被告答跟朋友在蘆洲附近修車,也不告訴我們人在何處,我當時就直覺懷疑可能就是他。因為我們急著找被告,所以我們請被告姊姊陪同去蘆洲找被告,順便送B女回家,等我們車子回到命案現場樓下,B女剛下車,林宏明就打電話給我,請我過去第二個樓梯,因為現場是第一個樓梯,林宏明是在第二個樓梯,算是雙拼建築的第二個樓梯,我就過去,進入樓梯間,看到林宏明與被告在一起,我問林宏明這個人是誰,林宏明就把被告健保卡拿給我,我一看,就是我們要找的人,我當時很生氣,就問被告為何要騙我說在蘆洲跟朋友吃飯、命案是否他做的,他回答不是,我問他為何在現場,他回答說「我為什麼不能在現場」這一句很無厘頭的話,我看他臉上有抓傷,我問他這個傷痕怎麼來,他回答我是被養的狗抓傷的,但我一看那個是指甲抓傷的傷痕,因為依照我們判斷的經驗,指甲寬度大約 1公分,被告被抓的傷痕差不多也是指甲 1公分的寬度,如果是狗的話,因爪比較尖,所以傷痕只有 1條,比較小,不可能會有這麼大的面積,所以我跟被告說「你不要騙我」。因為依照我們的經驗,兇殺案的動機是情、財、仇,財的部分,我們看過現場後已經初步排除,仇恨的部分,被害人交往單純沒有仇恨,剩下情的部分,我們原本認為 A女男友在當兵,可能就不是他了,但之後B女跟我們說A女男友現在結訓、放懇親假,這幾天有回來、有碰面,所以我們就鎖定是他,我在被告家中跟他通電話,我跟他說「你女友死了,事情很重大,希望不是你做的,既然你有接電話,希望你趕快出來配合幫忙提供線索」,他電話中就說「我很忙,沒有空」,很消極的應付我們,我們返回現場時,我到第二個樓梯看見被告臉上抓痕,而且又是在案發現場發現被告,所以我們覺得八九不離十,判斷是被告,就問被告說是否承認、自白可減刑,但被告當下說不是他做的。之後因現場還有很多記者,不方便再深入追問,我打電話給我們隊長,隊長從第一個樓梯那邊趕過來,我跟隊長就把被告帶上偵防車,要帶到分局深入瞭解,在車上我們跟被告講「命案已經發生,要給死者一個公道,如果是你做的,你就要勇敢承認,如果不是你做的,你就提供線索來幫死者申冤」,剛開始被告否認,但在車上約 5分鐘後,被告就哭了,承認事情是他做的。林宏明有再到頂樓查看,發現一塑膠袋,打電話告訴我們,我們請鑑識人員去現場依照鑑識採證標準採證、分析。另外,我到命案現場作初步勘察時,沒發現被害人這邊有財物損失,現場非常整齊,沒有翻動跡象,所以當時沒做財物清點,是我們把被告帶回分局,初步查證到一段落,因B女害怕進入現 場,我們陪同 A父、B女到A女房間拿一些衣物、行李要離開,B女找放錢的位置,才發現少1萬元,當下我在現場就打電話給分局偵辦小隊長,請小隊長詢問被告有無拿這 1萬元,後來小隊長向我回報說被告承認他身上的 1萬元就是在現場拿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36頁至第239頁反面),是警員黃明福據報前往案發現場後,雖尚不知悉被告有侵入住宅、殺害A母、對A女強制性交後殺害A女、竊盜等犯嫌,然其後詢問A父、B女後,獲悉被告甫與A女分手,乃聯繫被告出面說明並追查被告下落,然被告推託其詞,拒絕透露確實行蹤,迨黃明福接獲林宏明通報,至案發現場鄰棟大樓樓梯間,見被告臉上有遭人類指甲抓傷痕跡,又係在案發現場頂樓發現其人時,對被告係侵入住宅殺害A母及A女之犯嫌,已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懷疑,自堪認已發覺被告之犯嫌,因而當場詢問被告,然被告初始否認犯行,直至遭黃明福帶回警局途中,始坦承為下手行兇之人,復於B女發現1萬元款項遭竊而告知黃明福後,經黃明福轉知承辦員警詢問被告,被告始供認行竊並在其身上扣得該筆現款,是被告既未在為警發覺其為犯罪嫌疑人之前,向警告知犯罪,難認符合自首之要件。辯護人謂被告應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云云,亦無可採。 ㈧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並敘明: ⒈就侵入住宅、竊盜部分: 審酌被告係以殺害A女之犯意而侵入A女家中,對於A女、A母及其家人之家宅安寧構成重大威脅,且在侵入後陸續絞殺 A母、A 女,其侵入住宅之前行為,應予嚴加非難;另於清理現場之際,發現A女房中有現金1萬元而加以竊取,並為掩飾其罪行,同時竊取用以擦拭 A母指甲縫細之紅色長方巾、擦拭A女鼻血之紅色無袖上衣及A女身著之女用內褲暨在房間垃圾桶內發現之已遭撕毀之協議書殘片等物,兼衡所竊之財產價值、造成被害人之損害,且被告前此並無遭刑事判決科刑紀錄,素行尚可,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暨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犯後坦承侵入住宅犯行,迄未取得被害人原諒,亦未補償被害人等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侵入住宅、竊盜部分,各量處有期徒刑10月。 ⒉就殺害A母、對A女強制性交並故意殺害A女部分: ⑴我國於98年 4月22日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業於同年12月10日施行,依上開施行法第2條、第3條分別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之效力,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1項明定: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任何人不得無理剝奪。而死刑之剝奪生命,具有不可回復性。且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而現階段之刑事政策,非祇在實現以往應報主義之觀念,尤重在教化之功能,立法者既未將殺人之法定刑定為唯一死刑,並將無期徒刑列為選科之項目,其目的即在賦予審判者能就個案情狀,審慎斟酌,俾使尚有教化遷善可能之罪犯保留一線生機。故法院對於泯滅天性,窮兇極惡之徒予以宣告死刑之案件,除應於理由內就如何本於責任原則,依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審酌情形,加以說明外,並須就犯罪行為人事後確無悛悔實據,顯無教化遷善之可能,以及從主觀惡性與客觀犯行加以確實考量,何以必須剝奪其生命權,使與社會永久隔離之情形,詳加敘明,以昭慎重。 ⑵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標準應以:犯罪之動機、目的、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與被害人關係、危險損害程度、犯後態度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並顧及比例原則和平等原則為整體之評價,俾使罪刑相當。而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法定刑範圍從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至死刑,可裁量之範圍極廣,另刑法第226條之1之犯強制性交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法定刑範圍為無期徒刑、死刑,亦有裁量之必要,尤其在僅剝奪人身自由之「無期徒刑」與完全剝奪生命權之「死刑」之間,雖均得用以防禦無教化可能之人對社會之潛在危害,但刑法第57條並未提供可茲法院在此二者間選擇之具體標準。根據國內學者之比較法研究成果,外國立法例上所定殺人罪量刑考量因素以可責性、社會保障與犯後態度三個概念為據,其中可責性概念包括預謀犯罪、手段惡性、被害人年齡、犯罪與被害人關係、武器的使用、弱勢被害人、殺害特定職業(如警察)、受雇殺人、重罪結合犯、犯罪時有兒童或老人在場、其他實質危害(家屬傷痛、社會影響)、殺人動機為貪念、被害者的責任、為隱藏其他犯罪、為政治目的而殺害政治人物、行為人判斷力減弱、行為人為青少年或老人、行為人不幸背景、行為人身心障礙、受被害人刺激、為保護他人而殺人等項,社會保障概念有犯罪前科、緩刑或假釋狀態等,犯後態度則包含認罪、犯後行為(滅證、毀壞屍體)、犯後悔悟等(賴宏信,求刑與量刑歧異性與量刑標準之探索;以0000 -0000年之殺人罪為例),其所考量之因素,均較我國刑法第57條之規定具體。因此,法院於行使刑罰裁量之決定行為時,除應遵守憲法位階之平等原則,公約保障人權之原則,以及刑法所規定之責任原則,法理上所當然適用之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以及各種有關實現刑罰目的與刑事政策之規範外,更必須依據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而為適當之裁量。於法定刑包括死刑之案件,如考慮選擇科處死刑,本於恤刑意旨,除須符合上開諸項原則外,其應審酌之有利與不利於犯罪行為人之科刑因素,尤其刑法第57條所例示之10款事由,即應逐一檢視、審酌,以類似「盤點存貨」之謹密思維,具實詳予清點,使犯罪行為人係以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人」而非「孤立的犯罪人」面目呈現,藉以增強對其全人格形成因素之認識,期使刑罰裁量儘量能符合憲法要求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所應遵守之「比例原則」。如科處死刑必也已達無從經由終身監禁之手段防禦其對社會之危險性,且依其犯罪行為及犯罪行為人之狀況,科處死刑並無過度或明顯不相稱各情,且均應於判決理由內負實質說明之義務,否則即難謂其運用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之情形符合所適用之法規之目的,而無悖乎實體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審酌: ①被告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單親家庭出身、自幼由母親獨力扶養長大,行為時已入伍服役,為現役軍人,家庭經濟狀況非佳,未婚,本案之前未曾有遭刑事判決科刑紀錄,素行尚可,其與 A女為就讀高職之同學,於99年間交往成為男女朋友,102年7月間協議分手後,雙方仍有往來,被告經常性接送 A女,企圖挽回彼此關係,是其等間有相當感情,難謂疏離,竟僅因A女向其追討二人交往期間其所提領A女帳戶中之金錢,A女與A母並於其入伍服役後,向其母當面追討金錢之怨,即預謀攜帶童軍繩、頭套、手套、襪子、身穿黑色長袖高領上衣變裝掩飾身分,潛入A女住宅,欲以童軍繩絞殺A女,於潛入A女住宅後為A母發覺時,未放棄殺人犯意而離去,竟因主觀認定A母瞧不起其單親家庭之身分,且為免A母呼救,而痛下殺手,以童軍繩絞殺A母,此後並持續潛伏A女家中,等待A女返回後,即偷襲A女加以壓制綑綁,甚且在 A女發現其真實身分後,不顧已絞殺A母在前,竟乘A女前已遭其綑綁壓制等極度恐懼無法反抗之下,違反A女意願,對A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其後繼續遂行其殺害A女之犯意,而將A女絞殺,足見其欲致 A女於死之意甚堅。其視人命如草芥,採極端之絞殺方式,與A母並無怨隙,即遷怒無辜之A母,且在絞殺A母後,全無道德罪惡之感,猶在屋內另一房間對A女強制性交,所為已全無良善人性,危害社會秩序至深且鉅,犯罪手法殘酷、泯滅天良,罔顧他人生命,造成 A母、A女冤死,A父家庭破碎,夫妻、父女及母女、姊妹從此天人永隔。被告於案發後、警偵及原審審理時雖均坦承殺害A女、A母,然仍否認部分事實,並未全然坦承犯行,亦未提及對於死者家屬民事損害之填補。辯護人雖曾於原審審理時提出被告所抄寫之經本,謂被告欲迴向給被害人(被告所抄寫經本 6冊置於原審證物袋內),被告並曾書寫道歉信寄予 A父、C女、D女、B 女,惟因遷址而遭退回,此有該等信件(含信封)在卷可按(見原審卷三第37至48頁),被告亦曾親寫道歉信件請求原審轉交 A父,惟被害人家屬拒絕接受等情,亦有該等信件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三第159、160頁),被告當庭欲向被害人家屬道歉,亦未獲被害人家屬接受(見原審卷二第 244頁),然未見被告有何實際填補損害、賠償之具體作為,故被告雖寫信或當庭欲向死者家屬道歉,但不足以慰撫死者家屬身心之傷害,死者家屬仍心痛至極。 ②經原審囑託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沈勝昂對被告進行心理評估鑑定結果,認被告目前對自己犯行深表懊悔,並表達改變之動機,然其自我反省仍屬較表淺的,對導致自己犯案的不成熟人格及缺乏心理彈性、情慾上的控制感強以及反社會特質,較少有能力瞭解到,因此對於問題的探索仍顯現逃避面對的傾向,對犯案細節及當時心理歷程仍未有清楚覺察,談及未來如何改變時,仍偏狹地以功能性、物質性滿足來彌補對方,少對自己不成熟與偏差的身心狀態有了解的企圖,這可能因被告對「鑑定結果」的不安與可能的負面影響有關,然這正好也反映被告犯案原因如出一轍的狀態(高壓下的偏狹與不理性所產生的失控)。因此,在目前長期監禁和教化之外,也必須提供適當心理治療來協助其對自己問題的覺察、改變以及長遠生活型態之重建,否則以目前身心狀態(性格、人際互動模式、壓力因應與情緒調節),一旦遭遇類似情境,容易有再犯之情況發生,此有心理評估鑑定報告在卷可按(見原審卷二第 212頁)。鑑定人沈勝昂於原審審理時復證述:再社會化是一個很抽象的名詞,伊的解釋是說如果這個人進入矯治機構,有沒有辦法從現在的心理健康狀態、人格的特質經由矯治單位教化處遇;以被告情況來看,他性格上有些弱點,如果他情緒不穩定,面對問題時,如面對分手時,他一直想要挽回,又面對金錢的壓力下,人格特質就凸顯出來;矯治單位如果只提供職業的復建,道德的教育,伊認為不夠,被告無法理解到其人格上弱點;伊的理解應該是沒有人去幫被告把這件事情談清楚,被告遇到特殊事件時,事件帶來的張力,會凸顯其人格的弱點,用比較極端的方式去處理,目前的矯治單位無法提供這樣的治療方式,目前監獄並無對有暴力、情緒困擾的人去做深度的治療,這段時間被告沒有做這樣的治療,被告也只是知道自己錯了,但對這件事情理解是表淺的;如果提供適切治療,被告是否可以再社會化是一個雙方面的問題,對被告而言,如果被告有意願、動機去瞭解自己,也要有能力;另外需要一個受過完整訓練的精神科醫師或臨床心理師在穩定、長期、安全的環境下從事治療,還要考慮花多少時間從事治療,最後即使是在醫院接受治療,回到社會如復發又會回來,伊不知道假釋讓犯人受到法律上處罰後回到社會,有無機會去練習或有一個完整的支援去練習恢復,伊在醫院看到這個人正常的,為何幾天後又回來,是因為社會環境裡面沒有好的人或好的環境讓他可以維繫這樣行為,即使治療後還是要有一個好的心理治療模式讓他維繫,這樣的改變就會比較完整;再社會化不是在監獄,而是在社會中,如果在治療過程中,對於關係的理解或操作方式,沒有得到好的結果,又遇到這樣的關係、壓力,他又回到原來的性格習慣,這是一個層面很廣的問題,而且是很大的工程;至於被告有無動機、意願、能力去瞭解自己,在被告的情況一定會向伊表示他有動機,被告一直很擔心鑑定或審判的結果,被告這方面的擔心以致無法好好思考是不是在哪裡出了問題,看守所也無法提供這樣完整的機會,至於意願,也是伊剛才的說法,至於能力部分,這與再社會化是同樣的難題,被告因為現在的狀況,對於問題的理解並不是很好,不只對事實理解不好,被告對其心理狀態的理解也沒有很好,如果被告要透過心理治療,相對要花很大的力氣,伊無法回答再社會化需要花的時間、資源、人力,但一定要花很大的力氣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226至227頁)。 ③檢察官、死者家屬、被告及辯護人分別表示意見如下: 檢察官於原審審理論告時陳稱:被告犯案之起因係不滿 A女向其追討金錢,即以殘忍手段殺害A女及A母,對於被害人、被害人家屬造成之損害既深且鉅,被害人家屬經歷此劫難,身心、生活回復正常軌道之可能性渺茫,而被告犯後僅坦認部分犯行,並未真心悔悟,僅為求減輕罪責,辯解荒誕,犯後態度不佳,又犯殺人、強盜與強制性交等罪章之罪者,近年迭有假釋中再犯、交保後再犯或執行完畢後再犯等情形,而被告經鑑定結果,亦認被告遭遇類似情境,容易有再犯之情狀發生,此有心理評估鑑定報告可佐,請審酌上情,依法判處極刑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242頁反面)。 告訴代理人陳稱:A女及A母之死亡,導致被害人家庭破碎,被害人家屬所受傷害極大;被告之陳述恐有污名化死者之嫌,被告所述只為脫免刑責,可見其並無深刻反省。從歷次偵審中亦看不出被告有真心的道歉,評估報告中也提到被告的道歉是表面的,而先前被告所書寫寄予被害人家屬之 4封信件內容大同小異,如出一轍,是機械化的贖罪儀式,被告顯然並無深層認知自己的行為有多麼罪大惡極,而被害人家中並非篤信佛教,被告也提到自己是基督徒,不斷地抄寫佛經,這樣的道歉徒具形式,僅屬表面,被告為脫免一死而做的機械性道歉,其有無教化可能性,值得懷疑,且心理評估鑑定報告提到,其一旦遭遇類似情境容易有再犯可能性,輔以鑑定人沈勝昂教授之證述,目前矯治機關無法提出如此的心理治療,若不把被告與世永久隔絕,被告顯然有極高再犯可能性,被告不欲改變且攻擊性高,感情、金錢為被告重要需求,被害人家屬已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被告要面對龐大的金錢債務,卻無法有效的對被告進行任何教化,顯然將來再犯可能性、尤其是對被害人家屬報復可能性極高,任何人有免於恐懼生活的需求,被害人家屬面對此情,刑法應適度反應出正義功能。被告所犯為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屬兩公約及一般性意見中提出之「情節最重大之罪」,而被告並無教化可能期待,請依法將之與世永久隔絕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3至244頁)。 A 父陳稱:請求判處被告死刑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244頁)。 C 女陳稱:我們怕的要死,會覺得有人跟蹤我,我看見繩子都會害怕,請用法律保護我們,我只想好好活下去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4頁)。 D 女陳稱:希望判處被告死刑,伊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之中,還會夢到繩子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4頁)。 B 女陳稱:只要殺人兇手活在世上,我們全家人的性命每天都處於瀕臨死亡當中,被告不死,我們都會面臨死亡,我不知道我們要怎麼活,我要媽媽及妹妹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4頁)。 被告供稱:感謝心理評估鑑定,讓伊可以認識自己,伊才知道伊是多麼不成熟的人,才會一錯再錯犯下大錯,透過鑑定知道自己多可惡,讓伊看清過去犯下的錯誤,也會去做治療,伊對不起被害人家屬,未來不管判刑如何,這都是伊罪有應得、伊該受的懲罰。伊想請法官給伊一次機會向被害人家屬道歉,伊之前的道歉都沒有到達被害人家屬手中,後續道歉部分,伊會在修復式司法中完成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2頁反面、第244頁)。 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陳稱:被告從小失去父親,與媽媽二人生活,姐姐就像另位母親,三人感情很好,案發時被告剛滿20歲不到10天,甫入伍 A女就到被告母親上班地點理論,加上自己與A女藕斷絲連的情感、財務糾葛及A女平時提到家裡不贊成單親家庭,一時情緒激憤,犯下大錯。被告為警查獲後,即配合警察尋找相關證物,並寫下自白書,協助釐清案情,在冷靜後相當後悔,被告寫道歉信、書經表達悔意,被害人家屬雖不能接受,被告可以理解,被告知悉法務部宣導修復式司法溝通平台,請辯護人協助尋找相關資訊,現已透過看守所輔導員向地檢署聲請,辯護人向被告表示修復式司法與案件分開進行,判決後仍可進行,判決也不會等待修復式司法進行,且被害人家屬是否接受,不得而知,但被告願意接受、願意進行,希望透過實質的修復程序,而非物質上或空泛看到的道歉,盡量協助被害人慢慢走出陰霾,此舉表示被告於接受新資訊後,確能改變自己,或許還不夠,但會繼續努力,另鑑定人提到許多教化方向、具體的心理治療方式,並認為是有可能再社會化,因此被告並非絕無教化遷善之可能,依最高法院實務見解及兩公約規定,希望勿處死刑,倘認有永久隔離之必要,亦可以無期徒刑代替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242頁反面至第243頁)。 ④人權團體雖有主張廢除死刑,然一般國民及學者專家反對者猶屬多數,在全體國民尚未達成共識及修改法律前,法院仍應忠實依據法律規定妥慎量處適當之刑。 ⑤審酌上開各情,再衡諸我國一般國民對法律應實現社會公義、良知、人性普世價值等之期待與認知,被告僅因個人男女朋友關係破裂及與 A女交往期間金錢糾紛,在無法獲得其母完全支持解決該金錢糾紛之下,即視人命如無物,預謀殺害A女,顯露極其自大、自我、自私、無知之性格,且因侵入A女住處為A母發覺,恨上心頭而遷怒A母,為免 A母呼救,即行絞殺A母,令人髮指。復於殺害A母後,在 A母陳屍於房內之際,猶在A女返回後,在A母陳屍之隔壁房間內,對 A女強制性交,所為顯已泯滅人性,後再將 A女絞殺,造成其等家庭破碎,並致死者家屬驟失親人之痛,悲憤難當,對死者家屬形成無可彌補之傷痛、恐懼,死者家屬對被告所為迄今仍無法宥恕。被告手段極其兇狠,僅因男女朋友交往上情感之破滅及10、20萬元之金錢糾紛,即率爾犯下重大難容之犯行,在在顯示其惡性重大至極。其於原審已坦承殺人,僅對強制性交、竊盜等部分事實有爭執,雖足以認定其在某程度「知錯」,有認錯並欲向被害人家屬道歉,然於本案審理期間未聞被告有對己身行為深切反省,被告對於本案起因係其將A 女辛苦打工賺取之金錢提領花用之不當乙節並未表示反省,所謂道歉亦止於行為後所造成 2條人命之殞逝及被害人家屬之傷痛,然對於其本身人格、心理上之重大缺失及泯滅人性之反社會人格,均未見深切檢討,其否認強制性交犯行暨所為之辯解等,雖係其正當防禦權之行使,卻也顯露其僅因鑄下大錯面對重典而表示反悔,未有誠實面對己身所為之重大惡行,徹底檢討,尚難認其已有悛悔之實據。參以鑑定人沈勝昂之鑑定結果,除目前長期監禁和教化之外,必須提供被告適當心理治療,協助其對自己問題的覺察、改變以及長遠生活型態之重建,而目前監所之情況,無法提供適切之心理治療,且接受心理治療後,仍須進入社會中,也要有好的心理治療模式維繫,治療後的改變始完整;況被告目前僅擔心己身因審判結果遭受不利,未曾深度瞭解自己目前人格、心理狀態,被告是否確有接受心理治療之真正動機、意願及能力,顯然有疑,如被告要透過心理治療,需花費很大力氣,鑑定人沈勝昂亦無法評估再社會化所需花費之時間、資源、人力,尤以被告未徹底悔悟、面對己非之前,足見對於被告之教化顯非易事。綜上所述,被告因侵入 A女住處之際,為A母發覺,即行絞殺A母,單此犯行,即應量處無期徒刑。其後俟 A女返家,僅因區區男女朋友間之情感、金錢糾紛,即對A女強制性交並殺害A女,且在殺害A母後,隨即對A女強制性交、殺害 A女,行為極端惡劣,泯滅人性,倘不與社會永久隔離,則日後重返社會,恐再度僅因人際往來細故有所不滿產生壓力,即以相同手段侵害他人生命權或為其他侵害之可能性極高,是對A女所犯強制性交並殺害A女部分,如僅量處無期徒刑,顯然輕縱,非但不足以還死者及家屬公道,亦不足以撫慰死者家屬失親之痛,為維護社會秩序及確保民眾生命安全,被告此部分所為,有永久與世隔絕之必要,求其生而不可得,不得不施以極刑對待等一切情狀,就此部分量處死刑;並依刑法第37條第 1項規定,就此二罪刑部分均併宣告褫奪公權終身,暨定其應執行死刑,褫奪公權終身。⒊扣案鑰匙 2支,為被告所有、供侵入住宅所用,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所犯侵入住宅罪刑項下宣告沒收;童軍繩3條,為被告所購買、其中1條實際供絞殺A母、A女之用(另 2條則屬預備供殺人犯罪所用之物,原判決就此漏未載明,應予補充),頭套1個、黑色長袖高領上衣1件及手套、襪子各 1雙,均屬被告所有、供被告變裝以免遭人認出或留下指紋、腳印等跡證以遂行殺害A母、A女所用之物,均應依同款規定,分別於所犯殺人、強制性交故意殺害被害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至手電筒 1個、被告所穿著之白色上衣、黑色長褲、內褲及其購買童軍繩等物之統一發票 1張等,僅屬本案證據,而非供犯罪所用之物,均不予宣告沒收等旨。㈨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尚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㈩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就被告殺害 A母部分,證人陳金美證稱:「(問:A母與你對談關於被告花掉A女金錢的事情,態度有不好,或是口出惡言嗎?)沒有,A母說讓被告與A女自己處理好就好了」等語,而據被告自承 A母未曾對其口出惡言,則被告究出於何種動機,潛入 A女家中,先以童軍繩勒死與其無怨無仇之A母?被告描述殺死A母之情節,於偵查中略謂:伊一進去後,A 母在房間躺椅上休息,伊先看到她,一開始不知要如何下手,A 母看到伊,開始哭喊,伊先用雙手抓住A母脖子,A母反抗,抓伊右臉頰,伊用手肘壓制 A母雙手,順手拿起右邊的童軍繩,從正面繞了一圈脖子就出力;約過十多分鐘,A母就停止掙扎;伊確定A母「沒有脈搏」後,躲進廚房等情;嗣其於移審時改稱:起訴書記載我以童軍繩綑綁絞住A母脖子部分,剛開始沒用童軍繩,之後A母有反抗動作後,我才用童軍繩勒住她脖子,但時間沒很長,力氣沒很大,當下她還有很大呼吸聲,之後我想說她昏迷過去,就沒再對她做任何動作。A女返家之前,A母都還有呼吸聲,A女返家之前,我在廁所,A母在房間,我並沒有躲在廚房,起初我想離開,因我臉上有傷,所以我到廁所去照鏡子,我就隨手拿方巾去擦拭A母指甲,我擔心我臉部的皮屑留在A母指甲內,當時她都還有呼吸聲等語;被告兩次陳述雖不同,且隨時間經過避重就輕,意圖減免刑責,然綜合被告就殺死A母之說法,已足證其殺死A母並無強大之動機,僅為與 A女之金錢上爭執,於潛入A女家中時,任何在A女家中之人,均為其犯案目標,實為毫無差別之殺人,A 母之死亡,即無差別受害者之一,被告犯罪之動機,顯無宥恕之餘地。且 A母為一家精神支柱之母親,被告並為 A女之前男友,被害人家庭生活單純,A 父為工人階級,所賺取之薪資不多,僅足溫飽,名下並無不動產,一家人倚靠租屋為居所,雖擁擠但仍不以為苦,案發地點亦為搬入不久之處,A 母為家管,平常操持家務,除買菜或辦理雜事,很少離開家中,故 A父返回家中,按電鈴未見A母答門,即感大事不妙。A父本即患有精神方面之疾病,並需 A母陪同定期進行戒酒癮之治療,家中女兒均為半工半讀,獨立負擔自己學費,甚而協助 A父負擔家計,命運對此家庭雖無優待,然一家和樂融融,且知足常樂,努力在其等能做到的範圍內,各司其職。4名女兒與A母感情甚篤,A 母就像任何疼愛子女之母親一般,雖對子女之工作及學業無法給予實質幫助,然在其能力範圍內,關懷子女之食、衣、住、行,此有 A母生前傳予子女關於交代晚餐事項等數封簡訊可證,被害人家庭「辛苦並認真」在社會上打拼,雖無錦衣玉食,然一家人團聚心靈上之富足,完全不輸其他家庭,此有被害人家屬所提供之闔家出遊相本可參,被害人家庭即係刑罰法律制訂保護之對象:使善者有所倚恃。然因被告之行為,相片中令人欣羨之全家團圓景象完全崩裂,造成生存之父及 3名姐妹患有精神上之疾病,難以從打擊中復原,此有被害人家屬之診斷證明及心理諮商證明在卷可證,被告奪取者,不僅死者之生命,尚有生者之健康及闔家之夢想,此種傷害將跟從生者一生,永難完全復原。被告所造成之損害,不僅限於被害人家屬終身之遺憾與傷心,更甚者,C 女於庭外陳述:我們現在已經換了一個租屋,希望不要讓被告知道地點,我們也不想要收到被告寄送的任何東西,我們其實來開庭都很害怕,害怕看到被告的眼睛,感覺他好像會隨時出現在我們家中,現在要回家,我們要三姊妹在樓下集合,一起上去,我們不敢一個人回家,我們非常害怕被告,只要他可能有自由的一天,家人就處在恐懼當中,怕會遭到報復,連開庭我們都壓力很大等語;被告犯罪所造成之損害,不僅以殘忍方法奪走 A母性命,同時也奪走生還家人之勇氣與對未來之希望。被告於刑事訴訟法上本即有自辯之權利,然此一權利之行使並非毫無界限,倘若在事實明確之下,仍為許多不合理、事實上不可能之辯解,即屬犯後態度審認之範圍。被告所犯滔天大罪,若能對於犯行之動機與犯案情節詳加坦承,承認自己所為是錯,並誠心接受制裁,可能勉強告慰死者在天之靈,並或多或少撫慰被害者家屬之氣憤與不甘之情。然被告犯後對於不容否認之殺害 A母事實,尚且於移審時辯稱:A 母部分伊不是故意的,伊起初只是要捆綁,沒有傷害之意,後來因肢體衝突導致 A母死亡云云,雖最終就殺人事實坦認,然已對生存之被害者家屬沉痛之內心再劃下深刻傷痕,參以被告犯後湮滅證據之行為,可知被告就殺人部分坦認,僅係為減免自身罪責,並非出於真心悔悟,且鑑定結果亦提及「詢問個案(即被告)的心得,表示如果有機會重來,他會更努力的滿足對方的需求。判斷個案的自省仍屬於較表淺的,仍只想到用物質滿足來彌補對方」、「被告雖然對犯案的確深表悔意,但是仍有逃避面對問題的傾向(如對判刑的不確定、擔心或害怕),對於犯案細節及當時的心理歷程尚停留在表淺的層面,對深入的探究仍有所保留」等意見,足見被告雖經 1年之偵、審程序,仍未能深切反省自身,坦然面對過錯,心中所念想者為判決結果,益徵被告就部分犯行坦認,僅係為減免自身罪責。是被告犯案之起因僅不滿前女友 A女向其追討不法所得,即以殘忍手段殺害 A母,對於被害人、被害人家屬造成之損害既深且鉅,被害人家屬經歷此劫難,身心、生活回復正常軌道之可能性渺茫,而被告犯後僅坦認部分犯行,並未真心悔悟,僅為求減輕罪責,犯後態度不佳,經鑑定結果,亦認被告遭遇類似情境,容易有再犯情狀發生,原審就此部分僅量處無期徒刑,罪刑是否相當,非無研求餘地。又從 A女家人所提供A女生前自拍相片觀之,A女背後為其與胞姊共同居住之房間,其內如一般女性居住情形,色彩多樣繽紛,照片左側之開放式衣架上吊掛整排衣物,有其擺放之次序,非如案發現場照片顯示遭翻箱倒櫃之貌,亦足認被告侵入被害人住處後,有花費相當時間翻動屋內物品搜尋財物之行為,方能於A女房間內書架上紙盒內發現1萬元現金,再依被告於警偵審中供述之情節,其殺害 A女後未久,旋聽聞有人欲開門之聲響,衡諸經驗法則,此時理應心慌不已,亟欲逃離現場,斷無可能、亦無充裕時間於此時搜尋、翻找財物,已可合理推論被告搜尋財物之行為係於殺害A母後、A女返家前約莫 1小時之期間內,是其不法所有之意圖絕非殺害 A女之後方萌生。又其侵入被害人住處犯下本案,起因於102年9月29日之協商,其侵入被害人住處之目的,即係欲以不法手段解決與A 女間之債務關係,已堪認其侵入住宅之際已有不法所有意圖,而以強制性交並殺害A女為手段,使A女不能抗拒而強盜財物,是被告主觀上具有出於事先計劃以殺人、強制性交為手段再行強盜之包括認識,客觀上取走財物與殺人、強制性交間,亦有時間上之銜接性、地點上之關連性,原審單憑被告片面之詞,認定被告係於殺害A女後方尋得、取走1萬元及協議書,忽視被告於殺害 A女後已無時間翻找財物之客觀情狀,遽論被告係於殺害 A女後另行起意竊盜財物,此部分認事用法,尚有未洽云云。惟查: ⒈所謂「無差別殺人」,指一種罪犯完全臨時起意之犯罪行為。亦即使用之犯罪工具、犯罪對象、犯罪地點及時間都無特定之安排。正是因為「臨時起意」,在斷案中,辦案人難以把時間、地點、工具等作為突破口,亦即這些因素都是無差別而無特定指向。因此,在現實中,這類無差別犯罪更加考驗辦案人之經驗、法醫科學之完善。本案被告與 A女原為男女朋友,分手後於案發前有金錢糾葛,A母則為A女之母,於案發前更曾陪同A女向被告之母洽商還款事宜,是被告與A母彼此間並非互不相識、全然陌生,而被告原基於殺害 A女之意,侵入A女住宅後,沿屋內走道欲前往A女房間時,行經 A母房門口,偶見A母在房內躺椅上休憩,因遭A母發覺,且主觀上思及 A母瞧不起其單親家庭出身及過往對其態度冷漠等情,故而萌生殺害A母之意,遂以原備供殺害A女用之童軍繩勒斃A母,是依被告與A母間之關係、被告殺害 A母之時間、地點、動機、目的、所使用之工具等情以觀,與所謂「無差別殺人」仍屬有別,復無證據足認當時在場者如係 A母以外之人,亦必遭被告殺害,是上訴意旨謂在 A女住處之人均為被告犯案目標,被告係無差別之殺人云云,實屬臆測。又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業於理由內具體說明其審酌之根據及理由,顯係基於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明顯失出失入之違法或不當,就前揭上訴意旨所指被告犯案動機僅因不滿前女友A女向其追討金錢,即以殘忍手段殺害A母,對於被害人、被害人家屬造成至深且鉅之損害,犯後僅為求減輕罪責,坦認部分犯行,並未真心悔悟,經鑑定結果,亦認其遭遇類似情境,容易再犯等情,原判決亦於理由內敘明已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犯罪後之態度等旨,又被告於訴訟程序中,雖曾為避責而就部分犯罪情節供述不一,然於警偵審中均已供承殺害 A母犯行,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惡性、所生危害、犯罪後之態度、對被害人家庭所造成無可回復之傷害程度等情,就被告殺害 A母之部分,量處無期徒刑,難謂有何明顯悖於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失之過輕之違法或不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罪刑不相當云云,亦無可採。 ⒉本案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於侵入住宅之際,即有強盜取財之意,依罪疑唯輕原則,即應從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業如前述,上訴意旨徒以被告殺害 A女後未久即聽聞開門聲,衡情斷無可能、亦無充裕時間於此時翻找財物為由,推論被告係於殺害A母後、A女返家前約 1小時內搜尋財物,復以殺人、強制性交、取財等行為時間上之銜接性、地點上之關連性,推論被告係事先計劃以殺人、強制性交為手段行強盜,於侵入住宅之際已有盜取財物之意云云,洵屬臆測。至被害人家屬提供之A女生前自拍相片顯示A女房間內物品擺放情形,與案發後現場狀態縱有不同,然該等照片既係於案發前所攝,能否據以推論 A女房間於案發時之樣貌,亦非無疑,是上訴意旨執此而謂被告花費相當時間翻動屋內物品搜尋財物云云,亦非可採。 ⒊從而,檢察官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就侵入住宅部分量處有期徒刑10月,無非係以被告進入 A女住宅之行為,係其後續行為之前行為,應嚴重非難;惟關於後續行為,如非在進入住宅時即有圖謀,而係臨時起意,則該侵入住宅行為是否應嚴重非難,即有可疑,況被告取得鑰匙尚無違法可言;又原判決既認被告進入住宅為一危險前行為,且係後續行為之前行為,而後續行為乃屬故意犯罪,則被告對於防止前行為結果之發生,並不具備保證人地位,於事實上亦無期待可能性,是原判決此部分論罪科刑,或有速斷。再就竊盜部分,被告對於殺人犯行既已坦承不諱,本無須就竊盜乙事加以遮掩或否認,而由被告之母所述,足見被告確在入伍前為 A女繳納學費及多筆款項,且由A女與被告間協商債務之對話內容,A女亦不否認帳戶金錢有部分用於 A女個人花費,尚有二人交往中共同分擔之花費,尤以證人江定達、蘇軒立、魏伯翰之證述,可見被告於 102年 9月間幾乎同一時間內向其等借得共 1萬1000元,證人蘇軒立並證稱:被告蠻急的,所以伊叫被告來伊家樓下拿錢等語,足見被告主觀上認 A女對其負有債務,並非虛妄,況依罪疑唯輕法理,公訴人之舉證既無法證明被告取走 1萬元現金,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原審遽認被告有竊盜犯意,顯屬速斷。另參諸鑑定人沈勝昂所述,足證被告確仍有教化遷善之可能,且被告自幼失怙,與母相依為命,感情極佳,案發時甫成年未逾旬日,兼以剛入伍服役,面臨生活、生命中之巨大轉折點,尚不及調整心情,聽聞 A女至母親上班地點理論,未顧及母親是在包子店工作、只要一上線就不能停手,加以被告之母已一再向 A女表示無法請假離開崗位、希望等下班後好好談,A 女卻一再打斷、使母親在工作場合丟臉,且因糾紛越發劇烈,被告與 A女之情份恐已無挽回餘地,被告一時情緒激憤失慮始鑄下大錯,但自遭警查獲後,主動協助警方尋找相關證物,並在警方要求下配合書寫自白書,就客觀事實全盤托出,以利檢警偵查,於羈押時亦主動抄寫心經,除沈澱原有戾氣俾能修身養性之外,亦望迴向給被害人等,且因自知對被害人家屬有愧,偵查中雖未面對被害人家屬,惟起訴後進入審判程序,被害人家屬均到庭,被告深感悔恨,情緒衝擊之鉅,又不知該如何當面向被害人家屬致歉,亦知再多抱歉均無法彌補不能挽回之生命,被害人家屬無法接受,乃情所當然,且關於被害人家屬提出之附帶民事請求尚未審理,被告尚無法進一步對被害人家屬表示賠償方式,原審就前開部分漏未審酌,難謂科刑已盡「盤點存貨」式全盤考量云云。惟查: ⒈被告係基於殺害 A女之犯意侵入住宅,並非侵入住宅後始臨時起意,是原判決於科刑時審酌被告係以殺害 A女之犯意而侵入住宅,後又絞殺A母、A女,則侵入住宅之前行為應予嚴加非難等情,並無不合,因而判處有期徒刑10月,亦難謂有何量刑過重可言,上訴意旨徒憑己見,謂:被告對於防止前行為結果之發生,並不具備保證人地位,於事實上亦無期待可能性云云,顯屬無稽。 ⒉被告竊取B女所有之1萬元現款,主觀上確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業據本院敘明理由如前,其於本院審理時復已就竊盜部分自白、認罪,則其上訴意旨否認竊盜犯罪,要無可採。 ⒊按刑罰之目的,不外應報與預防,前者重在對於被告自由意志決定下所產生之犯罪行為,由國家施以對等之惡害,作為平衡。後者則在儆戒世人免蹈犯罪覆轍(一般預防),及對犯罪人之社會再適應,使之出獄後能減少犯罪,更生再返社會,暨社會隔離,使其不能侵害社會(以上為特別預防)。此外,對犯罪人施以適當刑罰,亦兼有填補被害人及其親屬心理情感上之痛苦。今日社會之家庭教育式微,學校及青少年教育之不週、社會風氣敗壞等,均為犯罪行為之種因,其影響個人人格之程度,固有不同,然犯罪者基於自由意志所為犯行,亦不應歸咎他人。而死刑為剝奪犯人生命法益,使犯罪人與社會永遠隔絕之刑罰,量刑時尤應謹慎考量犯罪之性質、犯罪人動機、行為態樣、犯行之執拗與殘虐性、危害程度及被害人數、被害人遺族情感痛苦程度、犯罪行為對社會影響程度、犯罪人年齡、犯罪人素行及其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倘其犯罪行為惡性重大,破壞社會秩序,且行為人窮凶極惡,絕無再教育矯正之可能,即有處以極刑使之與社會永遠隔絕之必要。本院審酌: ⑴被告與 A女原為男女朋友,於102年7月間協議分手後,仍有聯繫、互動,然因 A女在與被告交往期間,曾將打工所得薪資轉帳帳戶之提款卡交付被告保管,並授權被告從中提領款項供A女日常花費之用,迨同年9月間發覺該帳戶款項竟遭被告提領殆盡,所剩無幾,亟欲取回款項,適逢被告於同年 9月17日入伍服役,A女與A母只得急洽被告之母索討20萬元未果,嗣被告休假離營返家後,因A女催逼索款甚急,深覺A女對金錢錙銖必較,未念舊情,態度極差,又對其母不同意全額資助金錢供其返還 A女乙事甚感憤怒,然亦覺愧對其母,而無法面對 A女離去所帶來之痛苦及陷於緊張之母子關係,產生極大壓力,未能自我反省 A女之所以急於向其及其母索款,全因其任意提領、揮霍半工半讀之 A女辛苦打工賺得之薪資,竟不思己過,歸咎於A女,對A女極為怨憤,萌生以殺害 A女之方式解決上述問題之意念,旋於當晚購買童軍繩,供日後殺害A女之用,復因與A女達成還款9萬元之協議後,A女仍持續要求其返還餘款11萬元,此舉加深其無法面對與 A女間情感破裂及母子關係緊張之壓力與憤怒,促使其決心殺害A女,遂持備用鑰匙,蒙面、變裝後侵入A女住處,欲前往A女房間之際,行經A母房門口,為在房內躺椅上休憩之 A母發覺,詎其僅因主觀上認 A母瞧不起其單親家庭出身及過往對其態度冷漠,即萌生殺害A母之犯意,以雙手掐住A母頸部、阻止A母出聲呼救,復以手肘壓制A母雙手後,以童軍繩纏繞A母頸部再使力勒斃A母,而殺之滅口,為避免事跡敗露,又至屋內浴室拿取紅色長方巾,擦拭A母手指甲縫,以去除A母生前因反抗而抓傷其右臉頰、殘留在手指甲縫之皮屑、血跡,後潛伏在屋內廚房,等待 A女下班返家後,又蒙面偷襲、制伏A女,將A女帶入房間內,以同一童軍繩反綁 A女雙手,後因A女乘隙發覺其身分,其雖應A女要求為 A女鬆綁,然於明知其與 A女間因財務糾葛,其原本亟欲挽回之感情已難回復,竟萌生強制性交犯意,利用 A女因遭其上述作為而陷於極度恐懼、無助、難以逃脫、不敢反抗之狀態,親吻並撫摸A女,再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後,為免東窗事發,復以童軍繩勒頸方式,務必殺之滅口,其前後行為過程持續相當時間,犯意甚堅,且手段兇殘,惡性重大,又於行為後竊走相關物品,欲湮滅證據、避人耳目,行為過程未見懊悔、憐憫之心,足認被告心性兇殘,視人命如草芥,視法律如無物,所為對被害人及其家屬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助長暴戾之風,影響民心,危害社會治安甚鉅,犯後復未能坦承強制性交犯行,亦未對被害人家屬為任何實質賠償,復未能提出具體可行之賠償方案稍事撫慰被害人家屬並供本院審酌,僅於上訴意旨空言:關於被害人家屬提出之附帶民事請求尚未審理,被告尚無法進一步對被害人家屬表示賠償方式等託詞,口惠而實不惠。 ⑵又被害人家屬 A父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家本來很單純,我太太很好,我養20年的女兒,我努力賺錢養 4個女兒,被告真的很可惡,殺我太太、女兒,當時有被我太太抓傷臉,然後逃到頂樓要逃走,之後被警察抓到,他殺的是好人,應該被判死刑,沒有判死刑,社會就沒有公道等語(見本院卷第193 頁),A女之雙胞胎姊B女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跟妹妹的感情很好,我們每天都睡一起,妹妹遇害的樣子我每天都聽得到,因為我們長的一模一樣,我們會做的事情、講的話全都一模一樣,我還是會做夢夢到妹妹,覺得我好像回到那個時候,親眼看到妹妹被套頭、四肢被綁住,然後痛苦不已,一直尖叫,還被性侵的樣子,我超痛苦,連平常在看新聞,看到有人戴著頭套當下我都會崩潰,一直哭,誰可以瞭解我和妹妹的痛等語(見本院卷第203頁反面至第204頁);C 女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每天都作惡夢,我都夢到媽媽及妹妹是在很不甘願的情況下死亡,我們常常睡不好,我們 4個都有在看精神科,吃鎮定劑、安眠藥,這兩年都沒有停過,我去看病時常常會想說我是得了什麼病嗎?但是不去看醫生又不行,請法官幫我們主持公道等語(見本院卷第 204頁);D 女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們每天都生活在緊繃、恐懼當中,這兩年從來沒有間斷過,每天都很害怕,只要開庭,精神都很緊繃、緊張,每天都要吃安眠藥、鎮定劑,只要想到這件事情,或是每次開庭去看筆錄、書狀,去看被告瞎講的這些事情,我們必須要去回復,很多人叫我們站起來,我們想要站起來,但是沒有辦法站起來,還是要一直去回顧,好像是身歷其境,這件事情永遠在我們心裡面,我們是女兒,父親年紀已大,我們手無縛雞之力,只能請法官幫我們主持公道,我們沒有辦法,被告復仇心這麼重,他出監後,死的會不會是我們剩餘的家人?我覺得我能想像有這麼一天,我們是不是只能移民或等死,他在監獄裡面我們壓力已經很大,我們無法想像他如果出來我們如何生存。我們還要上班,要調適我們的心情,生活有經濟壓力,不能不去上班,那我們能夠死嗎?也不能死,我們要幫媽媽、妹妹求一個公道,我們不能死。我們知道我們可以不用來開庭,但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要我們讓這件事過去嗎?不可能,這件事是我們的全部,我們只能一直勉強自己,我也很擔心我自己會發瘋,但我們家人已經非常脆弱,還經得起任何事情發生嗎?發生事情之前我父親已經有吃精神病的藥品,發生事情後我們剩下的 3個女兒也都在吃藥,沒有一個人是正常的,我不敢想像這件事情是發生在我自己身上,每次睡覺睡不著時,我都不敢回想這件事情,只要回想我就會很害怕,在家裡只要有風吹草動,我們都會想門是不是沒鎖,如果有社會新聞,我們也不會有勇氣、心情去看,我們能避免就避免,回家後家裡都是暗的,我們一定都會先把家裡的燈打開,然後檢查所有的房間、浴室、廚房、廁所,全部都看過沒人,然後再看誰還沒回家,就會打電話給他確認他人在哪裡,我們兩年的生活非常痛苦,只想幫媽媽、妹妹討一個公道,我們只是致力做我們為人之女應該做的事情,希望法官、檢察官可以幫我們,在法律上給我們支持,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因為我們不能讓他死,我們自己也不能死,只能請求法官、檢察官在法律上給予被告嚴厲刑度,現在我們在法律上爭取我們的權益,被告出來後,是不是就會找我們,讓我們死呢等語(見本院卷第204至204頁),足見被告潛入被害人住處以童軍繩連殺兩命,對被害人家屬所造成之身體、心靈之創傷、痛苦極為深鉅,被害人家屬恐將長期活在本案所帶來之驚懼不安陰影下。 ⑶再參酌前揭鑑定人沈勝昂所為之心理評估鑑定結果暨其於原審審理時所述,顯見被告目前雖對自己犯行深表懊悔,並表達改變之動機,然其自我反省仍屬較表淺的,對導致自己犯案的不成熟人格及缺乏心理彈性、情慾上的控制感強以及反社會特質,少有能力瞭解,因此對於問題的探索仍顯現逃避面對之傾向,對犯案細節及當時心理歷程仍未有清楚覺察,談及未來如何改變時,仍偏狹地以功能性、物質性滿足來彌補對方,少對自己不成熟與偏差之身心狀態有了解之企圖,此可能與被告對「鑑定結果」之不安及可能之負面影響有關,然這正好也反映被告犯案原因如出一轍之狀態(即高壓下的偏狹與不理性所產生的失控)。故除目前長期監禁和教化之外,尚須提供適當心理治療,協助其對自己問題的覺察、改變及長遠生活型態之重建,否則以目前身心狀態(性格、人際互動模式、壓力因應與情緒調節),一旦遭遇類似情境,容易有再犯之情況發生。又所謂「再社會化」,係指犯罪行為人進入矯治機構後,經由矯治機構之教化處遇,改變其原有之心理健康狀態及人格特質等,被告能否「再社會化」,除需被告有「意願」、「動機」、「能力」瞭解自己外,尚須受過完整訓練之精神科醫師或臨床心理師在穩定、長期、安全之環境下對被告進行心理治療,迨被告恢復正常,回歸現實社會環境後,仍須持續擁有好的心理治療模式以維繫其正常行為,否則一旦面對類似之壓力、關係,極易回復原形(原有之性格習慣)。被告雖向鑑定人聲稱有「動機」、「意願」瞭解自己,然被告面對目前之審判程序,定會表達有此動機及意願,因被告一直擔心鑑定及審判結果,以致無法好好思考問題,被告對問題之理解(包括事實理解及自身心理狀態之理解)不佳,惟我國目前矯治單位「並未針對有暴力、情緒困擾之人提供深度心理治療」,故被告是否有「能力」瞭解自己,與「再社會化」面臨相同之難題,如欲透過心理治療矯正其行,使其再社會化,必需耗費極大之時間、資源、人力。是依被告之情形,雖未能「完全排除」矯正及復歸社會之可能,然需配合長期且專業之心理治療,始能達成,以我國矯治機構並無提供此等心理治療之教化處遇方式觀之,已足認被告在矯治機構中導正其心性、行為之可能性「微乎其微」,幾無矯正之可能。 ⑷被告雖於年僅 1歲餘時生父即過世,由其母獨力扶養,本案行為時甫滿20歲,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真的很對不起兩位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因為我犯下的錯誤,深深傷害他們及他們的家屬,我真的非常後悔,也知道自己做錯,一定會好好面對該負起的責任,犯下的錯誤,都照實坦承,但沒有違反 A女意願,我們當下真的是合意,我這麼說並不是為了要減輕我自己的罪責,只是要把當下最真實的情形說明清楚,做錯的我都全部坦承,也願意接受一切該有的懲罰,真的很對不起被害人家屬,對不起等語(見本院卷第 250頁),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鑑定人認為對被告的教化可能是很大的工程,依據現在監獄實務可能無法達成,但就算是很大的工程,代表被告還是有教化可能性,因為國家做不到,或是國家依照現在的制度做不到,這是國家的責任,不能歸在被告身上,應該是由國家去改進,被告的行為不對,造成被害人家屬痛苦,這都是被告造成的,但被告的行為、責任要由國家用刑罰來制裁,我們覺得無期徒刑就可確保被告一直在監獄內執行,有人可能提到無期徒刑可能假釋,但假釋有一定程序、要件,並非時間到了,就一定要讓被告假釋,還要經過相關評估、判斷,符合條件後才可假釋,在此機制下,應可確保被告再社會化之可能性等語(見本院卷 249頁反面、第250頁正、反面)。然查被告殺害A母後,本有充裕時間得以醒悟,拋棄原先欲殺害 A女之念,正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然其竟捨此不為,執意殺人,終至兩條寶貴生命殞落,其對A女強制性交、殺害A女之過程已如前述,犯罪手段之凶殘,令人髮指,犯後猶有心思仔細滅證(擦拭 A母指甲縫細、竊走相關證據等),且身在看守所羈押中,仍未能深切、真心悔過,猶因擔憂本案審判結果而僅口頭上表示懊悔、認錯,其所謂「悔悟」,實屬表淺,難認有悔改之真意及矯正之可能;又其雖出身單親家庭,然母、姐對其疼愛有加,其亦完整接受小學、國中、高職等正規教育,此除為被告所不否認外,並有上開心理評估鑑定報告可稽,其狀況與一般問題家庭出身者(多半缺乏家人關愛、輟學)尚屬有別,亦難將犯下重罪之責任歸咎於家庭、學校、社會、國家。是本院斟酌再三,仍認其罪無可逭。再按被告所犯強制性交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而無期徒刑經執行逾25年,經認有悛悔實據者,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監,刑法第77條第 1項定有明文。是除死刑外,無期徒刑亦有假釋之可能,然依實務所見,假釋出監者再犯比率甚高,被告甫滿20歲,犯罪手段竟如此凶殘,則監獄教化對被告是否有效,尤應予審酌,衡諸前述心理評估鑑定結果,對被告最為有效、治本而非治標之教化方式既係長期且專業之心理治療(協助其對自己問題的覺察、改變及長遠生活型態之重建),我國矯治機構又無提供此等心理治療,已足認監獄對被告並無教化效果,至辯護人指此乃國家之責任,應由國家改進云云,固非無見,然對受刑人之矯治、教化,需耗費人力、物力,在國家資源(預算)有限之情況下,照顧眾多較受刑人更為弱勢之族群猶力有未逮,更遑論依鑑定人所言,被告即便出監後,仍須終其一身持續擁有「好的心理治療模式」以維繫、確保其正常行為,從而,國家有無必要耗費如鑑定人所稱「很大的力氣」、花用預算、投注時間、人力在矯正被告之上,亦非無疑,是關於監獄之矯治教化處遇措施,既涉及國家之政策方向、有限資源之分配、價值選擇等重大議案,自不得單以「此乃國家之責任」一語簡化此一難題,更不得將國家無法耗費過多資源教化被告乙事,全然歸咎於國家。故被告如執行無期徒刑經假釋後出監,仍為40餘歲之壯年人,若再為惡,將使對之為無期徒刑之判決者背負「伯仁因我而死」之重責,遑論被告出監後如未持續接受適切之心理治療,一旦面對類似本案之情境,極有可能重蹈覆轍,尤以被告尚須面對被害人家屬之鉅額求償,日後倘遭被害人家屬索債(亦即類似本案遭 A女催討款項之情形),難保其在此金錢壓力下,絕不致回復原有之「高壓下的偏狹與不理性所產生的失控」之偏差身心狀態,而對他人再犯重罪,故被害人家屬陳述其等自案發後恐終其一生擔憂、恐懼自身安全乙節,似非全然無由。是我國刑事政策雖不採應報主義,亦有認死刑不宜執行者,惟本院認除非修改法律、增訂不得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刑人只能老死獄中,否則僅死刑始能真正將被告永遠與世隔離,故判處被告死刑,並非僅以應報主義為出發點,而係考量被告年紀尚輕,對 A女犯案手法即如此凶殘,完全泯滅人性,倘僅處以無期徒刑,因監所生活規律,誘惑較少,故其獲假釋之機會甚高,是就被告可能改過、再社會化之機率與被告可能再犯、又侵害他人之機率兩相權衡,仍認以保護社會不特定人之安全為要,就其所犯「強制性交而故意殺害被害人」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罪部分,確有處以極刑、永遠與世隔離之必要,以昭炯戒,並保善良。 ⑸至被告所犯前開「強制性交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依刑法第91條之1規定,雖尚有接受輔導、治療,於鑑定、評估認 有再犯危險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之治療處分制度。其徒刑執行部分,倘受無期徒刑執行,固亦須於徒刑執行期間接受輔導或治療,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者,始得依同法第77條規定,在有悛悔實據,並執行逾25年之情形下,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之機會。惟人類大腦結構複雜,欲「瞭解」、「覺察」個人之精神狀態、心理活動及思想、意念形成、性格特質等,已非易事,更遑論「矯正」重大之性格弱點,一旦出現嚴重心理疾患,「治癒」之可能性微乎其微,況誠如前開鑑定人所述,實務上不乏已接受治療、看似恢復正常之人,離開矯治處所、回歸現實社會後未久即故態復萌,而被告甫成年即為此重大惡行,其犯罪心思之縝密,處處可見,在監所接受有效心理治療所需耗費之資源又過於龐大,實務上亦顯不可行,其矯正可能性甚微,退步言,縱被告極其幸運獲得適切輔導、治療並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而假釋出獄後,仍須終其一生持續擁有「好的心理治療模式」以維繫其正常行為,確保治療成效,然其出監後是否不間斷接受治療,已非前開刑法第91條之 1規定之範疇,一旦未持續接受有效之心理治療,面對類似本案之情境,極易再犯。是本院權衡各項法益後,仍認對被告所犯強制性交故意殺害被害人罪部分維持死刑判決,尚屬適當、必要。辯護人徒憑刑法第91條之 1規定,謂本案得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尚無永久與世隔離之必要云云,亦無可採。 ⒋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猶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金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9 月 8 日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葉騰瑞 法 官 莊明彰 法 官 陳芃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無故侵入住宅罪及竊盜罪部分,被告不得上訴。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佳芬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9 月 1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6條之1 犯第221條、第222條、第224條、第224條之1或第225條之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使被害人受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 現役軍人犯刑法下列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 一、外患罪章第109條至第112條之罪。 二、瀆職罪章。 三、故意犯公共危險罪章第173條至第177條、第185條之1、第 185條之2、第185條之4、第190條之1或第191條之1之罪。 四、偽造文書印文罪章關於公文書、公印文之罪。 五、殺人罪章。 六、傷害罪章第277條第2項、第278條第2項之罪。 七、妨害性自主罪章。 八、在營區、艦艇或其他軍事處所、建築物所犯之竊盜罪。 九、搶奪強盜及海盜罪章。 十、恐嚇及擄人勒贖罪章。 前項各罪,特別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戰時犯前二項之罪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