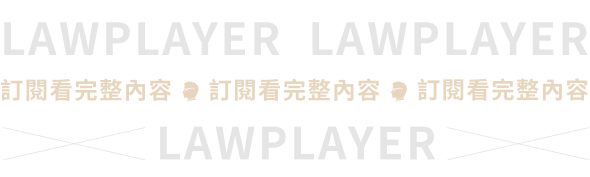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0年度訴字第42號
關鍵資訊
- 裁判案由貪污等
- 案件類型刑事
- 審判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 裁判日期96 年 12 月 21 日
- 當事人午○○、、己○○、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0年度訴字第42號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申○○ 巳○○ 國民 上列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劉 楷律師 被 告 午○○ 男 63歲 國民身分證 住桃園縣桃 選任辯護人 陳棋銘律師 陳適庸律師 被 告 癸○○ 男 48歲 國民身分證 住桃園縣平 選任辯護人 陳適庸律師 被 告 辛○○ 女 57歲 國民身分證 住台北市○○○路○段87號4樓 選任辯護人 林明輝律師 王怡惠律師 被 告 寅○○ 男 63歲 國民身分證 住桃園縣大 選任辯護人 呂傳勝律師 呂丹琪律師 被 告 壬○○ 男 41歲 國民身分證 住桃園縣楊 選任辯護人 吳仲立律師 林明輝律師 被 告 丙○○原名李文昌 男 43歲 國民身分證 住桃園縣蘆 選任辯護人 蕭佳灶律師 被 告 辰○○ 男 54歲 國民身分證 住桃園縣蘆 居桃園縣蘆 己○○ 女 50歲 國民身分證 住台中縣大 上列二人共同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辯護人子○○ 被 告 酉○○ 男 72歲 住桃園縣觀 選任辯護人 鍾儀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89年度偵字第11629號、89年度偵字第166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申○○共同連續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圖自己及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處有期徒刑捌年,褫奪公權捌年。所得壹仟貳佰伍拾肆萬玖仟參佰參拾元,應予追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以其財產抵償之。 午○○共同連續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圖自己及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處有期徒刑柒年,褫奪公權柒年。所得壹仟貳佰伍拾肆萬玖仟參佰參拾元,應予追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以其財產抵償之。 寅○○共同連續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圖自己及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處有期徒刑陸年。褫奪公權陸年。所得所得壹仟貳佰伍拾肆萬玖仟參佰參拾元,應予追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以其財產抵償之。 辛○○、己○○、巳○○、癸○○、壬○○、丙○○、辰○○、酉○○,均無罪。 事 實 一、緣民國八十二年至八十五年間,午○○擔任「經濟部工業局所屬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以下簡稱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主任,申○○為該中心副主任、寅○○為該中心環保組組長、卯○○(業於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病逝)為該中心業務組組員,均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當時適逢桃園縣地區垃圾風暴,清運廢棄物之價格高漲,申○○見有利可圖,遂邀集午○○、及寅○○,三人共同基於圖利自己及其他私人之概括犯意聯絡,由午○○出資新台幣(下同)二十萬元、申○○出資九十萬元、寅○○出資十萬元,另約定午○○、寅○○除固定於每年底分別分紅二十萬元、十萬元外,每筆工程尚分紅十至三十萬元不等。遂以不知情之巳○○(申○○之妻)、劉香妹(巳○○胞姊)、黃耀東(劉香妹之丈夫)、葉秀蘭(申○○二哥黎燕祥之妻)等人名義,於八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成立「超捷環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超捷公司),以劉香妹為名義上負責人,經營垃圾清運、廢水處理設備之設計及安裝等業務。利用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辦理一般廢棄物清運工程,及所屬污水處理廠有關納管工業區各廠商排放之污(廢)水,產生沈澱之污泥(屬事業廢棄物)清運工程,適用當時有效之「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例」(下簡稱「稽察條例」)及「工業區管理機構營繕工程暨購置定製變賣財物內部審核注意事項」(下簡稱「注意事項」),辦理年度招商委外清運之機會,對於其等應負主管或監督之下列事務,明知違背法令,規避稽察條例及注意事項之規定,夥同同有犯意連絡之卯○○(於審判中之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死亡,業經本院於九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判決公訴不受理),分別為以下行為: ㈠於八十二年間,由申○○向頂新清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頂新公司)負責人丑○○、林享河,以代支付百分之五發票稅金方式,商借頂新公司營業執照及台灣省環保處核發之廢棄物清運許可證,並於八十二年五月起,在申○○、午○○、寅○○之主導及授意下,規避「稽察條例」之規定,未以年度招標辦理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之一般廢棄物清運,共謀由申○○連續提供虛偽不實之廠商估價單,供業務組承辦人卯○○據以每月簽擬虛偽不實之公文簽呈,簽報「以詢價方式辦理,由最低價頂新公司清運」,並由申○○僱用其親叔叔,不知情之黎鎮湧負責將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之一般廢棄物,運往未向環保單位登記之申○○老家楊梅鎮高榮里北高山頂五之一號的垃圾囤積場處理。藉此以清運一般廢棄物為名,由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自八十二年六月七日起,至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止,連續多次支付清運費用,總計支付頂新公司(實由超捷公司領得)不法利益二百三十六萬三千四百五十五元,並足生損害公務文書管理之正確性及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 ㈡午○○、申○○、寅○○及卯○○食髓知味,復基於同前犯意,於八十四年二月七日,於超捷環工公司公司取得台灣省環保處核發之第一類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後,隨即取消與頂新公司借牌清運關係,再以與前相同手法,共謀由申○○提供虛偽不實之廠商估價單,供卯○○經不知情之業務組組長癸○○,呈簽由申○○、午○○等人層層簽准,委請超捷公司清運,致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連續於自八十四年二月十六日起,至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止,總計支付超捷公司一般廢棄物清運費用,共獲取六十一萬元之不法利益,並足生損害公務文書管理之正確性及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 ㈢八十五年七、八月間,超捷環工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遭臺灣省環保處撤銷許可證,午○○、申○○、寅○○及卯○○等人,即再基於同前共同圖利之概括犯意聯絡,共謀由申○○另向有蓄環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有蓄公司)洽借許可證,並於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再以申○○之妻不知情之巳○○名義收購有蓄公司,以巳○○任負責人,續以前述相同手法,共謀由申○○提供虛偽不實之廠商估價單,供卯○○簽報由有蓄公司清運,致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自八十五年六月二十日起,至同年十二月六日止,連續支付有蓄公司一般廢棄物清運費用,共計獲取四十九萬九仟二佰元之不法利益,並足生損害公務文書管理之正確性及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 ㈣緣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與領有第一類甲級廢棄物處理許可證(污泥年處理量八千噸以下,有效期限至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環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環瑞公司),連續於八十二年十月一日至八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八十三年十月一日至八十四年九月三十日,以每噸一千元清運費,委託環瑞公司清運所屬污水廠之污泥,雙方並分別簽定該兩年度之服務合同。豈料午○○、申○○、寅○○及卯○○等人,復基於同前共同圖利之犯意,在超捷公司於八十四年二月七日取得台灣省環保處核發之第一類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八四廢清字第0四二九號)後,即口頭告知所屬,環瑞公司因清運價格不敷成本,已片面毀約,隨即由申○○以月薪三萬元,僱用管理中心垃圾車司機不知情之李榮泉,以超捷公司名義,續以單價每噸一仟元清運費,轉由超捷環工公司清運,並在申○○老家楊梅鎮高榮里北高山頂五之一號,設立未經環保機關核准之廢棄物轉運站,以供囤積處理(廢棄物清理法當時並無處以刑事責任之規定)。寅○○、卯○○明知超捷環工公司之許可證上載明污泥日處理量僅有金聯製磚公司之七噸,卻仍准予超捷環工公司在每月請款之清運量統計單上虛偽填報不實之每日一、二十餘噸處理量,致不知情之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會計員呂幸說,分別自八十四年三月十六日起,至同年十月七日止,以污泥清理名目,支付超捷環工公司清運費。八十四年九月三十日結束與環瑞公司服務合同後,竟違反「稽察條例」及「注意事項」之規定,由寅○○刻意於九月三十日始上簽請求辦理招標,造成不及辦理公開招標之情事,先由申○○製作繕打「廢棄物清運處理合約書」,並於同年十月二日由午○○完成與超捷環工公司訂約用印手續,復由申○○提供偽造不實之大益環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益公司)、天良環保公司之廠商估價單,供卯○○據以於八十四年十月三日始補辦簽報以詢價方式辦理之內簽,委由超捷環工公司以每噸二千元處理費清運,致不知情之呂幸說又連續自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起,至八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止,再以污泥清理名目,支付超捷公司清運費。總計超捷公司獲取污泥清運費用達九百零七萬六千六百七十五元正之不法利益,並足生損害公務文書管理之正確性及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 ㈤總計午○○、申○○、寅○○、卯○○等人對於前述其等所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間接圖自己及超捷公司、有蓄公司私人總計一千二百五十四萬九千三百三十元之不法利益。 二、案經桃園縣調查站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部分 一、關於被告以外之人(含共同被告)於審判中之陳述 ㈠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就此定有明文。司法實務上向來以為,此處所稱「被告」亦包括「共同被告」在內,亦即共犯或共同被告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固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但此項不利之陳述,須無瑕疵可指,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者,始得採為犯罪事實之認定。縱可認其陳述無瑕疵,亦應調查其他足資以證明所供述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補強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若不為調查,而專憑此項供述即為其他共犯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顯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有違。足為代表之判例即為最高法院早於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及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兩件判例。換言之,前述法律及判例原則上均係肯定被告、共犯、共同被告之任意性自白具有「證據能力」,否則如不以此為前提,即無可能逕就「證明力」之部分有所限制。 ㈡惟按前述兩則判例肯定「共同被告之自白」對於他被告本人犯罪事實之證明,具有證據能力之見解,業經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公布之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宣告違憲。釋字五八二號解釋謂(略以):「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故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自不能因案件合併關係而影響其他共同被告原享有之上開憲法上權利。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及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判例所稱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證據一節,對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審判而言,未使該共同被告立於證人之地位而為陳述,逕以其依共同被告身分所為陳述採為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之證據,乃否定共同被告於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證人適格,排除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與當時有效施行中之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牴觸,並已不當剝奪其他共同被告對該實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利,核與首開憲法意旨不符。該二判例及其他相同意旨判例,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再援用」。換言之,前述兩則最高法院判例所認為,共同被告自白中對於他被告不利之事項,雖尚「應調查其他足資以證明所供述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補強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他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對於證據之證明力有所限制,惟討論證明力之限制,無異於「以承認共同被告不利他被告之供述具有證據能力」為前提,而有於法定五種證據方法(被告自白、人證、鑑定、勘驗、文書)之外,創設「第六種證據方法-共同被告」之嫌,是經大法官認為應將此時之共同被告列為證人,以保障遭共同被告不利指述之他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以符正當法律程序及保障被告之訴訟權。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之意旨,與同樣於九十二年九月一日生效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一、之二的規定,若合符節。按法院認為適當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或辯護人之聲請,以裁定將共同被告之調查證據或辯論程序分離或合併;法院就被告本人之案件調查共同被告時,該共同被告準用有關人證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一第二項、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分別定有明文。 ㈢又按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三,定有明文。又依據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項前段、第二百零二條規定,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定外,證人、鑑定人於陳述或鑑定前,原則上均應具結,以符法律明定之調查證據程序,始符嚴格證明法則。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00號判例意旨著有明文。告訴人、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告訴人之指陳,難免故予誇大,證人之證言,有時亦有予渲染之可能;然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台上字第一五九九號判例意旨亦著有明文。前述最高法院兩則判例,顯然於法律所明定之「證人」、「鑑定人」證據方法之外,另以判例「創設」「告訴人」此種證據方法,正如上述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兩則判例之意旨,另於法律規定以外,創設「共同被告」之證據方法相同,長期以來,受到有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嚴格證明法則」之質疑。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宣告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兩則判例違憲,其解釋意旨業如上述。依相同之意旨,前述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台上字第一五九九號、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00號兩則判例,肯定「告訴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法院亦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惟尚應調查其他證據證明之意旨,同樣有於法律之外創設「第七種證據方法-告訴人」之疑慮。此等判例(包括創設第八種證據方法-「被害人」之判例,例如業經最高法院以其他理由決議不再援用之該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二0三號判例),均於法律之外,創設法所不許之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方法,有違反嚴格證明法則,侵害人民訴訟權之虞。此等判例均應類推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之意旨,不應再予援用,而應回到證人、鑑定人之法定證據方法,始有踐行法定調查證據程序之可能。告訴人、被害人既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即屬於證人】,檢察官、法院於調查「告訴人」、「被害人」之陳述時,仍應令其具結,始謂合法。誠如學者所形容者:「嚴格證明法則猶如潘朵拉盒的據蓋子』,是啟蒙後現代證據法則的鎮箱法寶,從證據能力層次即先攔截未經合法調查的證據資料,避免其成為心證基礎;這個盒蓋有『三大法力』加持:一、僅許法院使用列舉的五種法定證據方法;二、必須依照各該證據法院的法定調查證據程序;三、應遵守直接、言詞及公開的共同審理原則」(參見林鈺雄教授,蓋上潘朵拉的盒子-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終結第六種證據方法,月旦法學雜誌第一一五期,第七四頁)。 ㈣查本院調查檢察官所提出之各共同被告陳述,業經分離審判,並於告以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得拒絕作證之旨下,被告本人均同意就他被告是否有為犯罪事實之情作證,而使各共同被告,就他被告之事項,均以證人之地位具結證述,並相互有對質詰問之機會,審判中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 二、關於被告以外之人(含共同被告)於審判外之陳述 ㈠按我國於九十二年九月一日之後,改採所謂「改良式當事人進行原則」,配合對於證人、鑑定人交互詰問之程序規定,於證據法則上,引進英美法系關於「傳聞法則」之規定,而與原有大陸法系之直接審理原則,並列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並於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之五,明定有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傳聞法則」與前述基於「嚴格證明法則」所要求之「法定證據方法」(及「法定調查證據程序」)限制,均屬於「證據能力」有無之要件,是以「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適有可能違反「嚴格證明法則」,以「證人」之法定調查方法為例,證人依法應「具結」並以「交互詰問」之方式調查其證言,否則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其證言自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三參見),惟如符合傳聞法則之例外,證人於審判外之警詢筆錄,仍具證據能力(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及之五參見),惟警詢程序中之證人依法無須具結,是以其證言筆錄,雖未具結,惟於審判程序中已合法例外具證據能力。同樣之情形,證人於審判外在檢察官或其他程序中法官前之陳述筆錄,雖依法應具結,惟因偵查程序中,一方當事人之檢察官即為訊問者,客觀上不可能踐行「交互詰問」,而其他程序中之法官前陳述(例如民事訴訟或少年事件程序等),依法亦不必以「交互詰問」方式為訊問,甚或該等證人於陳述時,所涉及之被告根本不在場,自無可能對之質問或詰問,惟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仍分別為「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及「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之例外具證據能力之規定。凡此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固然有違「嚴格證明法則」之法定調查證據方法(未行交互詰問),惟所謂「交互詰問」規定,係指當事人雙方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以次規定,所為之「輪流訊(詢)問」,其目的在透過被證人指控不利事項之被告之「反詰問」,以檢驗證人證言之可信性,換言之,其目的在發現證人證言之真實性,傳聞法則之發源國美國,該國學者證據法大師Wigmore 即採取所謂「真實性理論」 (Reliability Theory) ,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亦曾於多件判決中宣示採取此項見解。我學者認為此說有將傳聞法則憲法化之意味,在證據法稱「傳聞法則」,在憲法則易名為「對質詰問權」(參見王兆鵬,刑事訴訟講義,二00五年九月,初版,第六一四頁)。換言之,要求被告對證人行交互詰問,無寧係在保障被告之「對質詰問權」。㈡再按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不論於英美法系或大陸法系之國家,其刑事審判制度,不論係採當事人進行模式或職權進行模式,皆有規定(如美國憲法增補條款第六條、日本憲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四條、德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西元一九五○年十一月四日簽署、一九五三年九月三日生效之歐洲人權及基本自由保障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 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 第六條第三項第四款及聯合國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通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效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五款,亦均規定:凡受刑事控訴者,均享有詰問對其不利之證人的最低限度保障。足見刑事被告享有詰問證人之權利,乃具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在我國憲法上,不但為第十六條之訴訟基本權所保障,且屬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對人民身體自由所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之一種權利。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第五八二號解釋參見。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並謂:此等憲法上權利之制度性保障,有助於公平審判(釋字第四四二號、第四八二號、第五一二號解釋參照)及發見真實之實現,以達成刑事訴訟之目的。足見與前述美國證據法大師Wigmore ,及該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所宣示之「真實性理論」不謀而合,並同時扣緊被告憲法上「對質詰問權」之保障。 ㈢又按對質詰問權既為被告憲法上權利,基於其屬程序基本權之性質,且係為保障被告之權利,被告自得於資訊完整(例如國家機關盡詳盡告知義務)及有效明瞭其利弊得失之下,基於意思自主及意思自由原則,明示拋棄此項權利,憲法上當無不許之理。自法制層面觀之,我國訂有偵查中及審判中之協商程序(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以下參見),正係基於上述當事人(尤其被告)處分原則之理。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基於同意性法理所定之傳聞法則例外規定,亦係上述原則於法制上之體現。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雖不得作為證據;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其他法定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 ㈣綜上所述,本院以為,為保障被告憲法上之對質詰問權,刑事訴訟法關於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除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因被告不爭執之「同意性」要件,以及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之特信性文書外,餘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及之三之例外規定(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非典型之傳聞法則例外),因未設任何限制,或限制過於寬鬆,而有侵害被告對質詰問權之憲法上訴訟權保障範圍,並且如此廣泛承認此類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亦有違被告基於正當法律原則所得保障之對質詰問權。正如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理由書所言:「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含其他具證人適格之人)於審判中,應依人證之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至於被告以外之人(含證人、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依法律特別規定得作為證據者(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參照),【除客觀上不能受詰問者外】,於審判中,仍應依法踐行詰問程序」等語。是本院以為,證人、鑑定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如要在本案審判中取得證據能力,除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的同意性要件以外,否則必須被告於該程序中之對質詰問權獲得確保,亦即符合「先前的對質詰問權」法理,其於該程序向他法官所為之陳述,於本案審判中始有證據能力;如果審判外程序,被告對於證人等之對質詰問權未能行使,則該證人等在他程序向法官所為陳述仍不具證據能力,除另有「傳喚不能」(必要性)之要件外,本案審判中仍應傳喚該證人、鑑定人,使被告得以對之行使對質詰問權。換言之,審判外證人向他法官所為之陳述,如欲使用於本案審判程序,必須依法具結,並且該被告之詰問權曾獲得確保,亦即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九六條:「證人已由法官合法訊問,且於訊問時予當事人詰問之機會,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得再行傳喚」之規定,其審判外向法官所為陳述,始具證據能力。至審判外向檢察官所為陳述,基於相同理由,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除書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應結合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以被告之對質詰問權於偵查中獲得保障為前提,始具證據能力。總之,基於合憲解釋原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必須與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結合;第二項必須與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結合,實務上須以此目的性限縮之適用方式操作本條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否則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即可能發生違憲之結果。最高法院於九十五年八月十七日曾著有該院九十五年臺上字第四五五八號判決,有與本院上述意見類似之見解,甚具參考價值,茲抄錄該判決意旨如下(【】為本院所自行附加):「按刑事訴訟法為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及發現實體真實,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及增訂公布施行之前及之後,對於人證之調查均採言詞及直接審理方式,並規定被告有與證人對質及詰問證人之權利,其中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係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第十六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不容任意剝奪;故法院於審判中,除有法定情形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或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者外,均應依法定程序傳喚證人到場,命其具結陳述,並通知被告,使被告有與證人對質及詰問之機會,以確保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否則,如僅於審判期日向被告提示該證人未經對質詰問之審判外陳述筆錄或告以要旨,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即無從行使,無異剝奪被告該等權利,且有害於實體真實之發現,其所踐行之調查程序,即難謂適法,該審判外之陳述,不能認係合法之證據資料。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所稱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以及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係指【已經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者】而言,如法官於審判外或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被告以外之人之程序,未予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除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所列各款之情形以外,【均應傳喚該陳述人到庭使被告或其辯護人有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否則該審判外向法官所為陳述及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仍不具備適法之證據能力】。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審判外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其所謂『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係指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以證人身分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而其陳述與先前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不符時而言。如被告以外之人未於審判中以證人身分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縱具有特別可信之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仍不符上開規定,自不得依該規定採為斷罪之證據」。 ㈤查被告等及各選任辯護人,除選任辯護人陳棋銘為被告午○○主張,共同被告亦為被告本人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不符傳聞法則之例外,不具證據能力外,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他共同被告於檢察官前陳述筆錄之證據能力。至共同被告以外之其他證人(包括調查中被指為被告者)於檢察官前之陳述筆錄,及於桃園縣調查站之警詢筆錄,所有共同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證據能力,基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之例外規定,本院認均具證據能力。且因所有共同被告均經本院分離調查證據程序,以證人之調查證據方法交互詰問,並予被告本人對質詰問之機會,已確保被告之對質詰問權,是具共同被告身分之證人證言,如與警詢、偵查中所言一致部分,因被告對質詰問權已延緩至審判程序中確保,該與審判筆錄內容相同之警詢、偵訊筆錄均具證據能力;證人等審判中所言與警詢、偵查不一致部分,警詢筆錄部分(包括被告申○○於調查站所書立之自白書)依據,偵查訊問筆錄部分類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既經被告就相同問題行使對質詰問權,而先前證人陳述時所受干擾較少,其所言具可信性,其等審判外之陳述亦具證據能力。又共同被告卯○○於審判外之警詢筆錄,因未經以證人之調查證據方法詰問即已死亡,屬客觀上無法詰問,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第一款之例外規定,及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意旨,對他被告等均具證據能力。 三、被告壬○○於警詢中提出之錄音帶及其譯文 被告壬○○提出其與被告申○○於審判外之對話錄音,申○○不否認係其與壬○○之對話,而該等錄音內容係由對話之一方壬○○所錄,自無違反通訊監察保障法之情。至譯文僅係將錄音結果轉譯成文字,如其文字確與錄音帶內容相符,應與錄音內容為同一處理,且經本院勘驗後,審判外由調查員製作之譯文,與錄音內容相符,其略有不符及遺漏部分,均經本院製作勘驗筆錄在卷,自有證據能力。再譯文內容係被告壬○○、申○○間之對話,屬其等審判外之自白或對自己不利之陳述,與傳聞法則無關,又其他被告,包括被告壬○○、申○○相互間,均對此錄音暨譯文之證據能力不爭執,故具證據能力。 四、被告本人審判外之陳述 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官就自白之出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分別定有明文。此項規定就被告非自白之陳述(包括有利及不利被告本人之陳述),自亦有其適用。查除被告申○○外,其餘共同被告於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對於公訴檢察官所提出其警詢及偵查訊問筆錄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本院亦查無明顯事證檢、警機關於製作該等筆錄時,有對該等被告施以不正方法之情,是該等被告審判外之陳述係出於任意性,均具證據能力。至被告申○○所辯其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於法務部調查局桃園縣調查站所為自白筆錄及自白書(附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一六二九號偵查卷第四十六頁至第五十頁),係違法以不正方法取得云云,業經本院先行於準備程序,以合議庭組織調查,並於九十三年二月十六日裁定均具證據能力,是對被告申○○有證據能力;而所述有利及不利他被告之部分,既經所涉被告就該自白內容,於審判期日詰問證人申○○並予對質,自亦具證據能力(本院九十三年二月十六日裁定如附件)。 貳、關於證明力部分 甲、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就此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以限制向有「證據之王」稱號的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質言之,本條項乃對於自由心證原則之限制,關於自白之證明力,採取證據法定原則,使自白僅具有一半之證明力,尚須另有其他補強證據以補足自白之證明力。而所謂「補強證據」,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台覆字第一0號曾經加以闡釋:「指除該自白本身以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以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文後段,對於本條項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著有闡釋,足為刑事審判上操作「自白」與「補強證據」時之參考標準,茲節錄引述如下:「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證據能力之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為避免過分偏重自白,有害於真實發見及人權保障,並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基於上開嚴格證明法則及對自白證明力之限制規定,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自亦須具備證據能力,經合法調查,且就其證明力之程度,非謂自白為主要證據,其證明力當然較為強大,其他必要之證據為次要或補充性之證據,證明力當然較為薄弱,而應依其他必要證據之質量,與自白相互印證,綜合判斷,足以確信自白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始足當之」。尤須強調者,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一日修正生效之本條項,於原條文之「被告」之外,特增訂「或共犯」之規定,其目的不僅在限制被告自白之證明力,亦限制「共犯」自白之證明力,蓋所謂「共犯之自白」往往涉及「正犯」即他被告犯罪事實之陳述,為恐「共犯」因基於同為被告之身分,無庸具結而不受偽證罪之處罰,因而容有隨意攀誣他人之虞,致妨害司法公正,立法者特於此增訂有與被告本人自白相同之證明力限制。 二、次按共同被告不利於他被告之陳述,即應先分離審判程序,將該共同被告列為證人之地位,具結並詰問,以保障他被告之訴訟權,業如前述。惟須注意者,分離審判程序,將共同被告列為證人詰問之程序,僅係取得「證據能力」之作法,惟就「證明力」之限制層次言,即令程序上以分離審判程序,將共同被告準用證人身分結證訊問,惟如係共犯之共同被告,其自白中對於他被告不利之陳述,仍應受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之限制,換言之,【共犯之共同被告】所為自白,且有不利於他被告本人之陳述者,即令以證人證言之法定證據方法形諸於審判庭調查證據,仍不得以此「單一證言」為認定他被告犯罪之證據,始符前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限制被告及共犯自白證明力之意旨。換言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之規定,仍應受到同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之特別規定的限制,除該共同被告之「自白」(即不利於他被告之證言)外,尚應有足為補強證據之其他證據,始得論罪科刑,方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及刑事訴訟法於此特設之證據法則。正如大法官許玉秀於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所言:「同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所增訂之共犯自白規定,即應解釋為有共犯嫌疑之共同被告,就其與被告有關之供述證據,即便已經具結及詰問程序予以調查,仍應於該供述證據之外,另行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不得以其供述證據,當作證明被告犯罪之其他必要證據;否則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新增之規定,即可能導致同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形同具文,嚴格證明法則亦將遭到破壞,而違背憲法第八條及第十六條以法定程序保障被告訴訟權之本旨。至於不具共同被告身分之共犯,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本為被告以外之人,其自白當然必須依人證之調查方法予以調查,乃自明之理」。查本案被告等,實體法上係經檢察官指為共犯之嫌疑被告,程序法上亦經檢察官共同起訴而列為共同被告,其等屬共犯之共同被告地位,尚無疑問,對於其等自白及其中不利於他被告之陳述部分,其證據能力及調查證據之方法,應遵循本院前述所論述之證據法則,始謂合法適當。 三、再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又間接事實之本身雖非證據,然因其具有判斷直接事實存在之作用,故經由間接事實所形成之間接證據,即具有證據能力,但如何由間接事實推論直接事實之存在,仍應為必要之說明,始足斷定其所為推論是否合理。須強調者,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同此意旨,此方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及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所揭示的嚴格證明程序。另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被告,通常即是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或甚至是制度所產生之弊病為人為所利用,亦即此類犯罪者多為所謂「智慧型犯罪」,是其本質上即常有欠缺直接證據之情形,則運用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以為合理推論之場合即增加且重要。 四、訊據被告等均矢口否認犯行,被告申○○辯稱(略以):於調查站所書寫的自白書內容非真正,成立超捷公司係為工業區解決垃圾風暴的難題,以低於市價清運,虧本都來不及,有何圖利可言云云。午○○辯稱(略以):所有公文均非其批示,而係申○○負責,且雖有向申○○借錢,惟未投資超捷公司云云。被告寅○○辯稱(略以):未投資超捷公司,且未負責一般廢棄物及污泥清運之業務云云。惟查: ㈠申○○以其妻巳○○之胞姊劉香妹為名義上負責人,成立超捷公司,該公司由申○○、午○○及寅○○三人合夥,分別出資九十萬元、二十萬元及十萬元之事實,業據被告申○○於調查站警詢時,基於自由意志所書立之自白書一件在卷(參見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一六二九號偵查卷,第四十九頁)。申○○並於該件自白書分別就如何向頂新公司借牌,頂新公司抽取發票面額百分之十至二十作為利潤,以及超捷公司有關污泥清運由申○○本人主導,並詳述被告等人分紅及交付情形稱:「卯○○配合,主任明白莫(按「默」字之誤)許,卯○○雖配合,他沒拿好處,經常私下三、二萬借用未還,合計約有數十萬元,(主任)午○○除每年分紅二十萬元外,每筆工程約有分紅十至三十萬元不等。楊組長每年底分紅十萬元,分紅給每各(按「個」字之誤)款項,均由彰化銀行埔心分行提領現金交付」等語。自白書內另坦承有蓄環保公司意係營運污泥、垃圾清運,並借佑欣公司執照清運廠商一般廢棄物,以及估價單由申○○本人交卯○○,並由申○○本人製作,依當時行情估價填寫等語。 ㈡上述自白書書立時間為八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被告申○○於當日在調查站之警詢筆錄前半段尚全盤否認本件犯行,辯稱與頂新公司無關,惟經調查站承辦之司法警察,即當日製作筆錄之乙○○、未○○提示頂新公司負責人丑○○之子林享河指證被告申○○於八十二年十月間,即向頂新公司借牌承包大園工業區污泥清運工程等語,並經提示由申○○親筆開立之頂新公司名義之發票後,申○○因而書立上述自白書,自此以後之警詢筆錄即坦承開立頂新、有蓄環保公司之發票,以及超捷公司之估價單、簽收單等憑證,並稱「希望能給我從輕量刑之機會」等語(參見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一六二九號偵查卷,第四十七至四十八頁)。且查申○○於自白後之翌日即八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復經提訊於調查站製作警詢筆錄一件,再次坦承其向頂新公司負責人丑○○借牌,並提供估價單,經由頂新公司取得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一般廢棄物清運權利,偵查中更補充稱(略以):「八十二年間由我與與丑○○一起買垃圾車,一人買一部車,是到黃家訂約的,只有過年時給鄭(國武)二十萬元、楊(振村)十萬元,給了約五、六次」等語(參見同上偵查卷第六十五頁、六十六頁背面),核與證人丑○○於本院審判中結證所稱(略以):「任職頂新公司總經理,與申○○於七十九年間即為鄰居而認識,八十二年間申○○向我借牌,目的是要有清除許可證,承包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廢棄物清運業務,其中百分之五的稅金是申○○付的,沒有任何借牌費,我沒有投資超捷公司,借牌直到頂新公司八十四年間被環保局吊銷廢棄物清除證照為止,是因為頂新公司沒有最終焚化爐、廢棄物清理場,所以被吊銷,與借牌無關」等語(參見本院審判卷㈢第四十頁以下),以及證人林馨儀之子,同樣經營頂新公司之林享河於警詢中所指證(略以):「申○○自八十二年十一月起,向我借頂新公司的牌照,至八十四年一月,因他後來成立超捷公司,就以超捷公司名義清運,是申○○要我開據發票給他,以向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報銷、我只借牌給他申○○,未參予清運,申○○是由其叔叔黎鎮湧負責清運,黎在他老家楊梅鎮高榮里北高山頂五之一號,設有一處未經環保機關核准的垃圾轉運站,供他囤積廢棄物,申○○僅支付百分之五發票稅金給我」等語(參見八十九年偵字第一六六三二卷第四十、四十一頁),經互核相符,並核與申○○警詢、偵查中之自白,除支付稅金之比例,丑○○、林享河不承認有超過百分之五,以及有無一起出資購買垃圾車等情,丑○○、林享河均未提及外,餘均與申○○之自白相符」。並有扣案大園工業區於八十二年十一月至八十三年全年間之支出憑證,其上附具頂新公司名義之發票,而申○○坦承發票上數量、單價及金額均為其所書寫(部分經影印附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六六三二偵查卷第九十二頁以下),以及八十四年二月間至八十五年七、八月間,由超捷公司出具發票與大園工業區甚且自八十四年二月間超捷公司取得清運廢棄物許可證,至八十五年七、八間,許可證遭吊銷之期間,改由超捷公司名義出具發票供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以支出憑證核銷,惟於八十四年三月至五月所附「一般垃圾轉運民營公司清運統計表」,其上由司機郭世識所簽署之清潔公司,竟仍簽署「頂新公司」(參見八十九年度他字第一二三六號偵查卷第三十六至三十八頁、四十至四十二頁、四十四至四十五頁),此申○○於警詢中亦坦承稱(略以):「因為八十二年間向頂新公司借牌,到八十四年間超捷公司取得許可證,但是未告知司機,所以才發生司機仍簽頂新公司清運」等語「參見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一六二九卷第五七頁背面至五八頁)。已足證申○○成立超捷公司之初,因為未取得清運廢棄物許可證,遂情商與其有多年情誼之鄰居,頂新公司總經理丑○○,出借該公司許可證,實際上係由申○○擔任實際負責人之超捷公司,所自行購買之垃圾車實施清運工程,又為免此種謀利自己之事爆發,因而固定「分紅」午○○、寅○○,及以借款名義給予卯○○小利,堪認申○○於警詢、偵查中之自白屬實,其於審判中翻異前詞,辯稱係出於想獲取交保機會而為不實之自白云云,顯不足採信。 ㈢復查申○○之自白書分別就頂新公司、超捷公司、有蓄環保公司及佑欣公司之情形,陳述其與共同被告參與或與各公司合作之情形不一,其中就超捷公司之成立及經營模式敘述最詳,不僅詳述其與被告午○○、寅○○合夥出資之比例,且就日後如何分紅,以及卯○○雖無出資,惟以借款名義向之借款使用等情,均敘述詳實。如非確有實情,甚難想像其得憑空杜撰,且申○○於書立自白書後之警詢及其後偵訊中,不僅未推翻其詞,甚且就卯○○三番兩次向其借款,以及午○○、寅○○投資入股之時間及細節更陳述稱(略以):「寅○○在超捷公司成立之初,即入資十萬元買垃圾車」、「購買垃圾車的錢,尚有午○○的二十萬,我則出資九十餘萬,統一由我以頂新公司支票購車,垃圾車則登記在超捷公司名下」等語(參見八十九年度偵字義一一六二九號卷第五十八頁背面)。而詳核超捷公司於彰化銀行埔心分行帳戶之存提明細,確實有多筆提領現金之紀錄,而午○○所開設於大園郵局之薪資帳戶內,除每月初固定匯入之五萬餘元薪資外,其於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存入現金六十萬元,八十三間於二月八日、二月二十八日、五月五日、五月十七日、七月十三日、八月十六日、九月六日、九月二十三日、十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一日,分別存入二十萬、十八萬、十六萬、十五萬、十五萬、十二萬、十萬、十三萬、十萬、十五萬,共計一百三十四萬元之現金,八十四年間於一月九日、四月七日、六月十日、八月二十四日、十一月九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分別存入十五萬元、十六萬元、二十萬元、十五萬元、四十二萬元、十萬元,共計一百十八萬元,八十五年間於二月十三日、五月十三日、八月二十日、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日,分別存入六萬元、十萬元、六萬元、五萬元、十五萬元之現金,共計四十二萬元,有該帳戶存提明細表在卷可證。其於八十二年至八十四年間,幾乎每月均有現金存入,八十五年間則每隔四月有現金存入,而八十二年至八十五年之每年年底有較為大額之現金,如六十萬元、四十二萬元存入,此段期間正係超捷公司成立,並承攬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一般事業廢棄物或污泥清運工程之期間,而超捷公司於八十五年七、八月間遭撤銷許可證後,午○○於八十六年間之上述帳戶即無固定之現金存入,此與申○○所自白「午○○除每年分紅二十萬元外,每筆工程約有分紅十至三十萬元不等」之數額,大致相符。午○○對此等固定而來源不明之現金,就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六十萬元部分,辯稱係其為父母親作八十大壽時收入之禮金,八十四年六月十日存入之二十萬元,則係母親過世之奠儀,其餘部分係賭博所贏金錢,部分係向申○○借貸之金錢云云。惟查即使扣除被告午○○所辯之六十萬元、二十萬元兩筆現金收入,仍有多達數十筆之現金收入,至賭博所得現金,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而自其帳戶內餘額,始終留有七、八十萬元,甚至一百餘萬元不等之情形觀之,午○○並無須向申○○借貸十萬元至二十萬元小額不等金額之必要理由,所謂「借貸」云云,無非即係申○○給付之分紅,更屬合理。因而午○○所辯顯不足採信。而卯○○於調查站警詢中亦坦承向申○○借款之情,與申○○自白書所稱「卯○○經常私下三、二萬借用未還,合計約有數十萬元」等語亦符。已足認申○○自白有補強證據,經互核足認該自白之真實性,就共同被告午○○、寅○○及卯○○而言,申○○警詢中不利於其等之上述合夥、分紅等陳述,與審判中否認之詞相較,顯具特別可性之情,具證據能力,又因足認其真實性,而有可信之證明力。 ㈣就清運污泥之部分,申○○、午○○雖辯稱,是八十四年二月間,環瑞公司表示每噸一千元無法繼續清運,片面毀約,致管理中心不及招標,始直接以比價方式,委請超捷公司清運污泥云云。經查環瑞公司與大園工業區,分別於八十二年十月一日、八十三年十月一日,締結兩紙「委託事業廢棄物清理服務同意書」,由環瑞公司負責清運大園工業區之污泥,期間分別為八十二年十月一日至八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八十三年十月一日至八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固有查扣之兩紙契約在卷可證,惟經本院數度傳喚當時代表環瑞公司簽約之承辦人「甲○○」均未能合法送達,甚且契約上所載環瑞公司住址「台北市○○路一0一號五樓之一」,亦查無此址,加上該兩紙契約後,竟未附環瑞公司之得標資料,以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登記事項卡等足資辨識之文件資料,此兩件契約有略嫌草率之情。又經本院依職權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查詢結果,不僅台北或桃園地區,並且於全國,均查無「環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登記,而僅有「環瑞實業【有限】公司」,其負責人為戌○○,經本院傳喚證人戌○○,及戌○○之夫天○○到庭,均證明「環瑞實業有限公司」並非契約書上所指「環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其等從未與大園工業區簽署契約,亦未僱用「甲○○」其人。此已令本院啟疑並無該公司,亦無「甲○○」其人之存在,惟被告午○○、申○○均堅稱有該公司之存在,本院另依職權就該兩件契約書所載「廢棄物處理場(廠)操作許可證」、「清除許可證」字號,分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桃園縣環保局查詢結果,經回函確有「環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負責人為亥○○)及各該操作許可證、清除許可證等文件,是除非有事實足信桃園縣環保局內有人與被告等共謀圖不法利益,而偽造該公司名稱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及許可證等情,否則仍應認有「環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存在,至簽約之「甲○○」,經本院提示十數位名為「甲○○」之人供被告申○○、午○○辨識,二人均無從指出其人,自有無從傳喚到庭之難處,合先敘明。至被告申○○、午○○均辯稱係環瑞公司表示清運費用不敷成本,而片面解約,於八十四年三月間不願再履約清運污泥,始臨時委請超捷公司清運,未依相關規定另行辦理招標,而係以三家公司比價之方式,由最低價之超捷公司得標清運云云。惟查: 1殊不論被告等所稱「環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存在,有上述之疑義,即令如被告等所稱,有此公司之存在,而該公司於履約期限內片面解約,勢必造成每日均需清運污泥之大園工業區莫大損失,惟身為管理中心正、副主任之午○○、申○○(申○○並兼污水處理廠廠長),竟未循行政通報程序向上級報告,或依職權與環瑞公司進行調解,甚或修訂契約此等補救方式,否則亦應逕行對環瑞公司採取法律途逕之損害賠償請求,或沒入履約保證金等保護措施,而任令環瑞公司「全身而退」?其中有無圖利環瑞公司,著實令人啟疑。 2超捷公司係於八十四年二月七日取得台灣省環保處核發之第一類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八四廢清字第0四二九號),而得清運污泥事業廢棄物,業據申○○自承在卷,超捷公司因而於八十四年二月間起,即取消與頂新公司之借牌關係,而以超捷公司名義開始請領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運費用,業如前述。而被告申○○、午○○所辯稱環瑞公司片面毀約之時間竟適巧即為八十四年三月,即超捷公司開始領得清運許可證之翌月? 3縱令如被告等所辯,係環瑞公司於八十四年三月間片面解約,惟至九月三十日止之契約屆滿期間,究有無向上級機關報准以詢價方式辦理招標程序,午○○與申○○之陳述顯有不符。午○○於警詢中供稱,環瑞公司係因清運執照到期,其曾口頭報備經濟部經工管會核准,因而於未正式招標前暫時委請超捷公司清運污泥等語(參見八十九年度他字第一二三六號偵查卷第二六0頁背面);申○○則於警詢中供稱,大園管理中心將準備辦理污泥清除招標之底價送至工業局工業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因遲未核備下來,所以在八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期滿前未辦理公開招標等語(參見同上卷第一三三頁背面)。殊不論被告等均無法提出其等確有呈報上級機關之證據,且即令係因上級機關未及回覆核備,超捷公司暫先接替環瑞公司,其期限亦應至八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惟超捷公司卻自八十四年三月至八十五年二月止承攬污泥清運工程,其期間恰為一年。而經查扣之公文中顯示,僅有寅○○遲至八十四年九月間始上簽呈請求辦理招標,就此申○○於書立自白書後之翌日警詢筆錄中曾指證稱(略以):「因為寅○○在超捷成立之初,即入資購買垃圾車,所以他當然不願即早辦理招標」等語(參見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一六二九號偵查卷第五十九頁正面)。顯已透露出午○○、寅○○及申○○刻意護航其等合夥之超捷公司順利承運污泥清運工程之動機。 4再查卯○○於警詢中供稱(略以):「八十四年二月間申○○告訴我,環瑞公司表示污泥清運費調漲,該公司不敷成本要提前解約,解約後申○○拿給我三家估價單,我即簽辦由最低價之超捷公司清運,至八十五年三月一日經公開招標,由大益公司得標為止」、「八十四年環保組(按即寅○○組長)以零星工程名義,申請污水廠污泥清運工程並經主任核可後,我準備辦理議價,申○○拿了超捷、大益及天良三家公司估價單給我,表示可委託超捷清運,於是我簽呈表示由超捷承包,之後的零星污泥清運工程,亦都是由申○○提供三家估價單,每次都會有超捷的估價單在其中,且超捷之估價單最低而由超捷承包」等語(參見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六六三二號偵查卷一0二至一0三頁)。此與申○○於警詢中自白所述(略以):「我與大益環保公司、佑欣環工等廠商間彼此都有交換持有領據、估價專用單,以利估價作業,估價單均係我填寫後加蓋估價專用章後,交卯○○辦理」等語(參見同上偵查卷第五十七頁背面)相符。卯○○並於警詢中稱(略以):「我辦理比價時,污水廠寅○○或洪永松曾推薦超捷公司參加比價,因此我再找來大益、天良二家公司,連同超捷比價結果均由超捷得標」等語(參見八十九年度他字第一二三六號偵查卷第一五五頁正面)。足見比價之其他廠商估價單均係申○○提供,而申○○、寅○○均曾指示由超捷公司比價後以最低價得標之情。 5又查被告寅○○為圖利自己投資之超捷公司,刻意於八十四年九月三十日環瑞公司契約期滿後始上簽請求辦理招標,因而由申○○、午○○再以不及招標為由,以零星清運方式,規避「稽察條例」及「注意事項」規定,先由申○○製作繕打「廢棄物清運處理合約書」,並於同年十月二日由午○○完成與超捷環工公司訂約用印手續後,始由申○○提供偽造之大益公司、天良公司廠商估價單,供卯○○據以於八十四年十月三日始補辦簽報以詢價方式辦理之內簽,有查扣之契約書及簽呈在偵查卷及本院審判卷證物專卷二足查。自上述詢價核准程序之日期,竟晚於簽約日期之情觀之,足證所謂三家估價單比價程序,完全流於形式,且均係偽造之情。更遑論超捷公司清運污泥之價格為每噸二千元,明顯高於環瑞公司清運每噸一千元之單價有一倍之多,顯有圖利超捷公司之情。 ㈤更查經本院勘驗由張憙炎所提供,其與申○○於審判外黎對話之錄音帶內容之譯文可知(當時申○○尚未經羈押),申○○明白陳述污泥業務部分為申○○負責之頁務,卯○○有參與,而與張憙炎無關,且「癸○○是沒有事他根本不知道」(參見本院審判卷第四十七頁以下)。經核申○○上述自白書中亦未陳述癸○○、張憙炎參與合夥之情,足認其自白書並非無端虛構,而確有其事。是被告申○○所辯係出於想獲取交保機會而為不實之自白云云,無寧應認係申○○為求具保,終願自白犯行並向調查機關坦稱其他涉案共犯者,且已有打算於審判中再來翻供,始較符申○○當時之心態。末查申○○雖一再辯稱超捷公司除承攬大園工業區工程外,尚有承攬其他機關或地區之工程,惟自始至終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且即令如此,仍無解於其等圖利自己及超捷公司私法人之罪責,其等係專為承攬大園工業區內業務之目的,而成立超捷公司,應堪認定。 ㈥末按大園工業區內,不論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之污泥清運業務,即令非正、副主任主管之業務,亦為其等監督之業務,尤其申○○尚兼任所屬污水處理場廠長一職,對於污泥清運更難謂非其主管或監督之業務,寅○○任環保組長,上述清運業務自同為其主管或監督之業務。午○○、申○○及寅○○三人合夥成立超捷公司,並推由申○○為實際負責人,承攬大園工業區內工程,明顯未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並且以如上非法之方法,其圖利自己及超捷公司私法人,並且獲有如前工程款之利益,已堪認定。 ㈦此外,犯罪事實一之㈠部分,頂新公司自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處,分別取得以下時間開具之支票:八十二年六月七日(支票號碼【下同】:AJ0000000) 、六月十八日(AJ0000000) 、六月二十九日(AJ0000000)、八月十三日(AJ0000000)、九月十五日(AJ0000000 、AJ0000000) 、十月七日(AJ0000000)、十月十八日(AJ0000000)、十一月十六日(AJ823217)、八十三年一月十二日(AJ00 00000)、二月二十一日(AL0000000)、三月七日(AL0000000)、四月十一日(AL0000000) 、五月十三日(AL0000000) 、六月八日(AL138054)、七月十三日(AL0000000) 、八月十一日(AL0000000) 、九月十三日(AL716061)、十月十四日(BB0000000)、十一月二十八日(BB0000000)、十二月十九日(BB658973)、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BB0000000) 等。總計不法利益二百三十六萬三千四百五十五元。犯罪事實一之㈡部分,超捷公司自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處取得以下時間開具之支票:八十四年二月十六日(BB0000000) 、二月二十五日(BB0000000) 、四月十九日(BB0000000) 、五月十日(BB469339)、六月七日(BB0000000) 、八月十四日(BB0000000) 、九月十三日(BB0000000) 、十月九日(BB0000000) 、十一月十四日(BB0000000) 等。總計不法利益六十一萬元。犯罪事實一之㈢部分,有蓄環保公司自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處取得以下時間開具之支票:八十五年六月二十日(BB0000000) 、九月九日(BB0000000) 、十月十一日(BB0000000) 、十一月七日(BB0000000) 、十二月六日(BB0000000) 。總計不法利益四十九萬九千二百元。犯罪事實一之㈣部分,超捷公司自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處取得以下時間開具之支票:八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支票號碼:BB0000000) 、四月十九日(BB0000000) 、五月十五日(BB0000000) 、六月七日(BB0000000) 、六月二十日(BB0000000) 、十月七日(BB659719)等;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BB0000000) 、十二月七日(BB0000000) 、十二月二十六日(BB0000000)、八十五年一月二十日(BB0000000)、二月二十三日(BB0000000) 。總計不法利益九百零七萬六千六百七十五元。犯罪所得總計為:一千二百五十四萬九千三百三十元。固然超捷公司承攬上述工程,勢需支出成本,如人事、購車等,其借用頂新公司牌照尚需支付稅金,惟扣除成本以計算實際獲利,至少於本件事實上根本不可能,而且此涉及扣除之基準與範圍而異,且被告等如非違背法令,超捷公司、有蓄環保公司根本無從承攬到上述工程,自應將所得工程利益全數計入犯罪所得財物。 五、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應將行為時之法律,與行為後之法律,包括中間時法,比較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觀九十五年七月一日生效之現行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自明。按被告申○○、午○○及寅○○三人於行為後,原八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生效之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關於構成要件「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利者」之規定,曾有兩次修正,分別於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修正為「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私人不法之利益者」;九十年十一月七日即現行法修正為「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並刪除未遂犯亦處罰之規定。經比較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自原不限圖利國庫、私人之要件,修正為限於圖利私人,惟仍保留行為犯即已足之規定,經再修正為現行僅限於圖利私人,且需獲得利益之結果犯始處罰之規定。亦即被告等行為後,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圖利罪之犯罪構成要件,已因修正而予縮減,自原來處罰「行為犯」即已足,不須因而獲得利益,修正為須因而獲得利益之「結果犯」,應以修正後即現行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之構成要件較有利於被告等。惟就法律效果即法定刑部分,被告等行為時之該條法定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中間時法及現行法均同),經比較結果,顯以行為時之本條項款規定之法定刑較有利於被告等,而應以八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修正生效之本條法定刑為適用依據,換言之,構成要件以裁判時即現行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有利於被告等,法律效果之法定刑以行為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有利於被告等,基於最有利於被告原則之觀點,此處應割裂適用現行法(構成要件)及行為時法(法定刑)之結果。至本條例第二條將行為時之「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修正為現行之「公務員」(配合刑法第十條第二項公務員定義之修正),雖有所限縮,惟就被告等本件犯行而言,不論行為前後之規定,均不影響其等應適用本條例處斷之法律效果,而無行為後法律較有利於被告之情,依據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第一條所宣示之「適用行為時法原則」、「罪刑法定原則」,應適用行為時法即八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生效之本條例第二條論處。又按被告申○○於偵查中自白犯行,且因而查獲其他共犯,其行為時之本條例第八條後段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得減輕其刑」,分別於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兩度修正為本條立第八條第二項,中間時法及現行法之規定,雖均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之限制要件,惟其法律效果為「減輕或免除其刑」,而應以行為後即現行法第八條第二項為較有利於被告申○○,應依該條項減輕其刑。另被告等尚犯刑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六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之公文書罪,登載不實事項之罪,為行使之罪所吸收而不另論罪。另按被告等行為後,刑法總則諸多條文業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施行。與被告等有關之刑法總則條文有以下之修正,應探討有無新、舊法比較之必要: ㈠刑法第三十三第五款有關罰金之最低數額部分,因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原為銀元,修正前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規定:「罰金:(銀元)一元以上」,而銀元與新臺幣間之折算,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規定,以銀元一元折算新臺幣三元;修正後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則規定:「罰金: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經比較新舊法之規定,修正後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所定罰金之最低數額,較之修正前提高,自以修正前刑法第三十三第五款之規定有利於被告。 ㈡刑法第二十八條共同正犯之規定,由原條文之「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修正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涉及共同正犯構成要件之變更,且立法理由明文表示仍不排除所謂「共謀共同正犯」。修正前後之規定,輕重相等,修正後之規定並非較有利於被告,依據刑法第一條前段所定「罪刑法定主義」,以及同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所定「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仍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查被告申○○、午○○及寅○○就本件貪污圖利私人獲得利益犯行、行使登載不實事項公文書犯行部分,有相互將對方行為視為自己行為支配之意,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修正後刑法業已刪除第五十六條連續犯之規定。此刪除雖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變更,但顯已影響行為人刑罰之法律效果,自屬法律有變更,比較新舊法結果,應適用較有利於被告之行為時法律即舊法關於連續犯之規定,以一罪論,並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查被告等多次共同貪污圖利私人獲得利益罪、行使登載不實事項公文書罪,其犯罪時間接近,所犯分別係構成要件相同之罪,顯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為連續犯,均應依修正前刑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均以一罪論,並均加重其刑。 ㈣刑法第五十五條關於牽連犯之規定業經刪除,此刪除雖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變更,但顯已影響行為人刑罰之法律效果,自屬法律有變更,比較新舊法結果,數行為依新法規定原則上應予併罰,惟依修正前刑法第五十五條牽連犯規定,得從一重處斷,是以仍應適用較有利於被告等之修正前刑法第五十五條關於牽連犯之規定。查被告等連續貪污圖利私人獲得利益罪、連續行使登載不實事項公文書間,有方法、結果,及手段、目的之牽連關係,應依修正前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分別從一重之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之罪處斷。六、爰審酌被告等身居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要職,竟不知安分守己,貪圖鉅額不法利益之享樂之犯罪動機,於分層負責之公務員體系中勢生不良,甚至仿傚之不當影響,且其等所為嚴重侵害公務員應保持品位、清廉自持之形象,侵害公權力威信甚為深遠,又本件圖得不法利益高達千萬餘元,申○○居於主導地位,寅○○配合並積極參與,以及午○○為其等主管,不為妥適監督已有不當,甚且消極配合違法行為而同流合汙,申○○雖曾於偵查中自白部分犯行,惟審判中與鄭國午、寅○○等人均否認犯行,造成司法調查程序上之勞費之犯後態度,以及本件涉訟時間長遠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關於褫奪公權從刑之規定,行為時及行為後之規定輕重相等,基於主刑、從刑一併適用原則,本件論罪主刑係依行為後本條例規定,自一併適用行為後即現行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褫奪公權之從刑。另被告等犯本罪所得財物利益,對於共犯之獲利應一併計入所得財物範圍,總計為一千二百五十四萬九千三百三十元之不法利益,經比較行為時本條例第九條及行為後本條例第十條規定,就本件而言之輕重相等,依上述相同原則,亦依行為後即現行貪污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應予追繳,如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分別以其等財產抵償之,又被告三人共犯本罪所得,分如主文所述,是就其等財產抵償部分,如其中一被告之財產經抵償後,其餘被告即應免除其抵償之責,以免重覆執行,附此敘明。 乙、辛○○、己○○、巳○○、癸○○、壬○○、丙○○、辰○○、酉○○無罪,及申○○、午○○、寅○○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癸○○為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業務組組長,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巳○○係申○○之妻,擔任超捷公司之董事,及有蓄公司之負責人,就上述經本院認定有罪之犯罪事實,癸○○、巳○○,與申○○、午○○及寅○○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緣辛○○為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出納,亦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壬○○係超捷公司「環工部」負責人,李文昌係大益環保有限公司(下簡稱大益公司)負責人,辰○○係大園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顧問,丁○○、己○○分別為「旭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貫公司)之董事長、董事,酉○○係大堀種苗園之負責人。其等分別或共同與申○○、午○○、寅○○、癸○○、巳○○有為以下犯行: ㈠於八十二年四月間,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所屬污水處理廠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申請污水排放許可,承辦人王秀娟於同(八十二)年四月十五日簽報,依規定將污水處理廠之排放口水質檢測業務,外包給「具合格營業項目之環工公司」;詎午○○、申○○、寅○○、癸○○、卯○○復基於圖利之概括犯意,明知超捷環工公司未取得環境保護署審查合格之廢(污)水檢驗測定資格,竟違反「水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將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所屬污水處理廠之水質檢驗工程,共謀由卯○○虛偽填載超捷環工公司、佑欣環工股份有限公司(誤書為佑「新」,為黎某向佑欣公司負責人呂國祚借牌之公司)、佳宏環保公司之不實詢價記錄,簽報「以詢價方式辦理,由最低價超捷環工檢驗」,經寅○○、癸○○、申○○、午○○批核,並由壬○○連續提供虛偽不實之廠商估價單及水質檢測資料,向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請領水質檢測費,致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連續於八十二年六月七日(AJ0000000)、八月九日(AJ000 0000)、九月七 日(AJ0000000) 、十月七日(AJ0000000)、十月二十六 日(AJ0000000) 、十二月十三日(AJ0000000)、八十三 年一月十四日(AJ000000 0)、六月一日(AL0000000)、 八十四年十二月七日(BB0000000) 、十二月二十七日(BB0000000) 等日,支付超捷公司公司水質檢驗費用,共獲取二百五十七萬七千九百零七元之利益,足生損害公務文書管理之正確性及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 ㈡午○○、申○○、辰○○等三人於八十四年十二月七日,分別獲聘大園工業區廠商協進會之「創會總召集人」、「常務監事」及「顧問」,大園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址設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二樓,因業務往來,辰○○獲悉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辦理污泥清運工程招標,遂與領有省環保處核發八四廢清字第○二○五之三號第一類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大益公司負責人李文昌謀議合作,由辰○○負責將管理中心所屬污水廠污泥清運至大益公司設在蘆竹鄉○○路之廢棄物轉運站,再由李文昌負責污泥之後處理清運,辰○○並與游溪琳合資四十餘萬元,購買乙輛二十一噸中古貨車(車號:MU-440,登記在桃富運輸公司名下),由游溪琳任司機清運,所得利潤均分。其後辰○○遂積極向午○○、申○○、寅○○、癸○○、卯○○等人推薦大益公司,午○○、申○○二人基於圖利他人之概括犯意,明知桃園縣境有多家(二家以上)具第一類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資格之廠商,卻指示卯○○在八十五年一月十九日函發台灣省建設廳工業區管理委員會(下稱:工管會)有關污泥清運招標案內容,虛偽簽報不實之「委託第一類乙級以上廢棄物清除業者代為清除,經查桃縣境內僅有二家公司符合其資格」;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並於八十五年二月二日發函通知大益公司、翼贊企業有限公司,同年二月七日辦理議價,李文昌減價至單價二○五○元,仍高出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核定底價,當日流標;詎申○○即指示寅○○、癸○○、卯○○將污泥清運工程先行交大益公司清運,卯○○遂通知辰○○、李文昌,大益公司即於隔(八)日開始清運污泥。唯因未完成法定招標簽約程序,同年二月二十七日,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與大益公司再次舉行議價,鑑於工管會核定該污泥清運招標案總量四○○○噸,預算底價為六佰三十萬元,午○○即於議價會議公開預算底價六佰三十萬元,經李文昌核算成本,僅願意清運三二○○噸,後由卯○○塗改大益環保之估價單,將原繕打之四○○○噸,修改為三二○○噸,並完成議價紀錄,報工管會核備;同年三月一日,雙方簽訂六佰三十萬元清運合約,足生損害於公務文書管理之正確性及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又午○○、申○○、寅○○、癸○○、卯○○等人於審核廠商資格文件過程,明知大益公司所附臺灣省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有關廢棄物處理委託運泰公司每日三十噸處理量,至八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到期,亦即自同年四月一日起,大益公司每日僅餘委託昌冠公司之每日三噸處理廢棄物量,卻仍在四月一日之後,連續未經公開招標程序,以議價及緊急清運名義,直接委託大益公司每日清運二至四十噸污泥量,迄同年七月底始因大益公司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遭撤銷許可證而終止。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分別於八十五年三月八日(BB0000000) 、四月八日(BB661039) 、四月三十日(BB0000000)、五月二十二日(BB0000000) 、六月八日(BB466135)、六月二十二日(BB0000000)、七月四日(BB000 0000) 、八月七日(BB0000000) 等日,支付大益公司清運一般事業廢棄物(污泥),總計一仟五佰萬零八仟六佰三十六元正,足生損害公務文書管理之正確性及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㈢午○○、申○○、寅○○、癸○○、卯○○等人明知旭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貫公司)、旭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竹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寬昇股份有限公司、益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互為旭貫公司負責人丁○○、董事己○○之持股公司,自八十二年九月起,在辦理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污水處理藥劑採購案過程,為規避「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例」、「工業區管理機構營繕工程暨購置定製變賣財物內部審核注意事項」之規定,由寅○○以每次採購不超過五十萬元簽報,再由卯○○以詢價程序辦理,復由丁○○、己○○提供前開持股公司估價單共同圍標,經申○○、午○○批核,連續向旭貫公司採購污水處理藥劑。八十三年二、三月間,己○○以公司營運週轉困難為由,分別向午○○、申○○、寅○○及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出納辛○○借款二佰萬、二佰萬、一佰萬、一仟八佰萬元,而同(八十三)年六月間,午○○、申○○、寅○○獲知旭貫公司面臨倒閉,在午○○、申○○授意下,寅○○乃以緊急採購化學藥劑PAC、硫酸鋁、液咸之名義,當月由卯○○連續分批向旭貫公司詢價,計採購污水處理藥劑達三百零五萬一千三百元,其中六月七日、六月十一日、六月十五日、六月十七日、六月二十二日、六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七日之採購金額均超過「工業區管理機構營繕工程暨購置定製變賣財物內部審核注意事項」規定之五十萬元限額,理應辦理公開招標,午○○等基於圖利之概括犯意,直接以詢價辦理;旭貫公司當月因債務宣布倒閉後,又依八十三年六月份之「污水廠化學藥劑使用總表」,當月並無硫酸鋁七二○噸及液咸二六○噸之進貨紀錄。而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仍於六月二十七日開據支付旭貫公司支票(號碼AL0000000) 三百零五萬一千三百元正,由辛○○直接將支票款經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電匯三百萬元予土地銀行古亭分行之黃秀華帳戶,扣除匯款匯費四十五元,餘額五萬一千二百五十五元逕行匯入辛○○設於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個人帳戶(帳號:000-00-00000 -0) ,當日再由黃秀華提現交辛○○匯總款額,分配交付午○○、申○○、寅○○等人。前開採購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分別於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AJ00 00000)、十一月二十五日(AJ583227)、十二月二日(AJ0000000) 、八十三年一月五日(AJ0000000) 、一月二十七日(AL0000000) 、三月三日(AL0000000) 、三月三十日(AL0000000) 、四月二十二日(AL117197)、四月三十日(AL0000000) 、五月十七日(AL0000000) 、五月三十日(AL713038)、六月二十四日(AL0000000) 、六月二十七日(AL0000000) 等日,支付旭貫公司污水處理藥劑費用,計二千八百三十三萬五千二百元正,並獲取其利益,而足生損害公務文書管理之正確性及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㈣卯○○在辦理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污水處理廠之綠化工程案,先與酉○○取得意思上聯絡,並在招標程序違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營繕工程招標注意事項」之規定,於領表截止日八十二年六月四日始刊登招標公告;酉○○乃於八十二年六月八日向觀音鄉農會購得合作金庫中壢支庫支票(支票號碼:KT0000000 、KT0000000 、KT0000000) 三張,充作中國造園社、大堀種苗園、資群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資群公司)押標金,並偽造不實之中國造園社、資群標單紀錄參與投標。午○○、申○○、寅○○、癸○○、卯○○等人明知酉○○之作為,復基於間接圖利之概括犯意,明知中國造園社及資群公司未參與投標,仍虛偽記載於投標記錄等文件資料,於八十二年六月九日由酉○○以二百萬七千一百五十三元標價取得污水處理廠之綠化工程案,並獲取其利益,而足生損害公務文書管理之正確性及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及同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意旨曾強調此一原則,足資參照。又按最高法院於九十二年九月一日刑事訴訟法修正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精神之立法例後,特別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再次強調謂:「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等語(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二八號判例意旨參見)。此即學說上所稱基於嚴格證明法則下之「有罪判決確信程度」,對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據應證明至「無庸置疑」之程度,否則,於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自始被推定為無罪之人,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告無罪。 三、檢察官認被告等涉有上述犯罪事實,無非係以申○○之自白書、酉○○警詢中之坦承筆錄、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支付超捷環工水檢費支出憑證、支付旭貫公司污水處理藥劑憑證、壬○○提供之錄音帶譯文、、超捷公司之八十四年至八十五年營業稅申報書、超捷公司八十三年至八十五年彰化商業銀行活期存款明細紀錄、大園郵局第036955號午○○存簿儲金帳戶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明細紀錄、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辦理污泥清運八十四年十月三日內簽、八十四、八十五年間桃園縣事業廢棄物清除業者名單、桃園縣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廠商協進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錄及理、監事、會務人員名單、巳○○、壬○○、魏碧珍共同簽訂之超捷環工環工部合夥契約影本、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污泥清除工程(五、六月份)招標案卷、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污泥處理招標專卷、大益環保有限公司之八四廢清字第零貳零伍之參號臺灣省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收執超捷公司八十四年十月七日至八十五年七月三十日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廠外紀錄遞送聯單(四聯單)、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收執大益環保有限公司八十五年二月八日至八十五年七月三十日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廠外紀錄遞送聯單(四聯單)、臺灣省政府環境保護處北區環境保護中心事業廢棄物稽查工作紀錄表(八十四年七月十八日查獲超捷公司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五條)、旭貫公司負責人丁○○、竹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己○○登記之名下公司、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辦理污水廠藥劑採購案八十三年一月四日內簽、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之化學藥劑使用總表案卷、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支付旭貫公司三百零五萬一千三百元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支票(支票號碼:AL0000000)、旭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臺 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000-00-00000-0明細紀錄、八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旭貫公司董事己○○電匯三百萬元予土地銀行古亭分行黃秀華帳戶之電匯單申請書暨黃秀華之臺灣土地銀行古亭分行活存第41769-9 帳號八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八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存款明細、辛○○設於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個人帳戶(帳號:000-00-00000-0)明細紀錄:八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存入款項、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之八十二年污水廠擴建工程廠區綠化工程招標案卷、合作金庫中壢支庫支票(支票號碼:KT0000000、KT0000000、KT0000000)三 張暨桃園縣觀音鄉農會收入傳票、工業區管理機構營繕工程暨購置定製變賣財物內部審核注意事項、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八十二年至八十五年會計年度支出憑證簿等文書證據。 四、惟查偵查檢察官所起訴上述四大部分之事實(包括本院上述認定部分被告有罪之四大部分事實),均僅籠統臚列上述各項文書證據,就何項證據究係證明何者犯罪事實,以及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均未有說明,致被告、辯護人屢以檢察官未盡舉證責任抗辯,且被告等均堅決否認犯行,本件於調查證據上先即面臨諸多困難。惟本院為被告等之重大利益及公平正義之維護,仍促使公訴檢察官區分各項犯罪事實盡其說服責任,並為調查證據如下: ㈠支付超捷公司公司水質檢驗費用,總計二百五十七萬七千九百零七元部分 1被告申○○辯稱(略以):超捷公司另設有環工部門,係由壬○○個人負責,其對此部分均未過問亦不知情等語。被告午○○辯稱(略以):基於充分授權及分層負責,此部分均授權各該主管依行政裁量處理,其並不知情等語。被告寅○○辯稱(略以):水質檢測發包屬管理中心業務組之業務,與環保組無關,其從未參與之,且水質檢驗部分,費用大部分用在試運轉,由工程顧問公司在做,工業區只是在做程序上代辦,依照工程顧問公司所預估之費用去上簽核准。有關招商、詢價部分,係由業務組卯○○單位做,申請排放許可依法必須做技師簽證認定處理功能,所以一定要有合格的環工公司去做,超捷是合格的環工公司,除無法為代檢測工作外,其餘均可。被告壬○○辯稱(略以):依據當時之水污染防制法二十二條規定,另外涉即第五十四條限期改善、第五十九條功能測試,包括二十二條本身提報廢水操作程序紀錄,都需要有合格的環境檢測公司才能做,共計三項要求。起訴書所載的檢驗費用其實包括前面三種工程驗收費用,以及第四種,大園工業局管理中心污水處理廠與施工廠商(榮工處)對於這個設備改善完畢後驗收參考數據。前三種要合格檢測公司資格,第四種依法令規定不須要。關於前三種的費用,我們有按規定在做,都有委託合格的檢測公司實施,而且都有向環保局報備,環保局那裡一定有資料,他們會再自己實際檢測後才定案。關於連續提供不實的檢測報告部分,起訴書所言也不對,因為水質檢測資料是在檢測完才會有的,而且部分是委託合格代檢驗公司完成的,是根據實際水樣完成的實際程序,更沒有提供其他廠商的估價資料。起訴書所載八十二年申請排放許可應該有誤,八十二年應該是申請結案用的功能測試,依據當時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四條的規定,須做功能測試,才可以結案說廢水處理設備改善完成,之後才可能申請排放許可,於八十四年這條修改,不須再提功能測試報告,只須提出放流水之檢驗報告即可向環保單位申請結案。超捷公司具有這個資格,功能項目很多,水質檢測是其中一項,對於水質檢測,超捷公司本身雖沒有資格檢測,但可以委託其他公司做,超捷這部分都有委託合格的公司施作,而其餘項目都是超捷可以自行完成的,最後由超捷提出「功能檢測紀錄報告書」,環保局核准之後才可以申請排放許可,申請排放可時,如已有功能檢測報告核可,就不需要做水質檢測,如果事後又被告發違反排放標準時,就要再做水質檢測等語。 2經查壬○○固然名義上為超捷公司之董事長負責人,惟實際上之負責人為申○○而非巳○○,此為被告等所不爭執在卷。又壬○○係與巳○○簽約,僅負責超捷公司「環工部」負責水質檢測之業務,不得過問參與污泥清運業務,有巳○○、壬○○、魏碧珍共同簽訂之超捷公司環工部合夥契約影本一件在卷可查。且申○○、巳○○亦證述相符在卷,又有壬○○所提出其與申○○通話之譯文一件在卷,是足認壬○○與污泥清運工程及工程款之請領等業務確未參與,至多僅係形式上用章而已。又巳○○為申○○之妻,經申○○使用其名義為超捷公司、有蓄環保公司名義上負責人,後超捷公司負責人改為壬○○,巳○○、壬○○對於污泥清運部分均不知情,亦無參與,而申○○就水質檢測部分,亦未參與,而係壬○○之業務,業據證人申○○證述在卷,而關於水質檢測業務,依上述合夥契約,亦非巳○○所得參與之事務,檢察官未能指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巳○○有參與污泥及水質檢測業務,合先敘明。 3又查關於水質檢測部分,八十二年間之「水污染防治法」規範尚嫌簡陋,並不似現行規定如此嚴密。經查大園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於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始取得排放許可證(許可案係於八十五年一月十五日申請),有桃園縣環境保護局九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桃環水字第0940701099號函所附「廢(污)水處理及排放許可證」一件在卷可查,其有效期間自八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九十年十二月十日止(參見本院審判卷㈧第三十八頁)。而當時有效(八十年五月六日修正之)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所定「放流水水質水量之檢驗測定,應委託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廢(污)水檢驗測定機構辦理」之規定,依據八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環署水字第五0九七四號函說明:「事業取得排放許可證時,主管機關將同時告知有關申報之規定。事業應即開始履行廢(污)水處理設施操作情形及放流水之檢測及用電紀錄及申報義務,故事業應於申領許可證前完成廢(污)水處理設施獨立專用電表之裝置」,定期申報應以事業取得排放許可證時同時告知有關申報之規定,事業應即開始履行廢(污)水處理設施操作情形及流放水檢測。至無須向環保機關申報放流水水質水量之單位,自行委託一般環境工程公司檢測放流水水質水量,屬該單位「內部自行檢視放流水水質之行為,不論當時或現今法令均無規範。有同上函文附卷可證(參見本院審判卷㈧第三十五頁)。足認本件檢察官所起訴之八十二年間,因大園工業區尚未取得排放許可證,工業區委請超捷公司所實施之水質檢測,即非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條所規範範圍,檢察官此處起訴尚有誤會。且環工公司不可能包山包海,具有所有檢測之能力及項目,是以相互間委請他公司針對各項專業檢測,法既無明文禁止,即屬可行。是被告壬○○所辯尚可採信。又八十二年間因為大園工業區進駐不少廠商,當時各家工廠並非申請排放許可,應該是申請結案用之「功能測試」,依據當時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規定,須做功能測試,始得結案說廢水處理設備改善完成,其後始有可能申請到排放許可。經查超捷公司具有得實施檢測之資格,功能項目很多,水質檢測是其中一項,對於水質檢測,超捷公司本身雖沒有資格檢測,惟可以委託其他公司做,祇要最後由超捷提出「功能檢測紀錄報告書」,經環保局核准,始可申請排放許可,申請排放可時,如已有功能檢測報告,就不需要做水質檢測,如果事後又發現有違反排放標準時,就要再做水質檢測。業經壬○○、部分由寅○○證述在卷,因而此部分查無違法情事。 ㈡支付大益公司清運一般事業廢棄物即污泥,總計一千五百萬零八千六百三十六元部分 1被告午○○、申○○均辯稱(略以):大益公司為依法參與招標之合法廠商,亦經上級機關同意以比價方式辦理,八十五年二月間之零星清運係在大益未確定得標前之空窗期,為免造成污泥無法清運,而委請大益公司暫為清運,一切均屬合法等語。被告辰○○辯稱(略以):僅係單純以協進會顧問及大益負責人丙○○友人身分,請大益幫忙清運,並無不法情事等語。被告丙○○辯稱(略以):辰○○認識我的兄弟,知道我在從事廢棄物清運工作,而我的大益公司當時確實有清運桃園縣內其他公家機關的污泥,例如林口工業區、中壢工業區,辰○○來找我告知大園工業區有工程可投標情事,我去投標,因為只有二家公司投標不符合規定而流標,流標後不久,我又接到大園工業區通知我及翼贊公司去議價,翼贊就是當初投標的另一家公司,因為我們二家提出費用都超出底價,工業區要求我們減低價格,議價現場有申○○、卯○○等人,到了減價二次時,翼贊不願意再減,我願意再減一次,減價價格還是超出他們的底標,翼贊則在第一次減價完後因不願意再減價即離開,我記得以工業區要求的清運總量計算,含稅後是八百多萬元,四千噸的清運總量,他們要求再減價,後來有人公布底價是六百三十萬元,所以我仍然沒有得標。午○○等人詢問我可否清運,我說只能清運三千噸,卯○○要求可否再多一點,因為工業區經費不多,請我幫忙,我才勉強說可以再多運二百噸,隔幾天之後才簽約,而簽約前就開始進行的清運,是零星方式清運,我記不得是誰找我的,並沒有簽約,是在議價隔天就開始清運,一直到簽約之前,這段期間給付我的清運費用是用簽約之後確定的價格去換算每一噸的價格請款的,這段期間的重量並不含在三千二百噸的重量裡面,此零星清運部分是否透過辰○○幫忙,我記不得等語。 2訊據證人即經濟部上級機關負責監標之庚○○結證稱(略以:「五百萬元以上的工程上級機關經濟部會派員參與監標,本件印象中,大園工業區他們有向部裏報名。經三次流標之後,進入議價程序,與公開招標相同不能告知底價,但得詢問投標廠商可否按照我們的底價來承包(不可先告知底價)。如果廠商願意,只能在上面寫願意按底價來承包,並把標單遞出後,我們再告知底價」等語。而會計單位曾對大園工業區管理中表示若能發包就發包,儘量不要用零星採購方式等語。 3證人丙○○(原名李文昌)結證稱(略以):我大益公司的清運許可證是台灣省政府發的,清運地點是全國區域,主管機關是台中市政府,因為我們公司跟桃園縣的某家公司發生違法的情事,一共有十七家包括我們公司,被桃園縣政府向省政府提出撤銷的我們的許可證,我還有訴願,因為一直沒有獲得答覆,我也不知道是否會被撤銷許可證,所以我當然繼續清運大園工業區的污泥,後來我有收到桃園縣環保局轉來的公文,說我及其他十幾家公司的清運執照被撤銷了,我才有依據向大園工業區通知說我沒辦法再清運污泥。訴願沒有下文,後來我也沒有再提出行政訴訟。辰○○到我家來找我,他認識我哥哥或弟弟,知道我在從事棄物清理的工作,我的大益公司當時確實有清運桃園縣內其他公家機關的污泥,例如林口工業區、中壢工業區。在這之前我並沒有承包過大園工業區的工程,我自己也看過他們有招標,但我沒有去投標過,我記不得是辰○○來我家之前或之後,我就自己去參與大園工業局這項工程,我去投標,但因為只有二家公司去投標不符合規定流標了,流標之後不久,我又接到工業區通知我及翼贊公司去議價,翼贊就是當初投標的另一家公司,因為我們二家提出的都超出底價,工業區要求我們減低價格,議價現場有七、八個人,有申○○、卯○○,還有無其他人我記不得了。當天我跟翼贊就再減價,到了減價二次時,翼贊不願意再減,我願意再減一次,減價出來還是超出他們的底標,翼贊在第一次減價完之後說不願意減價就離開了,我記得以他們要求的清運總量計算含稅後是八百多萬元,四千噸的清運總量,他們要求再減價,有人公佈底價是六百三十萬元,所以我仍然沒有得標。午○○等人說我可否清運,我說我只能清運三千噸,卯○○說能不能再多一點,因為經費不多,請我幫忙,我才說我勉強可以再多運二百噸,隔了幾天之後才簽約,開標現場辰○○也在為何簽約之前就已經先行清運?我記得是用零星方式清運,我記不得是誰找我的,並沒有簽約,是在議價隔天就開始清運,一直到簽約之前,這段期間給付我的清運費用是用簽約之後確定的價格去換算每一噸的價格去請款的,這段期間的重量並不含在三千二百噸的重量裡面。「零星清運」工業區是否透過辰○○幫忙我記不得了。當天不記得是否有談零星清運的事宜。記得在第三次流標之後才議價,日期是如何我記不得了。零星清運是在議價前或後我記不得了,清運零星的單價是依照三千二百噸去換算的。二0五0是議價,還是最後標單的價格我記不得了等語。經查有大益公司投標及得標資料在卷可證被告丙○○所辯有據。 4是本件既有經濟部派上級指導員監標,且依法辦理比價及減價程序,被告午○○、申○○於其等所得運用之行政裁量權限,就大益公司於底價六百三十萬元下所能清運之三千噸污泥,經議價為三千二百噸,不僅有利於紓解工業區內每日愈增之污泥量,且相當程度為工業區節省部分公帑,屬合義務性之裁量權行使。而辰○○雖曾力勸丙○○為短期之零星清運,並以自己之大貨車參與清運,惟既無證據其藉此取得不法利益,檢察官既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證明其等間有違法情事,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自難認被告等此處有圖私人不法利益之情。 ㈢支付旭貫公司污水處理藥劑費用,總計二千八百三十三萬五千二百元,及三百零五萬一千二百五十五元部分 1經查丁○○(業經本院發布通緝)與己○○為夫妻,而旭貫公司、旭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竹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寬昇股份有限公司、益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之負責人均為丁○○,己○○則為其中多家公司,包括旭貫公司在內之董事,此為己○○所勿爭執在卷,並有該五家公司之公司登記事項卡在卷可證。 2被告申○○、午○○及寅○○固不否認均有借貸現金予旭貫公司負責人丁○○之情,惟辯稱(略以):見該公司營運良好,係為貪圖現金,並無因而將採購工程違法予丁○○之公司承攬,當初亦不知道旭貫等五家公司均係丁○○家族之公司等語。被告辛○○亦不否認有借貸金前予丁○○之太太己○○,惟與旭貫公司之得標無關,就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於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支付旭貫公司三百零五萬一千三百元工程款,何以會分別匯入辛○○帳戶部分辯稱(略以):因為己○○積欠其金錢,而其中有些是其找友人黃秀華借的,因知道旭貫領到工程款,要求己○○以該筆款項清償部分債務,才將其中三百萬元電匯至土地銀行古亭分行黃秀華之帳戶,餘額五萬一千二百五十五元則逕行匯入辛○○帳戶,並非洗錢,更無用來分配交付午○○、申○○、寅○○等人等語。被告己○○辯稱(略以):旭貫等五家公司均係丁○○家族企業,其僅掛名其中部分公司之董事,惟未過問公司之業務,是丁○○要其向辛○○、午○○、申○○及寅○○等人借款週轉公司,因與施燕傾熟識而引薦認識,並非不法所得利益等語。 3訊據證人辛○○對於其與午○○、申○○,如何借貸及借貸數額予丁○○、己○○夫妻等情,結證稱(略以):「八十三年間曾陸續借己○○金錢,每次都是五十萬、一百萬元等金額,八十三年初她來找主任、副主任及我借錢,我借她一千二百萬元,其中兩百萬元是鄭主任的,三百萬元黎副主任的,我出七百萬元,利息是一分二。加上之前她跟我借的錢,她一共欠我大概一千五百萬元,其中一筆最大之金額為二百萬元,有先扣掉利息。借貸期間從八十二年前半年開始,最後一次是八十三年六月初他們公司要倒閉前一星期又向我借一百萬元,錢還是我哥哥從屏東匯上來給我的。這一千五百萬元沒有開支票,因為她不是一次借的,而是零零碎碎借的,中間借的過程都沒有寫,她也有參加我的合會,也曾經跟我標走會款,有註明是她標走某會的單據。我是賣掉位於台北市信義區的房子的錢借給她。我知道午○○、申○○亦有借錢給己○○,至於寅○○有無借我不知道。午○○是借兩百萬元、申○○借三百萬元。申○○、午○○借給己○○的錢,申○○是自己匯款,午○○是把自己的存摺、印章交給我及己○○,己○○直接把錢領走」等語。經核與被告午○○、申○○所辯係借款之情相符。辛○○並主動提供其所有中小企業銀行之帳戶,審判中並提出多件匯款證明,以證明其與己○○間早有多次借款關係,就有憑證之部分計算,己○○迄今至少積欠其九百七十三萬四千元(參見審判卷㈨第一一二頁以下。雖辛○○於審判中所述之借貸金額,包括午○○、申○○二人於審判中坦承借貸之金額,有與偵查中所述金額前後不符之情,因而導致偵查卷所附由辛○○自行提出記載分配之款項比例有所不合(提示八十九年他字第一二三六號卷㈠第一六五頁),惟檢察官於起訴書亦認午○○、申○○、寅○○及辛○○與己○○間確為借貸關係。 4有問題者在於,己○○向午○○、申○○、寅○○及辛○○等人借貸,是否係出面代表上述五家公司負責人丁○○向其等借貸,抑或係私人間的單純借貸,以及午○○、申○○、寅○○是否因而於辦理招標時,圖利旭貫公司或其他丁○○、己○○為負責人、董事之公司。經查己○○並不否認向辛○○等人借貸金錢係丁○○之主意,款項除用以週轉各公司之資金需求外,丁○○用作何用途其不清楚,因為其僅係掛名董事,不清楚公司之運作,現在五家公司均已倒閉,丁○○也不知去向等語。而己○○借貸用以擔保之支票,並非開具本人名義,發票人均為旭貫等公司票,次為己○○、辛○○所不否認在卷。而午○○、申○○及寅○○等人所貸予之款項,均係透過辛○○、己○○之引介,其等夫妻甚且與丁○○夫妻曾於借款前於餐廳舉行家庭聚會,午○○甚且直接將其存簿、印章交由辛○○,由辛○○、己○○提領,交己○○使用,此均為被告等所坦承在卷。足認被告等與己○○間之借貸,已非單純之私人借貸,至少係丁○○代表公司之借貸,至於是否為被告等投資丁○○公司之資金,因檢察官未提出積極證據證明,且起訴書亦認屬借貸關係,本院尚不置喙。至於被告午○○、申○○及寅○○等人,有無因為此等借貸關係,進而圖利旭貫公司得標污水處理藥劑工程,經查檢察官認上樹旭貫等五家公司均為丁○○、己○○之持股公司,而無證據證明旭貫公司以外之其他四家公司為「空殼公司」,換言之,即便如被告等(尤其寅○○)所言,係因為零星採購,林時需要大批之污水處理藥劑,而不及辦理招標,則此時參與詢價之公司均為丁○○為負責人之公司,檢察官未能證明當時尚有其他足以承攬該等工程之與丁○○、己○○無關之公司,遭被告等排除在外,則無論係由旭貫或其他四家中任何一家公司得標,均屬丁○○為負責人、董事之公司,且均有承作能力,在當時並無公平交易法或政府採購法的年代,難謂有圖利特定私人之情。是檢察官認自八十二年起至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止,總計支付旭貫公司之二千餘萬元為圖私人不法利益之金額,尚嫌速斷。 5又檢察官提出午○○、申○○、寅○○及癸○○等人,於八十三年六月間,以緊急採購化學藥劑PAC、硫酸鋁、液咸之名義,由卯○○連續分批向旭貫公司詢價,採購污水處理藥劑金額高達三百零五萬一千三百元,且當月份所採購之六月七日、六月十一日、六月十五日、六月十七日、六月二十二日、六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七日之採購金額均超過「注意事項」規定之五十萬元上限額,竟未辦理公開招標,直接以詢價方式辦理招標。旭貫公司又適於當月因債務問題宣布倒閉,且依八十三年六月份之「污水廠化學藥劑使用總表」,當月並無硫酸鋁七二○噸及液咸二六○噸之進貨紀錄,由大園工業區管理中心開具同年六月二十七日為發票日之支票(號碼AL0000000) ,面額三百零五萬一千三百元正,隨後即由出納辛○○直接將該支票款經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電匯三百萬元予土地銀行古亭分行之「黃秀華」帳戶,扣除匯款匯費四十五元,餘額五萬一千二百五十五元,逕行匯入辛○○設於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個人帳戶(帳號:000-00-00000-0),當日再由「黃秀華」提現交辛○○匯總款額,分配交付午○○、申○○、寅○○等人。用以證明被告等人確有圖利私人之證據。 6就上述三百零五萬一千三百元工程款之部分,經訊據被告等均辯稱不知道旭貫公司經營不善之情,否則不致於將倒閉前尚借貸數百萬元之金額等語,而訊據辛○○固不否認其收到上述由工業區開具予旭貫公司之三百零五萬一千三百元支票,惟辯稱,係因己○○積欠其一千餘萬元,而其中部分是其向「黃秀華」及其他親友借來借予己○○者,因而經己○○之同意,直接電匯三百萬元予「黃秀華」之帳戶,零頭匯入自己之帳戶,其後提領而分別清償親友,並無分配予午○○等人。經查上述於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匯入「黃秀華」帳戶之三百萬元,隨即於翌日轉入辛○○丈夫謝朝龍設於臺灣土地銀行之帳戶內,隔日又提領一百六十一萬二千元,分別清償各親有,其中償還黃秀華四十萬元(二十五萬元匯入黃秀華花旗銀行帳戶內)、辛○○二嫂吳金月三十五萬元、五十四萬元存入辛○○設於台灣中小企銀之帳戶、三十五萬二千元存入被告大園郵局帳戶,另於八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償還被告兄長施泰安一百萬元,所餘款項則轉定存。有被告所提出之各今融機構交易明細表或匯款單據等附卷可查(參見本院卷㈩第三十六頁以下)。檢察官未能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將三百萬元分配午○○、申○○及寅○○三人,而辛○○又提出上述足生合理懷疑之資金流向,確與被告午○○三人無關,自難以認定被告午○○等三人,曾分配到上述款項。是難以此處證據遽斷被告等有圖利旭貫公司私人之犯行。7末查依辛○○所提出之存提明細,記載於八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八十一年一月十四日、四月十四日、六月十五七月十四日分別均有「大益」入款之紀錄,引人是否與上述大益公司有關之懷疑。惟辛○○堅決否認「大益」為「大益公司」,辯稱是其借貸一位台中的親戚,名為「戊○○」之利息錢,此經本院查詢結果,確有辛○○所指之戊○○其人,有戶籍謄本一件在卷可證。僅能視為巧合,而無證據證明辛○○與午○○等人之犯行。 ㈣支付大堀種苗園即酉○○污水處理廠之綠化工程費用,總計二百萬七千一百五十三元部分 1被告被告申○○、午○○、寅○○及癸○○均辯稱,此係合法招標之工程,由卯○○主辦,其等並不知情。被告酉○○辯稱(略以):是卯○○告知園區內有綠化工程要招標,請其來投標,並且需要有三家公司參與投標,因而其去商借另兩家親友所開設之公司參與投標,並由其代出投標金等語。2經查被告上述所辯,核與卯○○之警詢筆錄陳述相符。是被告酉○○確係經卯○○之「建議」而參與本件工程投標,並另行經親友同意下,以「中國造園社」及「資群公司」名義之投標單,與其經營之「大堀種苗園」共同參與投標,並代為代墊押標金,並無證據證明卯○○對此知情,進而難認被告午○○、申○○知情,而更與非業務組之寅○○無關。再查本件工程開標當時,被告經營之大堀種苗園係以「一百九十七萬元」得標,未超過其預定底價之二百萬七千一百五十三元,且當時該工業區管理中心承辦人員為節省費用,仍建議被告再行減價,經被告同意後,核定以「一百九十萬元」決標,就主持開標作業之被告午○○等人,被告酉○○僅認識卯○○一人,其餘申○○、午○○、寅○○、癸○○人被告並不認識,並無證據證明被告酉○○於事前曾告知卯○○或午○○、申○○等人,其將另行借牌之事,卯○○亦未指示被告借牌圍標,已難認被告與其等間有圖利私人之犯意聯絡。且被告午○○等人如有圖利被告之犯意,大可逕由被告以一百九十七萬元得標,何須要求被告再行減價七萬元,減少被告預期可得之利潤。又查「中國造園社」為被告胞兄鍾爵章所開設,「資群公司」則係被告女婿黃兆鳳所開設,被告既事前向之借牌參與投標,自無未經權利人同意或授權填載之偽造文書之可言。又依當時有效「稽察條例」第十九條規定之意旨可知,工程發包人員對投標廠商之投標單等資料並非僅有形式審查權,而係擁有「實質審查權」,以判斷是否有圍標之事實,是被告所為,即難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構成要件。末查「中國造園社」及「資群公司」既均非空殼公司,其等均有能力施作本件工程,且當日開標並無此三家廠商以外之其他廠商參與投標,而不論此三家中之任一家廠商得標,均有能力施作本件工程。又即便被告與另兩家廠商私下協議投標金額,或逕由被告代為填載,而是否開標或可否得標,尚須視有無此三家以外之其他廠商參與而定。在當時並無公平交易法及政府採購法之年代,難認被告所為屬違法之圍標,更難遽以推論被告與被告午○○、申○○等人有共同圖利私人之犯行。 ㈤至癸○○固係擔任業務組長,惟依申○○之自白書及警詢自白筆錄,其並未與被告申○○、午○○、寅○○等人合夥成立超捷公司,而業務組與申○○、午○○、寅○○有犯意聯絡者為卯○○,據卯○○之警詢筆錄,提供三家公司不實估價單及向之推薦超捷公司者,均係申○○、寅○○二人跳過癸○○而對其所下之指示。又據壬○○所提出之前述其與申○○、謝生民三人對談之錄音帶,經本院勘驗結果,申○○曾提及「癸○○是沒有事,他根本不知道」、「癸○○不是什麼監督職責,比較不知道」,謝生民則回以「問題就是怕沒有事被調去問」、「越沒事的一問就套出來了」等語。更足認癸○○對於被告申○○、午○○、寅○○及卯○○之犯行均不知情,更未參與,固然卯○○為業務組之下屬,其監督下屬固有疏失,惟檢察官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之下,尚不能據此遽斷其犯行。 五、綜上所述,公訴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難以使本院形成被告辛○○、己○○、巳○○、癸○○、壬○○、丙○○、辰○○、酉○○,等有罪之心證,而被告等是否有如檢察官所指犯行,尚有前述合理懷疑之存在,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本件既就卷內現存證據及本院依職權調查之證據,均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等有涉犯檢察官所指犯行,依前述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等犯罪,即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示審慎,惟就被告申○○、午○○及寅○○三人,因檢察官認此部分犯行,與本前經認定有罪之犯行,有修正前較有利於被告之刑法關於連續犯、牽連犯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因而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八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生效貪污治罪條例第二條,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第八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十條第二項,刑法第十一條、第二條第一項前段、修正前第二十八條、第五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雅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2 月 21 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 孟 宜 法 官 黃 翊 哲 法 官 錢 建 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 中 華 民 國 97 年 2 月 5 日書記官 李 玉 華 附件:本院九十三年二月十六日所為九十年度訴字第四二號刑事裁定書一件 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未遂犯罰之。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 犯第 4 條至第 6 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 4 條至第 6 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 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貪污治罪條例第10條 犯第 4 條至第 6 條之罪者,其所得財物,應予追繳,並依其情節分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 前項財物之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為保全前二項財物之追繳、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