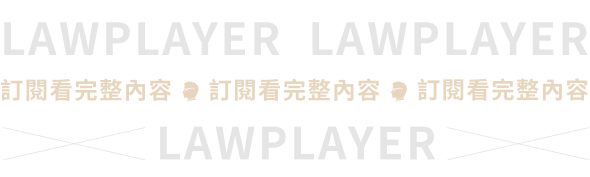要旨
收養媳婦仔之事由發生於日據時期,使媳婦仔身分換為養女之事由發生於臺灣光復後民法親屬編修正 (民國七十四年) 前者,則須依修正前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規定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二條所定之養女身分」。 參考法條:民法 第 1079 條 (89.04.26)
案由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九十年度判字第四九四號原 告 許盧葱妹 訴訟代理人 劉帥雷 被 告 桃園縣八德市戶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汪榮鐘 右當事人間因戶政事件,原告不服臺灣省政府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八八府訴字第一六○六四九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緣訴外人彭秀榮認原告戶籍資料稱謂登載為養女,係被告誤錄所致,又因原告不願配合辦理更正,乃以利害關係人身分申請更正其稱謂為家屬,案經被告查明屬實後,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函請原告限期辦理更正未果,被告遂依利害關係人所請浮籤更正完竣。嗣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原告以原稱謂並無錯誤,申請再更正為養女,為被告以所提證明文件不足以證明收養關係之存在為由,否准所請。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再訴願均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訴。茲摘敍兩造訴辯意旨於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一、按「在養家無特定匹配男子(俗稱無頭對)而收養之媳婦仔嗣後於養家招贅或由養家主婚出嫁,於具備當時有關收養之要件者,雖應視為自該時起與養家親屬間發生準血親關係,其身分即轉換為養女。惟此係就收養媳婦仔及使媳婦仔身分轉換為養女之事由均發生於日據時期者而言。」法務部八十四年十二月五日法八四律決二八一五九號函釋在案。惟原決定書認原告「故有婚書可證婚約之成立,然未有親迎及合巹等結婚儀式。且定婚後尚可因特定事由使婚約解消,是以訴願人所提婚書尚難認定其已有結婚之事。」然查,原告與袁方增之婚姻,乃當時當地之人所得共聞共見,媒人袁徐雖已百年,其子袁奕養、媳袁吳長等人俱曾參與原告結婚之儀式,足資作證。原告由養家主婚出嫁,乃係客觀存在之事實,豈可因婚書未記載成親日期,即否定其存在。二、又查日據時期判例:戶口簿上之有關身分關係之記載,並無確定之效力。(大正十四年上民字第四十號同年五月十八日判決)在本島人(指臺灣人民)間之婚姻,並非以聲請登記為有效要件,如既事實上締結婚姻,即有其效力。(大正六年控字三一七號同年七月十八日判決)而原決定書不察,豈可一再舉日據時期戶籍簿無結婚之登記,否定原告在當時成立之婚姻,更何況原決定書連袁阿增或袁方增都無法確認下,又如何認定其婚姻狀況或配偶何人。三、原決定書即引婚書記載,認定婚書作成時,原告應尚未依當時習俗舉行結婚之禮,卻何以婚書上,一再言及原告稱謂為養女,例如:「主承婚字人彭奎契等先年立有養女名喚盧氏蒽妹...招得奎契養女結為夫妻...」原決定書卻又不採認,顯有雙重標準之嫌。況又依戴炎輝教授見解「養媳,在其本質上既係收養,故未婚男子父母,可單獨逕將養媳身分變更為養女。」(臺灣民事調查報告第一三二頁)是以更勿庸置疑原告本係養女之身分。四、媳婦仔與養女,兩者在觀念上有區別,實際上卻不僅甚難區別,而表示的名稱亦屢被混用。(臺灣私法第五九六頁)原決定書因原告於本姓上冠以養家姓,且戶口調查簿續柄欄載為媳婦仔,即認定原告係養媳,非養女,而不深思媳婦仔與養女身分之互換及養女身分本質為何,則實有謬誤。「養媳可變更為養女,養女既不以擬配養家男子為目地,而於其本姓冠養家姓,則與養父母間發生與親生子女間相同之親屬關係。」(臺灣民事調查報告第一三八頁註九一記載)是以原告雖於本姓冠養家之姓,卻仍無損原告養女之地位。原決定豈可因原告冠養家姓,而非從養家姓,即認定原告之身分,寧非失之草率。本案原處分、訴願及再訴願決定均顯有違誤失平,請判決併予撤銷。 被告答辯意旨略謂:一、原告以日據時期臺灣人間之婚姻,並非以聲請登記為有效要件,如既事實上締結婚姻,即有其效力。惟本案被告經調閱相關資料後,發現下列諸多事證均無法顯示原告與阿增有客觀的夫妻關係事實存在:1、原告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均未有婚姻之記載。2、原告大正四年養子緣組入戶後姓名為彭盧葱妹,迄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初次申報戶籍登記申請書仍記載彭盧葱妹,期間並無袁盧葱妹之記載,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與許陳桂辦理結婚登記時始改冠夫姓為許盧葱妹。3、原告民國三十五年初次申報戶籍登記申請書記載為戶長彭奎契之家屬,且配偶欄係空白。4、原告昭和十七年至民國四十二年間所生之子女彭美代子第六人均係原告之非婚生子女(全部經生父許陳桂認領)。5、原告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彭奎契證婚與許陳桂結婚,如前次婚姻屬實有效,養家將其二次出嫁有悖常理。6、原告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與許陳桂辦理結婚登記時結婚登記申請書,前配偶姓名及其去處欄位記載為「初婚」,意謂原告與許陳桂結婚前婚姻狀況係未婚。7、查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新竹州桃園郡八塊庄八塊三百四拾五番地戶主袁阿房戶內袁阿增個人事由欄亦未有與原告結婚之相關記載,同戶袁氏菁個人事由欄記載昭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婚姻入籍(依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初次申報戶籍登記申請書記載袁阿增之配偶為袁洪菁)。二、原告以原決定書內袁阿增或袁方增都無法確認下,又如何認定其婚姻狀況或配偶何人乙節,被告於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桃德戶字第一八五二號訴願答辯書及桃園縣政府八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八八府訴字第○六○五二八號訴願決定書中即己載明「方增係阿增之筆誤」。三、依法務部八十年八月一日法八十律一一六六四號函略以:「查日據時期被收養為無頭對之媳婦仔,嗣後於養家招贅或由養家主婚出嫁者,應視為自該時起與養家親屬間發生準血親關係,其身分即轉換為養女,惟仍須具備身分轉換當時有關收養要件」。(日據時期收養所應具備之實質、形式要件詳載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第一五六頁至一六二頁)。日據時期定婚之形式要件仍舊沿用清末習俗,當時婚姻成立之儀注大致為父母之命,為媒妁之言,婚聘財之授受,為婚書之交換。(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第六十五頁)。按此,婚書亦可僅為「定婚之證明」,且定婚之後尚可因特定之事由使婚約解消(詳載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第七十五頁至七十七頁)。另日據時期習俗上之成婚儀注概述如下:...至婚期,男備花轎偕媒婆往女家迎(親迎),花轎到男家時,新郎迎於門口導引新娘至新房,行共牢合巹禮...(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第六十八頁)。「合巹」俗稱食婚桌,新郎新娘進洞房後互拜,然後相對就桌,吃紅圓、飲喜酒、飲畢,進床,至此禮成(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第七十二頁)。原告所提示之主婚出嫁書約中記載「...即將妹與阿增擇日敬神合巹永為夫妻」,顯示原告於婚書製作時應尚未依當時習俗完成「敬神合巹」之禮,故原告之婚書尚不足以作為與阿增有結婚之證明。原告以戴炎輝教授見解「養媳,在其本質上暨係收養,故未婚男子父母,可單獨逕將養媳身分變更為養女。」惟本案除原告大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迄民國三十五年光復前所有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均有「彭奎契媳婦仔」之記載外,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初次申報戶籍登記申請書更係以彭奎契之「家屬」申報登記,據此,實無從認定原告之養媳身分已變更為養女。四、原告謂「養媳可變更為養女,養女既不以擬配養家男子為目的,而於其本姓冠養家姓,則與養父母間發生與親生子女間相同之親屬關係。」惟本案在於無從認定原告之養媳身分已變更為養女,且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稱:「養媳與養女不同之點,在於養媳係以將來擬婚配家男或養男(未出生或未收養均非不可)為目的,養女則否。又養媳係以將來必成之為子婦為目的而養入之異姓女子,猶如已婚之婦,於其本姓上冠以養家之姓,對於養家之親屬發生姻親關係;養女則異乎其是,並無上述與養男結婚之目的。又養女從養家姓,對養家之親屬發生與親生子女同一之親屬關係,故養媳與養女,其身分關係完全不同(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第一二八頁)。本案原告原名盧葱妹大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養子緣組入戶後係以其「本姓冠以養家之姓為彭盧葱妹」,並非從養家姓,且續柄欄亦記載為媳婦仔,依上開見解原告當時之身分「應屬媳婦仔而非養女」。五、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初次申報戶籍登記申請書記載原告為彭奎契之家屬,抄錄戶籍簿頁時載為戶長彭奎契之養女,其身分如何轉換,經查並無原告被彭奎契、彭吳應收養相關登記資料。依法務部八十四年十二月五日法人四律決二八一五九號函略以:「至於收養媳婦仔之事由發生於日據時期,使媳婦仔身分換為養女之事由發生於臺灣光復後民法親屬編修正(民國七十四年)前者,則須依修正前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規定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二條所定之養女身分」。本案於查無原告與彭奎契、彭吳應間有收養關係之相關登記資料,且原告亦未能提供足資證明與彭奎契、彭吳應間有收養關係之情形下,依戶籍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變更、更正、撤銷登記以本人、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受理利害關係人彭秀榮之申請將原告稱謂養女更正為家屬,同時於受理更正登記前並依內政部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台(八一)內戶字第八一○六八三九號函釋規定通知原告自行申請更正稱謂為家屬,逾期將由利害關係人彭秀榮申請更正,因原告逾期未更正亦未提憑足資證明與彭奎契、彭吳應間有收養關係之證明文件辦理補填養父母姓名,本所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四日受理利害關係人彭秀榮委託蔡長泰先生到所辦理更正原告稱謂養女為家屬並無不當。原告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委由劉帥雷先生持憑彭奎契親屬系統表、戶主彭奎契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初次申報戶籍登記申請書等證明文件申請更正原告稱謂家屬為養女,因所持證明文件均不足以認定原告與彭奎契、彭吳應間有收養關係之事實,故被告未予受理原告更正之申請及一再訴願機關之決定均無違誤。原告之訴無理由,請予駁回。
理由
按於日據時期被收養在養家無特定匹配男子(俗稱為無頭對)之媳婦仔,嗣於養家招贅或由養家主婚出嫁者,雖應視為自該時起與養家親屬間發生準血親關係,其身分即轉換為養女,惟仍須具備身分轉換當時有關收養要件。(日據時期收養所應具備之實質、形式要件詳見前司法行政部印行之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第一五六頁至第一六二頁),且此係指其收養媳婦仔及使媳婦仔身分轉換為養女之事由均發生於日據時期者而言。至於收養媳婦仔之事由發生於日據時期,使媳婦仔身分轉換為養女之事由發生於臺灣光復後,民法親屬編修正(民國七十四年)前者,則須依修正前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規定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二條所定之養女身分。此為有關法律適用上所當然。查訴外人彭秀榮認原告戶籍資料稱謂登載為其祖父彭奎契之養女,係被告誤錄所致,乃以利害關係人身分申請更正原告稱謂為家屬。案經被告查明屬實,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函請原告限期辦理更正未果,被告遂依利害關係人所請浮籤更正完竣。嗣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原告以原稱謂並無錯誤,申請更正為養女。被告以所提證明文件不足以證明收養關係之存在為由,否准所請。原告不服,訴經桃園縣政府、臺灣省政府一再訴願決定,以原告原名盧葱妹,於日據時期大正四年養子緣組入戶後係以其本姓冠以養家之姓為彭盧葱妹,非從養家姓,且戶口調查簿續柄欄亦載為媳婦仔,足見其當時身分應係養媳而非養女,次查日據時期昭和十四年原告由養家主婚出嫁書約所載「...即將葱妹與方增(或係阿增之筆誤)擇日敬神合巹永為夫妻...」,觀其意,此婚書作成時原告應尚未依當時習俗舉行敬神合巹之禮。我國古來,為將婚姻與野合加以區別,規定有一定方式,以之為形式要件,一為定婚、二為成婚,定婚以男女兩家之合意,婚書之作成及聘財之授受等為中心,即是婚約之締結,成婚以親迎及合巹為中心,此乃結婚之儀式,婚書僅係婚約成立之證,(參照前司法行政部編印「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第六四、六五、七五至七七頁),是以原告所提婚書尚難認定其已有結婚之事實。再查原告及訴外人袁阿增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均未有對方結婚之相關記載,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初次申報戶籍登記時,訴外人袁阿增申報之配偶為袁洪菁,原告之配偶欄位則係空白未填載,迄民國四十二年與訴外人許陳桂結婚辦理登記時,其結婚登記申請書之「前配偶姓名及其去處」欄仍填載為「初婚」,且至此始將所冠養家姓彭盧葱妹改冠夫姓為許盧葱妹。另原告於昭和十七年至民國四十二年間所生子女六人,均係經訴外人許陳桂認領為婚生子女,據此,實難證明原告與袁方(阿)增間已有客觀之夫妻關係事實存在。且民國三十五年初初申報戶籍登記申請書「關係人」欄申報原告為戶長彭奎契之「家屬」,戶籍簿頁應係依據申請書抄錄,其記載為戶長彭奎契之「養女」,其中身分之轉換,顯係誤錄所致,遂認原告所訴無理由,駁回其一再訴願。揆諸首揭說明,核無違誤。茲原告起訴仍執前詞,謂日據時期之婚姻,不以登記為有效要件,如事實上締結婚姻,即有其效力,原告所舉婚書上一再言及原告稱謂為養女,例如:「立承婚家人彭奎契等先年立有養女名喚盧氏葱妹,...招得奎契養女結為夫妻...」,原決定不採,顯有雙重標準云云。除原決定業已論明,不再贅述外。查原告於日據時期大正四年以養子緣入戶主彭奎契戶內為媳婦仔,已如前述,並有日據時期戶籍資料附原處分卷足證。此後亦從無與訴外人袁方(阿)增結婚之確切事證,至所舉婚書影本雖有「...即將葱妹與方增擇日敬神合巹永為夫妻,...」之記載,然既稱「擇日」,則其婚書作成時原告與袁方(阿)增並未即完成婚禮,尚待擇日合巹成婚。原決定認該婚書僅可作為原告與袁方(阿)增婚約之證,即非無據。原告以該婚書證明其已由養家彭奎契主婚出嫁與袁方(阿)增,其媳婦仔身分已轉換為養女云云,即不足採。此外亦無其他具體事證足證原告於日據時期與袁方(阿)增有結婚之事實,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將其戶籍上稱謂重新更正為養女,即不足取。其起訴意旨難謂有理,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二條、行政訴訟法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三 月 二十九 日最 高 行 政 法 院 第 五 庭 審 判 長 法 官 廖 政 雄 法 官 黃 璽 君 法 官 趙 永 康 法 官 林 清 祥 法 官 姜 仁 脩 右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法院書記官 彭 秀 玲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三 月 三十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