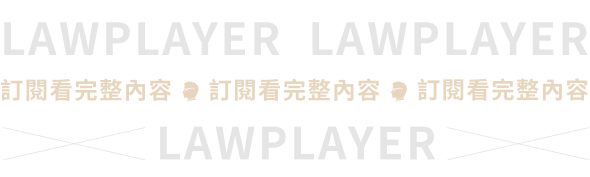案由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六年度重上字第一九七號上 訴 人 潘月雲 (即潘越雲) 訴訟代理人 黃榮謨律師 複 代理 人 呂孟儒律師 被 上訴 人 飛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鳳崗 訴訟代理人 徐小波律師 蔡東賢律師 黃心漪律師 右當事人間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六年重訴字二0三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甲、上訴人方面: 壹、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 ㈡右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台幣(下同)壹仟萬元,並自八十六年一月十四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㈢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㈣本件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貳、陳述:除與第一審判決記載相同予以引用外,補稱: 按『解釋私人之契約應通觀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以期不失立約人之真意』、『解釋當事人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不得拘泥字面,致失當時立約之真意。』、『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十八年上字第一七二七號判例、十九年上字第五八號判例及十九年上字第四五三號判例分別著有明文。而本件兩造間簽訂有歌星合約,至於合約書第六條所謂『乙方(指上訴人)同意於合約期間內,至少為甲方(指被上訴人)錄製三張新歌專輯:::且甲方有權視需要增加其錄製母帶之數量。』應作如何解釋?實有探究當事人真意之必要? ㈠按上訴人從事演唱工作多年,為一知名歌手,有相當之知名度已為眾所週知之事實。是上訴人簽約所在意者係唱片公司如何來推銷歌手,如何來延續歌手之演唱生涯,並創造渠演藝生涯之高峰。按演藝人員必須不時推出新作給歌迷大眾,以便保持與歌迷之聯繫,尤其在競爭激烈之唱片市場,更屬必要。是就本件歌星合約中除約定報酬外,上訴人所最關切的應是新歌專輯之發行數量多寡,故於合約書第六條末段規定『:::且甲方有權視需要增加其錄製母帶之數量。』,從文字僅規定『有權增加』而非規定『有權增減』,可探知當事人真意在於至少應發行三張新歌專輯。 ㈡況依合約書第二條規定『合約期間內,乙方同意獨家為甲方演唱,:::上述權利乙方不得再授與本身或任何第三者。』本條係關於勞務專屬之規定,依前揭規定在合約期間內,上訴人已喪失其怹任何演唱機會,而專屬於被上訴人。是若就第六條規定拘泥於文義,解釋為上訴人單方之義務,而認被上訴人沒有錄製之義務,是在被上訴人不為上訴人錄製新歌專輯之情況下,則上訴人演藝生涯不過啻平白中斷二年,渠所受傷害又豈是金錢得以彌補? ㈢再者,依合約書第四條『:::有關錄音、詞曲、編曲、槳手、編導、攝製:::等製作事宜由甲方按排及出資,乙方負責演唱:::」由前揭條文可知新歌專輯之所有『前置作業』均係由被上訴人負責,而上訴人僅需配合入錄音室灌錄即可!又合約書第七條末段亦規定『::每一張新歌專輯,甲方同意支付乙方新台幣一五0萬元之保證版稅,此項保證版稅於錄製前支付二分之一:::。』是被上訴人在錄製前亦負有給付保證版稅之『先行給付義務』,故所謂錄製新歌專輯絕非係上訴人之單方義務而已。 ㈣更何況依合約書第二十一條規定『如有違約行為,違約之一方應支付對方新台幣一、000萬元正之損害賠償。』該條規定係針對合約雙方而為規定,亦即對被上訴人亦有適用。故合約書第六條若僅解釋為上訴人單方之義務,則被上訴人永遠也沒有適用本合約書第二十一條規定之機會!此絕非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 ㈤末以上訴人為一知名藝人,過往所發行之專輯於市場上均有一定之銷售量,是本件合約中被上訴人所給付之三百萬簽約金,於上訴人而言其對待給付義務即為合約書第二條之『獨家演唱』,是上訴人亦付出代價(喪失其他工作機會),並非平白獲取報酬。是原審法院之見解,認上訴人收取簽約金係獲得相當之報酬,而被上訴人是否為上訴人出新專輯復為其權利云云,實係對演藝界『藝人簽約金』之性質有所誤會。更何況被上訴人一再掩飾真相,辯稱上訴人可另外從事〞演戲〞或〞拍廣告〞等之表演行為,亦係混淆視聽之說詞,按上訴人係一專職歌手,出道以來亦未曾從事演唱事業以外之表演行為,亦為上訴人所明知。捨此上訴人何以謀生? 二、再查被上訴人復於原審主張在合約期間內之所以未能完成三張專輯之錄製工作,係可歸責上訴人之事由,被上訴人洵屬不可歸責云云,惟查: ㈠按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於⒓⒌簽立合約後,被上訴人公司內部即進行股東改組,且人事異動情形極為嚴重,先是負責統籌製作上訴人專輯之製作人先後即更易數人(李世忠、丁曉雯、鄔裕康)以致整個專輯製作幾乎停擺,且每人在職期間極短上任不久旋即因故離職,根本沒有任何進度可言,如此豈可將責任歸責於上訴人,至於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之工作底稿及製作人記事簿節本,不論就形式及實質證明力,上訴人均予否認。 ㈡又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於八十五年四月間提出醫生診斷書『需臥床休息陸個月,不宜勞累』,佐證上訴人拒絕履約云云。惟查上訴人交付被上訴人前揭診斷書,原係希望被上訴人能妥善安排錄製專輯之時間,依醫生囑咐盡量避免有熬夜錄製之情事,而非拒絕錄製,是被上訴人故意曲解。至於被上訴人復引媒體報導,略謂上訴人於合約期間『常頭痛沒法錄音』『遠離演藝圈退出人群』,而認上訴人拒絕配合錄合錄製專輯,亦係空穴來風。按媒體報導娛樂(演藝)圈新聞,往往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充斥,實非事實,亦為上訴人所否認。 ㈢又被上訴人以曾提出四十餘首砍曲供上訴人灌錄,因上訴人挑剔拒錄而未使用,亦非事實。爰就被上訴人內部唱片製作流程及所提出之歌曲、詞底稿加以說明。⒈就被上訴人公司唱片製作流程以觀: 按被上訴人就唱片製作流程與其他唱片公司不同在於:該公司內部設有『A&R』部分(即藝人產品發展部)專責〞音樂製作〞與〞專輯方向〞規劃;並握有決定〞製作人〞人選及〞詞曲〞篩選之主控權,是關於詞、曲之決定,歌手(即上訴人)根本沒有置喙之餘地,砍手僅參與對KEY及灌錄配唱。關於被上訴人公司唱片製作流程,請傳訊『該醒了』專輯之製作人許卿燿到庭結證,以明實情。 ⒉被上訴人公司所提之曲詞底稿: 惟該等詞曲或重覆甚多、或曲同詞不同、或詞同曲不同、或僅有詞未有曲、或台語歌曲(不適合上訴人風格)、或其間挑本上訴人未曾看過之詞曲。如此,豈可為係上訴人挑剔拒錄。 ㈣再者,上訴人本係隨時處於可提供勞務(配合灌錄)之狀態,且願意隨時配合被上訴人公司提供勞務,此尚可從被上訴人於八十四年九月間要支旗下歌手灌錄『相親相愛』合輯,上訴人在未支取任何報酬的情況下猶予以配合,足證只要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無不盡力配合,絕對沒有被上訴人所謂挑剔拒錄之情事,且上訴人並於八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合約期滿之後,依然配合專輯之灌錄,重新配唱、重新編曲之主打歌(該醒了)一曲。 叁、證據:除援用第一審之證據外,並聲請訊問證人許卿燿。 乙、被上訴人 壹、聲明:求為判決如主文所示外,並聲明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以現金或等值之華南商業銀行南港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貳、陳述:除與原判決所記載相同者,予以引用外補稱: 本件上訴人上訴意旨無非主張依兩造八十三年十二月五日所簽基本歌星合約(以下簡稱「歌星合約」)真意,被上訴人有為上訴人錄製專輯之義務,且雙方未於二年合約期間內錄製三張專專輯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云云。 惟查,本件無論依歌星合約整體內容或合約第六條明文規定觀之,雙方當事人真意均係以錄製歌曲專輯係上訴人之義務,而為被上訴人之權利,並非被上訴人之義務;且合約期間內雙方所以僅完成一張專輯之錄製實由於上訴人一再遲延配合為必要行為所致,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上訴人違約未履行合約義務之事實極為明顯,乃竟反誣被上訴人違約,其主張實屬無據。茲分別析述事實理由如下: 依歌星合約約定,錄製歌曲為上訴人之義務,而為被上訴人之權利,並非被上訴人之義務: ㈠歌星合約第六條明文規定:「乙方(上訴人)同意於合約期間內,至少為甲方(被上訴人)錄製三張新歌專輯(或至少三十首歌曲之錄音著作母帶)...」,,此項約定已明文表示合約期間內(至少)錄製三張專輯乃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應負之義務,毫無疑義。原審援引最高法院十七年上字第一一一八號判例,認為「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之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拾契約的文字而更為曲解」洵屬正確。上訴人拾此契約明文,執意曲解,顯屬顛倒是非。 ㈡歌星合約第二十條約定:「甲方(被上訴人)同意本合約簽約金為新台幣三百萬元正,於簽約時一次付清。」被上訴人並已依約付清款項,業於原審提出上訴人簽收款項之收據為證,上訴人亦不否認。按依目前國民所得水準,學有專長之大學畢業生,早出晚歸,工作一年所得往往不足四十萬。是此項簽約金之約定,於上訴人生活已提供優渥之保障。益證錄製專輯係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義務,而非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義務,其理甚明。 ㈢如上訴人所自承,歌手才華有賴唱片公司推銷始克彰顯;才藝過人,若乏唱片公司包裝促銷,亦難為消費大眾所共知。是則唱片公司既具備錄製、規劃、配樂、錄音、促銷等各方面專才,並有資力決定是否投資製作某歌手之專輯,依市場經濟法則,唱片公司於情於理實不可能簽訂全然圖利歌手,不顧公司立場之合約。苟如上訴人所曲解之合約內容:唱片公司憑白預付三百萬元,尚須背負為歌手規劃、收歌、配樂、配唱、錄音、促銷專輯等義務及違反義務時應負一千萬元損害賠償之責任,而歌手竟然僅單純負擔不為他人錄製專輯之義務(仍可為錄製專輯以外之表演,如演戲、拍廣告、單純演唱...等等)。試問被上訴人簽約之經濟利益何在?若果合約明文規定為歌手義務者,尚可如是曲解為唱片公司義務,則私法自治原則將蕩然無存,唱片公司亦將無以為生! ㈣上訴理由謂歌星合約第六條係約定被上訴人公司「有權增加」專輯數量,而非「有權增減」專輯數量,從而主張被上訴人僅有增加之權,而無減少之權。實則合約文字所以為:「被上訴人『有權增加』專輯數量」,係承上文:「上訴人應至少為被上訴人錄製三張專輯」而來,兩句文字合併解釋,後者意在強調甲方之權利,而非限制前者之文義,觀諸兩句連接詞用「且」而非用「但」,亦可見一斑。亦即此項約定之真意在充分保障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錄音之權利,而非限制被上訴人權利或被上訴人義務,用意甚為明顯。 ㈤上訴意旨謂上訴人同意在合約期間獨家為被上訴人錄製專輯,不為他人錄專輯,即為簽約金三百萬元之對待給付,其說詞顯然違反經驗法則。蓋上訴人若僅消極承諾不為他人錄專輯,而未積極負有為被上訴人錄製專輯之義務,則於被上訴人實無利益可言。被上訴人亦斷不致虛擲三百萬元,為此毫不利己之約定也。 ㈥上訴意旨又謂上訴人依歌星合約負專屬義務之同時,如依約無權要求被上訴人錄製專輯,則演藝生涯將中斷二年,其說詞實與事實不符。按歌星合約所要求於上訴人之專屬義務,乃不為他人演唱專輯之義務,並未禁止歌手為演戲,拍廣告片或錄製專輯以外之其他表演行為,上訴人誇大所謂專屬義務之範圍,曲解當事人真意及合約合理之解釋,顯屬無據。 ㈦上訴理由另謂依歌星合約第四條約定錄製專輯之前置作業由被上訴人負責,及第七條約定錄製前(進錄音間前)被上訴人應支付二分之一版稅,由此可推知錄製專輯亦係被上訴人義務云云。按此項推論忽略所謂「前置作業」及「半數保證版稅之支付」均係決定開始錄製專輯以後之事項,被上訴人如決定製作專輯,當然依相關規定辦理,然究非主張因合約中有被上訴人開始錄製專輯以後之規定,推論依合約約定被上訴人必有製作專輯之義務。上訴理由此項推論顯不符論理法則。 ㈧至於上訴理由所謂,如將歌星合約第六條解為上訴人單方義務,則合約第二十一條將無適用餘地,有違當事人真意乙節,亦與事實不符。姑不論被上訴人依歌星合約原有支付簽約金之義務,合約期間內如請求上訴人錄製專輯,另有保證版稅及銷售版稅之義務,非謂被上訴人依合約全不負義務。事實上,唱片公司與歌手簽約之條件乃取決於簽約當時雙方各自具有之市場價值及地位,苟約定內容無悖乎公序良俗,依私法自治原則即應尊重合約約定。於合約文字明確之場合,自無別事曲解之餘地。本案上訴人依合約所負專屬義務範圍,根本不致影響其生計,歌手以著眼於唱片公司錄製為遵守專屬義務及接通告之義務,投效唱片公司,換取唱片公司於適當時機考慮為該歌手包裝促銷之機會,並於實際錄製專輯時另行支領保證版稅及銷售版稅,其交易條件原無違反公序良俗可言。況上訴人已領取可觀之簽約金,依約負擔接通告錄製專輯之義務更無絲毫不合理。上訴理由再三指稱合約約定上訴人錄製專輯之單方面義務為非立約當時真意,顯屬無據。 ㈨末按上訴理由謂「簽約當時被上訴人給予上訴人之訊息為『二年三張專輯』,並無其他條件限制,依唱片界慣例,即雙方均負有出三張專輯之義務...」云云,其主張亦屬無據。按所謂「二年錄三張專輯」,合約明文係乙方(即上訴人)之義務,上訴人故意忽略該條文主詞,曲解為「並無其他條件限制」,其說詞顯非可採。上訴人如主張此種合約明文約定下,依唱片界慣例,竟係雙方均負有錄製專輯之義務,顯屬無稽,應就所謂「唱片界慣例」負舉證責任。合約期間內所以未完成三張專輯之錄製,實屬可歸責於上訴人而不可歸責於被上訴人: ㈠雙方未於二年內完成三張專輯之錄製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原因: 按錄製專輯之程序,係歌者與唱片公司共同配合進行「①製作會議商定專輯主題風格②收歌選歌③雙方對Key ,就選定歌曲由歌手試唱、與樂隊排練,以尋找最適合歌手之音階曲調(KEY)④公司進行編曲、灌錄演奏背景音樂(KALA)⑤歌者進錄音間錄製歌聲(配唱)⑥唱片公司進行混音工程,完成母帶」,其中①至⑤之程序非由歌手配合,無以完成,而本件合約專輯錄製工作所以未能如期完成乃因上訴人故事拖延、挑剔拒錄所致。相關事證如下: ⒈雙方簽訂歌星合約後,製作人李世忠先生即積極展開製作之工作,然因上訴人再三藉詞推拖,不予配合致無法進行工作,是李世忠先生擔任統壽製作期間,專輯錄製所以無進展,實因上訴人之推拖所致,此項事實,鈞院可傳訊李世忠先生為證,即可明瞭。 李世忠先生離職後,由製作人李子恆、王治平、丁曉雯接任製作工作,亦積極進行專輯製作作業,但上訴人配合意願仍然低落,多次取消既定配唱計畫,或稱病告假,相關事實已於原審提出工作底稿及製作人記事簿節本為證,足見上訴人亮無配合履約之誠意。 ⒉上訴人再三推拖之餘,至八十五年四月初索興提出醫生診斷書,藉詞須臥床休息六個月,表明拒絕繼續錄製專輯之意願。此項事實亦已於原審提出上訴人交付之中山醫院醫師診斷證明書為證,足證上訴人拒絕履約之事實。 ㈡被上訴人就隻方未完成至少三張專輯錄製工作,洵屬無奈且不可歸責,相關事證如下: ⒈本件被上訴人於簽約時即已支付三百萬元簽約金,其用意無非希望上訴人誠意履行錄製專輯之義務,俾被上訴人順利發行各專輯。於情於理上訴人絕不可能於付出三百萬元後,自行放棄要求上訴人錄專輯之權利,消極不進行製作工作。 ⒉依業界慣例及歌星合約約定,原應於歌手進錄音間配唱前始行支付二分之一保證版稅,然被上訴人本於愛護歌手之立場,於八十四年四月即預付第一張專輯半數保證版稅新台幣七十五萬元,業於原審提出請款單為證。試問被上訴人若無履約誠意,何須憑空支付上訴人半數保證版稅? ⒊被上訴人為錄製專輯,積極收歌,已於原審提出歌曲歌詞底稿為證。 ⒋被上訴人為維護錄製專輯之權利,於上訴人稱病告假期滿,立即函請上訴人配合錄製專輯;亦已於原審提出相關信函為證足證被上訴人積極錄製專輯之事實。 ㈢上訴理由辯稱上訴人非可歸責等節,均屬無據: ⒈上訴理由指稱被上訴人公司因股東改組,人事異動致專輯錄製停擺乙節,並非事實。蓋公司組織變動無礙其事業之永續進行;人事更迭,更不足以妨礙業務之正常推展。被上訴人公司組織變動期間,旗下其餘歌手固如常發行專輯,八十三年底至八十五年底二年間,發行數量約六十八張,有專輯發行紀錄單為證並未如上訴人專輯錄製之多所稽延,足見專輯錄製工作之阻礙非來自被上訴人。 ⒉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蒐集之詞曲,確多所挑剔,無理拒錄;上訴理由謂被上訴人藝人產品發展部專有詞曲篩選之權,上訴人無置喙餘地,並非事實。按依歌星合約第四條約定,被上訴人雖有安排詞曲之權,但音樂專輯之製作,乃藝術之表現,不能不顧及歌手之情緒。被上訴人刻意於合約中爭取安排詞曲之權利正足以顯示被上訴人地位之無奈。所謂立約從嚴,執行從寬。既已投資製作專輯,專輯製作過程中唱片公司為使歌手錄音時充分表達情感,展現動人旋律,無不曲意承歡,委屈求全。何敢觸怒歌手?事實上,於雙方完成之「該醒了」專輯中「何必當初」、「於心何忍」、「面具」、「誰辜負誰」等四首歌詞均係上訴人之未婚夫孫義志(筆名「達夫」)所撰歌詞,而上訴人猶感未足,其於上訴理由中指稱「無牽無掛」「覆水難收」「人生沒有不散的筵席」「紅顏」「夢境」未為專輯所錄用,言下之意,竟謂該專輯須全數使用其未婚夫所撰歌詞,始為合理乎?於此具見上訴人執意使用其未婚夫之作品,對其他歌詞輒多所挑剔,確屬實情。 ⒊上訴理由指稱上訴人所提出之曲詞底稿重覆甚多,不符合上訴人歌路及未交付上訴人過目等節,亦與事實不符。事實上,被上訴人就該底稿核計詞曲數目時,已將重覆者剔除,計算出總數約四十餘首。而所謂詞同曲不同,曲同詞不同,有詞無曲等節,係原始資料必有之現象,詞曲篩選過程當中,於各種版本之詞或曲中擇一最適當者,原屬合理。上訴意旨空言指摘詞曲底稿非真,顯然無據;其另指稱歌路不合,未見過該詞等更屬遁詞,委無可採。關於被上訴人積極收歌,上訴人則多端挑剔乙節,該專輯歷任製作人均可為證。 ⒋上訴理由謂上訴人隨時處於可配合且願配合灌錄之狀態,並援引其參與相親相愛專輯錄製及合約期滿後配合配唱之事實為證,所述並非事實,此可分以下三點說明: ⑴相親相愛合輯之錄製,與本案上訴人是否依本件歌星合約履行其個人專輯錄製,乃不相干之兩件事,殊不得以其偶為相親相愛合輯之配唱,即推論其亦履行本件專輯之錄製義務。猶如債務人不得以其已清償甲債務,而推論其必已清償不相干之乙債務。其理至明。 ⑵上訴人雖於合約期滿後配唱,然其時點距其提起本件訴訟,甚為接近,是否故作姿態,不得而知。要之,上訴人此項行動並不影響其合約期間內違約未履行錄製義務之事實,應屬無疑。 ⑶上訴人於簽訂歌星合約後,即因個人因素遠離人群,被上訴人為與其聯絡,而為其申請之呼叫器,上訴人亦中途退還。而費盡週章聯繫後,上訴人往往藉故挑剔拒錄,甚至稱病告假長達六個月,已如前述。根據媒體報導,上訴人於合約期間內「常頭痛沒法錄音」「遠離演藝圈退出人群」「從沒有斷過之傳言此起彼落...包括經濟拮据、潦倒度日...幾乎與世隔絕」可見上訴人所謂其簽約後始終處於可配合且願配合之狀態,顯屬不實。 三、綜上所述,本件依兩造歌星合約之約定,錄製專輯實為被上訴人之權利,被上訴人並無為上訴人錄製專輯之義務,且被上訴人於支付三百萬簽約金後雖極希望上訴人多多錄製專輯,但雙方終究無法於合約期間內完成三張專輯之錄製,其原因實屬可歸責於上訴人。上訴人既未誠信履約,乃竟顛倒是非,圖謀非份,其請求損害賠償實屬無據;而其明知無理,猶執空言,無端興訟,濫行上訴致被上訴人續遭訟累,徒損勞費,顯已辜負法律保障私權之意旨。 叁、證據:除援用第一審之證據外 一、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影本乙件。 二、發行專輯統計表。 三、剪報影本乙件。
理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原任法定代理人吳楚楚已解任董事長職務,由姚鳳崗接任董事長,其聲明承受訴訟,依法應予准許,先予敍明。 二、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兩造間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五日訂立「基本歌星合約」,期間兩年,約定在契約有效期間,上訴人至少可灌錄三張新歌專輯,被上訴人亦應至少為上訴人灌錄出版三張新歌專輯,惟迄合約終止時止,被上訴人僅為上訴人灌錄一張專輯,被上訴人顯然違反兩造「基本歌星合約」,依合約的第六條之規定,應給付損害賠償一千萬元,爰提起訴訟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則以:兩造間「基本歌星合約」約定錄製歌曲專輯為上訴人之義務,且為被上訴人之權利,而非義務,被上訴人於簽約時已給付簽約金三百萬元,並給付第一張專輯半數保證版稅七十五萬元,被上訴人已為上訴人製作一張專輯,其他之專輯未能製作完成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並非被上訴人違約,上訴人請求依約賠償一千萬元,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綜觀兩造間八十三年十二月五日所簽訂之合約書,其雙方應負之義務為:被上訴人於簽約時有約給上訴人簽約金三百萬元之義務(合約第二十條),支付保證版稅之義務(合約第七條),給付版稅之義務合約第八、九條)。至於上訴人則於合約期間內獨家為被上訴人演唱錄製錄音著作母帶及演出錄影視聽著作母帶,且至少為被上訴人錄製三張新歌專輯,如被上訴人需要時則增加錄製母帶之數量,此觀兩造不爭執之合約書自明,本件合約兩造之權利義務均甚清楚,均有對價關係,並無違反公序良俗或強制或禁止之規定。依本合約書之規定被上訴人於簽約時已付給上訴人簽約金三百萬元,出版第一張專輯前已付給保證版稅之二分之一計七十五萬元予上訴人,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則被上訴人依合約上所定之義務已盡,至於被上訴人是否錄制三張專輯唱片或予以增加數量,則由被上訴人視實際需要而斟酌,上訴人於被上訴人需要錄製時,有配合之義務。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應有錄製三張專輯唱片之義務。 本院查: ㈠被上訴人於簽訂合約書時已付出簽約金三百萬元,其付出之三百萬元,無非想從日後製作專輯唱片銷售後回收,否則何必付出此三百萬元,其如認為發行專輯唱片後可回收,勢必積極於合約期間內錄製專輯唱片發售,反之,如認發行專輯唱片銷售後,非但無法回收,恐有虧本之虞時,仍勉強發行,對被上訴人企業之經營,將造成莫大之損害,因此簽約後,被上訴人應有權衡量是否製作發行,其不製作發行時,應係權利之放棄,而非不履行義務。 ㈡上訴人在合約期間內,確係受合約第二條「乙方(上訴人)同意獨家為甲方(被上訴人)演唱錄製錄音著作母帶及演出錄影視聽著作母帶,上述權利乙方不得再授權與本身或任何第三者。」之拘束,在此合約期間,上訴人仍可為演戲,拍廣告單獨演唱等之行為,同時上訴人為防止被上訴人簽約後故意不製作專輯之情事發生,於洽談合約時,可提高其簽約金,以防堵之,被上訴人在付出巨額之簽約金後,為無重大事由,定今依合約久內容履行,否則其何必平白付出簽約金?由此可知,錄製專輯唱片或影帶係被上訴人之權利。 四、退萬步而言,縱認錄製三張專輯唱片係被上訴人之義務,但查專輯錄製工作之所以未能如期完成乃因上訴人之拖延所致,如上訴人多次取消既定配唱計畫,或稱病告假,有工作底稿及製作人記事簿節本為證(原審被證四);上訴人於八十五年四月初提出醫生診斷書,藉詞須臥床休息六個月,此有中山醫院醫師診斷證明書附原審卷可稽(原審被證六),於本院言詞辯論時,上訴人雖補提八十六年八月廿八日中山醫院診斷證明書對八十五年四月六日之診斷書加以說明,但當時對提出之診斷書,並無此項記載,被上訴人並不知其真意如何,被上訴人依轉診診斷書辦理,並無不合,上訴人如認在該期間內可為錄製之行為,應隨時與被上訴人聯繫,或請醫生再為詳細之說明,其於本院言詞辯論時,如補提醫生之說明,已於事無補。由此觀之,上訴人確實有不配合錄製專輯唱片之情事,其不能完成專輯之製作,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 五、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之請求為無理由,原審為其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應予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無理由已臻明確,兩造其他之攻擊防禦方法均無庸一一斟酌,上訴人聲請訊問證人許卿燿,亦無此必要,併此敍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六 年 九 月 十七 日臺灣高等法院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李 文 成 法 官 陳 重 瑜 法 官 郭 松 濤 右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方 素 珍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六 年 九 月 二十三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