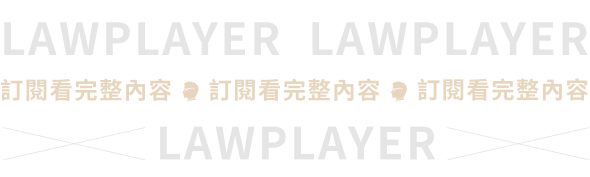案由
上 訴 人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官 被 告 戴榮聰 (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王忠沂律師 右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台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廿九日第一審判決(六十六年度訴字第六五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決關於戴榮聰偽造文書部分撤銷。 戴榮聰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處有期徒刑拾月。 偽造之陳春水約定書一本沒收。 事實 戴榮聰因於民國六十四年四月至同年九月,間多次與被害人陳春水之妻陳曾寶淑通姦(戴某妨害家庭部分早於本院前審判決確定)。至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八日,陳曾寶淑生下一男嬰,戴某以嬰係與陳曾寶淑通姦所生,為其骨肉,乃於同年四月卅日前往被害人家中討取此嬰,雙方發生爭執,繼則又於同年五月二、三、日連續(一)包括向被害人母陳曾寶淑討此嬰男嬰,並口出不遜,引起被害人不滿,被害人乃於同月六日具狀該管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告以戴某妨害家庭及恐嚇(恐嚇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無罪確定)。戴某經該分局於同月十四日訊問後,為求脫卸刑責,及將來可以索取該男嬰計,乃於同月十四日起迄同年六月十日間之不詳日期在其家中,利用陳某以往與其交往中,無意間遺置其家中之印章一顆,偽造陳春水名義約定書一紙內載:「茲為本人(按指陳春水)之妻曾寶淑於民國陸拾伍年壹月捌日所生之男孩,本人願意讓與載榮聰收為合法養子,恐口無憑,特立書為証」倒填年月日為民國六十五年一月書立,並偽造陳春水署押立約訂書人項下復,盜蓋上述陳春水之印章於其上,完成偽造行為,足生損害於陳春水(有使陳某將此嬰依約交其收養之危險)。並於原審法院檢察官於同年六月十四日偵查中,提出該偽造約定書之影本行使,據以主張陳某曾願將此嬰歸其收養,俾求脫卸其刑責,足生損害於陳春水(有使陳某將此交嬰依約交其收養之危險)。案經原審檢察官偵查起訴。 公訴意旨又以: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中旬,陳曾寶淑因患甲狀腺腫瘤病,由戴榮聰護送至沙鹿綜合醫院治療,於施行手術時,偽造陳春水名義之委託書,並在麻醉書及手術志願書上偽造陳春水之署押,以便陳曾寶淑施以手術。足生損害於陳春水。亦犯刑法第二百十條、二百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十六條之偽造文書罪云云一併起訴。
理由
一、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証據,並不以直接証據為限即綜合各种間接証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非法所不許。早經最高法院於民二十七年訴上字第六四號著有判例。 二、訊據被告戴榮聰雖堅決否認有盜用陳春水印章及偽造陳春水名義之約定書之情事。弁稱:「我們事先約好的,不分男女生下來都要給我收養」「是在生孩子前一年約定的」「因為他以前借我的錢,我答應這孩子給我收養,我以前的錢不必還,不要給他三萬至五萬元,他初說滿月要給我抱去,後來沒有實行諾言,以後就一直拖下去,至四月底,我去他家會談,我說不履行就算了,他欠我的錢要還」「後來沒有拿這張約定書向他要小孩」「這張約定書事沒你不拿給他看主張權利,一直到於被告偵查的時候才拿出來的,而且是影本」「約定書上原章是陳春水本人的,名字是陳春水簽字,稿子是我擬的」「約定書上圖章是真正的,他在六十五年一月四日用過(並提陳寶貞六十五年一月四日簽發本票一張,面額新台幣一萬元,號碼七一二六二六號,上有陳春水簽名及蓋章背書為証)」「我沒有偽造約定書,沒有向他強索小孩的事」云云(本院更(二)卷二八八,二九頁,五八頁,五九頁,一四五頁)。其在本院前審亦弁稱:「他們說他們有小孩要給我,我太太身体不好,只有一個小孩……」「約定書是一月十一日(按係指民國六十五年)曾寶淑結紮及肓腸開刀前在開刀房前面,陳春水一起在那裡,我向陳春水談叫他把約定小孩給我,寫的約定書,他叫我自己寫,然後當面陳春水簽名蓋章」「約定書是向台中醫院服務台護士小姐要的紙」「約定書不是偽造的」(本院上訴卷四四頁,一三三頁,一四八頁,一八三頁)「約定書是六十五年一月十一日前後寫的,詳細日期忘記了」「我沒有與他太太通姦」「他有同意其太太與我的結晶之男嬰歸我收養」「本院更(一)卷二五頁,三四頁)云云。 三、據查: (一)本爭之約定書陳春水署押,非陳春水所簽,及陳春水印章雖為陳春水所有,但該印章陳春水早已遺失,該印亦非陳春水所蓋,原無約定書所載之事實,實係戴榮聰所偽造等情,業據陳春水先後在原審偵審中迭訴甚詳「偵四○八○卷一○八的末行、一一二頁五六行、原審卷一九頁末行,六○頁九、十行,一三六鑑定頁六行,一三八頁二行,七──九行,反一頁─按本案有關上述約定書上陳春水印章與後述之委託書上陳春水印章相同,業經本院函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復在卷,且經陳春水於原審卷第一三八頁正面局第七──九行供明。是以,上述原審卷第一三六、一三八內陳春水關於冊印章之供詞,雖係針對後述之委託上之印章而為,但該印章總與約定書上為同一印章,則約定書上所蓋之印章,自亦係陳所有,並為陳某所遺失無疑)。 (二)被告戴榮聰對此約定書先則弁稱:係六十五年一月十一日所寫,繼則謂係陳曾寶淑生產此嬰後之第二日所立,後在本院前審復又模稜與其詞謂此約定書是在六十五年一月十一日前後寫害的詳細日期忘記了」(見本判決理由一內所証記告之迭次弁解)。据陳曾寶淑係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八在台灣省立台中醫院生下此一男嬰(見約定書內容所載),是則寫此約定書之日係具所供係陳婦生產後之第二日推算,應為六十五年一月九日,己與其前初所供為同年月十一日書寫不符,其後因見本院上訴字第四五六號判決內針對此點加以指駁。另又在發回更審中即本院上更(一)字第二五七號六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訊查中故為模稜其詞謂:六十五年一月十一日前後寫的,詳細日期忘記了」(本院更(一)卷二五頁)。用圖搪塞 矇混。誠屬欲蓋彌彰,均非可採。且係被告之本意弁解。指該約定書之用紙係在台灣省立台中醫院服務台向護小姐索取之。但據本院前審將原此約定書於送該院查明該院於民國六十五年一月間根据本無此种用紙函復在卷(本院上訴卷一七○)。再本案之約定書係被告所供係至陳曾寶淑於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八在台灣省立台中醫院生產後之同月十一日(或同月九日或同月十一日前後)(詳上述)彼與陳春水當面所寫。並由陳春水當場親自簽名蓋章(詳本判決既由(一)所記被告之弁解)。但查原約定書之內容及書立年月日以及所訴「立約定書人」「住地」等字均為被告以鋼筆書寫。若陳春水果屬在場,自必由被告隨手將鋼筆交付陳春水,並由陳春水隨手接過鋼筆當場簽名具上,不但極為簡便,且亦合於理論法則。你會再由陳春水另以墨跡渙散之筆(据被告稱可能係簽字筆)簽名,並見原審卷第一頁)於簽名後並蓋上私章(見原審卷第四四頁行政部調查局第六處通知單內載陳春水簽名墨跡渙散。本院上訴卷第一一一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通知書載約定書上之陳春水簽名及陳春水印章,係先墨後硃即而先寫字後蓋章)亦與情理不合。盡雙方既原係好友,陳春水復同意將此男嬰歸其收養,應屬雙方歡喜之事,由陳某簽名此約定書上,已足徵信。何必再加蓋私章,豈非多此一舉,逸出常情。況被告於原審就此「陳春水」三字何以會墨跡渙散對其偵訊時,初則供稱:「因為我用漿糊粘在委託書(按實係約定書之誤。因另紙委託書上陳春水三字並無墨跡渙散,模糊現象,因濕透才變成這樣」。嗣經追問何以約定書上其他字未跡未濕透,單單「陳春水」三字會變成這樣。則搪塞答稱:「不知道」(見原審卷三七頁六──二行)。繼復稱:「可能是簽字筆所寫之故」(同上卷六一頁四行)。尤見其係情虛敷衍,莫衷一是。況本案之約定書蓋章屬雙方同意,由具於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十一日或同月九日或同月十一日前後所寫,經陳春水當場簽名蓋章後,交其收執為憑。則其於事後即同年四月卅日五月二、三日彼又何必先後親自下或以電話向陳春水反陳曾寶淑迭索此男嬰並詔該男嬰係其與陳曾寶淑通姦所生(見偵四○八○卷六頁末行,二三、四二、五八),而不憑此約定書直接向陳春水主張判決,請求收養。且在其造次電話中又無一字半語,亦及沒有此約定書事。尤屬情于情理。想被告縱屬至愚,亦不致捨有利之正途而不為,反而,多次談話,口出不遜,向陳某等索討此男嬰。再被告在本院此次更審中所陳並無以在陳寶淑生此嬰一年前即與陳春水約好說無論男女均由其收養云云,尤屬不倫不類。並彼謂之一年前陳曾寶淑應尚未懷孕,又何能將來必懷孕等情。而預先約定收養互為勾結印記,可見此約定書確為其於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卅日,六月二、三日先後親自及以電話向陳春水,陳曾寶淑迭討此男嬰未果,復遭陳春水於同年五月六日具狀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告訴其妨害家庭及恐嚇、經該分局於同月十四日對其偵訊後,心中懼怕為求脫罪,始偽造此約定書,冀圖國將來在訴訟中提出,用以矇混卸責無疑。前再觀謂其在警局初訊中,亦無片字一語及此雙方約定收養及書立有約定書之事(見偵四○八○卷四、五、六、七、八)。立至杗移原審法院於被告於同年六月十四偵查時始以陳春水曾同意其收養共立有此約定書為辯解之理。原審既以認定,此約定書確係其於六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在警局接受偵訊以後迭)同年六月十四日稱以此約定書影本提出於原審法院於****期間內之不詳日期所偽造。否則,此約定書既早已在被告持有中,且此係其一生中僅有之大事,自不會輕而忘之一乾淨,而不於警局訊其:「有無與陳曾寶淑通姦生一男嬰,你要求帶走,否則要殺害陳春水全家之事」,僅遁詞等以「我有去他家,是向他討債,並無說以上之話」。而不據此約定書及陳某曾同意收養之間為辯。尤可認,此約定書確係在彼於警局應訊後,於**卷於上開日期偵訊前不詳日期所偽造。再其偽造此約定書,應自知為違法犯罪之事,自必祕密為之。是除捨在其家中偽造較為穩妥外,當不可能在他處冒險偽造。從而本判決衡度理性認定其係在其家中偽造,應合乎事實。末查此約定書之原審直至原審於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廿一日審理時,始由被告呈庭。可知始終均在其持有中。再參被告呈案之上述約定書原本上端之「天」已被齊邊剪去(該用紙第四行頂端當有殘留之字跡一小筆劃)。被告並謊稱此紙係台灣省立台中醫院之用紙(詳述),更足認其中大有隱情。蓋該約定書之用帛第四行頂端既留有字跡之筆劃,可見此帛為帶「銜」之公用紙。若果係台灣省立台中醫院或其他有利於被告及無不利於被告之機關或公司行號之用紙:被告又何必將此紙之「天」,齊邊剪去。即可認此「天」上之銜名被告大有不利。況被告對此种剪「天」之事,又不能作合理之解釋。竟謂「不曉得誰剪的」「本院卷一四八頁九行)尤有**乎理論。 (三)陳春水於原審審判中雖曾一度供稱:「約定書上章是我太太拿去蓋的」云云(原審卷三一頁一行)。但查其妻陳曾寶淑所拿之章為其另一印章即蓋在該陳婦入住沙鹿綜合醫院之手術麻醉志願書上者,並非此約定書上之章(見卷附陳曾寶淑住院歷──外於──內該志願書二份及本院上訴卷一一一頁刑事行政局通知書載:志願書上陳春水印章與約定書上者不同)。可見陳某此供與事實不符。況該陳某在原審復供稱:「此章早已遺失」「同原審卷六○頁)。互為印証,當以後者所供為可採。從然而,該陳某在本院前審調查中或謂該章非其所有,或謂該章係被告所偽造云云,顯均非實在。自難憑陳某此項不實之指訴,而律被告以偽造印章之罪刑。又被告與陳春水早年即已相交,且頗有經濟上之往還,已據被告及陳春水分別供述函在。是以,陳春水至被告家中借貸還債或洽談中,無意間而將蓋在本案約定書上之私章,遺忘於被告家中,亦屬情理之常有。被告事後發覺是此章,未即行檢還,固難認為有侵占遺失物之故意及犯行。但乃因其被陳某告訴,為求脫卸刑責:利用此章偽造約定書,究難辭盜印章之刑責。再參之此次更審中,被告竟又能提出有陳春水簽名背書,由陳春水之叫即証人陳寶貞簽發(實為証人即陳寶貞之夫陳以瑜代陳寶貞簽發)之六十五年一月四日面額新台幣一萬元之本票一紙,而該票上背書之陳春水印章之印文,經本院拆角比對,確與上述約定書上所蓋印章之印文相同。被告並弁謂該印章陳春水於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四日曾在使用,亦即指陳春水曾用該印章在上述本票上背書,用以證明該印章並非其所偽造的。但查本院並未認定被告有偽造此印章之罪行,已詳上述且縱令陳某有於民國之十五年一月四日用此印章背書,亦與其在事後之同年五月間利用陳某將此印章遺忘在彼處之機會予以盜用,偽造約定書之事實不相抵觸。已不能據此為其作有利之認定。況經如本院以此本票背書之事分別訊問陳春水陳寶貞陳以瑜之結果。陳春水已不記憶有在該本票背書蓋章之情事,陳寶貞則結証,陳春水僅在該本票背面簽名,未蓋章。陳以瑜則謂不知陳春水在該本案上簽名蓋章之事。何況被告所提出者係影本,且經本院令其提出此本票之影本,命由陳春水在該影本上蓋上陳某之另一圓形私章後,且加影印,亦與蓋與該影本上之上述陳春水之方印無差異(見本院更(二)卷)七一八九、一○二、一○五,一○六、一二二、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此,此本票影本後面陳春水之印章非但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明,且反面可據以証明,上述陳春水遺忘在被告處之印章,迄今仍在被告持有中。否則,被告又何能於本案已發生四年,迄今仍能提出此本票影本。顯可見此票影本背面之陳春水之印文係其在該案之影本後面加蓋上述私章後再行影印者。茲再觀察被告所提出其他紙據,背書僅有陳春水之簽名而無簽名與蓋章之併行之情事。(見本院更(二)卷六七──六九)。原屬昭然,至被告所提出之另一紙二萬元支票影本(本院更卷七○、一三一)背面雖亦有陳春水簽名後蓋章併行之事,但該支票既亦為影本,被告究非不能如法炮治,用圖矇混。實不定為其作有利之証明。又經本案陳春水背書之印文,經本院與上述約定書之印文比對,既屬相同,即出自同一印章已詳遽。自無再送有關機關鑑定之比要,被告於六十九年六月二日具狀說將此與本案影本連同約定書函送鑑定,用以証明蓋上陳春水之印文相同,然而,証明陳春水於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四日曾用過此印章背書該本票。即無必要。應於此指明。 (四)本案約定書上印文之印章,既為陳春水所遺失,嗣又發覺被告盜用此印章偽造約定書,已詳為上述,及衡之陳春水與被告早已相交,且迭有經濟上之往還,是以,此章為陳某章被告家中借貸還債或洽談中無意間遺忘在被告家中,亦理所恆有。從而,被告雖未能**發覺後即時返還陳某但究不能認為其有侵占之故意,而律以刑責。蓋既不能証明被告係偽造此印章又不能証據被告有侵占此章之故意及犯行。即難率以偽造印章或侵占遺失物論處。但此印章又確在被告之手中,由其加以望問自以認定為被害人遺忘在彼處為**事實。至復有偽造之上述約定書紙在卷可稽(存原省卷記物**)。 四、綜上而論,被告之前開辯解,均非可採,罪證洵屬明理,應予依法論科。原審未詳為調查推求遽而諭知無罪,當嫌率斷檢察官指**不當,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情由當本院予以撤銷,另行自為判決。 五、被告盜用印章,偽造署押,進而偽造私文書並持以行使均足生損害於陳春水。其盜用印章,偽造署押,均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應不另行論罪。其偽造私文書後持以行使(影本所載與正本毫無二致,其持影本呈向檢察官,並據該文書而主張其內容所載之權利,即屬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為高低之行使行為所吸收,應僅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查被告先則與被害人之妻多次通姦,破壞被害人之家庭,繼則又公然向被害人索討此因與被害人之妻通姦所生之男嬰不但顯示其霸道強悍,目無法紀,尤足証其不知羞恥為何物。及其被陳某告訴後,則又偽造此約定書行使,企圖倖脫刑責,並於偵查審判中,一再狡詞飾卸更見具刁頑無悔。惡行實屬重大應予從嚴科處,爰酌情量處適度之刑,用示怨儆。偽造陳春水名義之約定書一紙為被告因犯前所得之物,且屬被告所有,應依法沒收至偽造陳春水之署押已因隨上述約定書之沒收而沒收,毋庸另為沒收之諭知。併以敘明。 六、公訴意旨又以: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中旬,陳曾寶淑因患甲狀腺腫瘤症,戴榮聰護送至沙鹿綜合醫院住院治療。於施行手術時,偽造陳春水委託書,並在麻醉志願書及手術志願書上偽造陳春水署押,以便陳婦施行手術。應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七條之罪云云。維經訊據被告戴榮聰堅決否認有偽造等情,偽造文書進而行使之情事。弁稱:「志願書上陳春水的名字是我代簽的,章是他太太蓋的」「是她住院前寫好的陳曾寶淑拿回去交給陳春水自己蓋章」「陳春水委託我的」「他委託我辦理這些事情(按指陳曾寶淑住院手續)」「本院更(二)卷二八頁、五八頁、一四五頁後)。在本院前審亦弁稱:「是陳春水陳曾寶淑委託我辦住院手續,委託我寫的(按指志願書)」「志願書我寫好的,章是她委託我蓋的」「委託書是住院前寫好,我寫好叫她拿回去叫她先生蓋章」「本院上訴卷八一頁一行,八三頁七行,一四八頁四行)。而陳曾寶淑辯証:「志願書是戴榮聰寫的」「那天我先生叫我去,第二天才來醫院替我辦手續,後來我找戴榮聰來醫院」「陳春水章我帶出來,是他(按指陳春水)交給我的,因他答應我隔天就來……陳春水章是我拿給戴榮聰蓋」(見是本院上訴卷七九頁後)互為印証,足見陳曾寶淑前往住院時,確已得其夫陳春水之同意,**且志願書上所蓋用之陳春水印章,亦係陳春水交付,是則陳曾寶淑在其夫未至醫院前先以其夫之印章委託戴榮聰代填麻碎手術志願書二紙,並在志願書上代寫陳春水之姓名。及受陳曾寶淑之交託,在志願書上蓋下陳春水印章。不祇據無任何偽造文書之故意,且此志願書完全係應陳曾寶淑手術之用,而陳婦之手術,復已得有其夫陳春水之同意,則此志願書之書行使而交付沙鹿綜合醫院,亦無任何足生損害於陳春水及該沙鹿綜合醫院之可言。蓋陳春水既已同意其妻陳曾寶淑住院手術於先,則手術之一切後果即應由陳春水負責。沙鹿綜合醫院就此志願書之書立更屬可減其責任。當均無損害之可生。至本案之委託書上陳春水之印章,固經陳春水指明係其所遺失者,而其上陳春水之署押,復強原審法院函送司法行法部調查局鑑定結果認係筆書寫(見原審卷四四、六○)。及衡謂(1)小陳曾寶淑在本院調查中証稱:「那天我先生叫我去,他第二天才來醫院替我辦手續,後來我找戴榮聰來醫院」(可見事前根本無委託之事蓋如果有委託之事,陳婦何能會臨時找戴榮聰前來)(2)其當時未將此委託書一併繳付醫院(養其果已事前得有委託,定會將此委託書與志願書一併送繳醫院,用求責任分明)。(3)此委託書上蓋用之陳春水印章與志願書上所用者非屬同一(此點照本院前審函刑事警察局鑑定在卷──詳本院一一一頁──若陳春水果已委託其代辦,則當陳曾寶淑前往住院,陳某一時無法同往,而將印章交付陳曾寶淑時,不難會交付與委託書同一之印章,以免將來因兩章不同,醫院不予受理,影響手術時間。更會自行電請被告前往代辦,何能任由陳曾寶淑一人巠行先往醫院(等情。可見此委託書確屬事後,被告為恐代書自願書若有刑責,方予以偽造,用求脫責者至為明顯此再觀諸此委託書上所蓋用之印章確與上述被告所偽造之約定書上所蓋用者相同──見本院前審上訴字一一一頁形事警察局鑑驗結果通知書所載),尤無可疑。戴某之前開弁解,雖非可採信,經核謂此委託書之內容非但書明陳婦之住院手續及費用,一切均由他來代理。且陳婦之住院復已沒有陳水之同意(詳為上述)。從而,此委託書對陳春水實無任何足生損害之可言,殊與刑法第二百十條偽造私文書罪及第二百十六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不合,難令其負刑責,惟此部分,與被告所犯之上述偽造文書罪;檢察官係以連續犯起訴,為起訴上之一罪。即無庸另為無罪之諭知,合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的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次上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上段;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判決為主文。本件經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